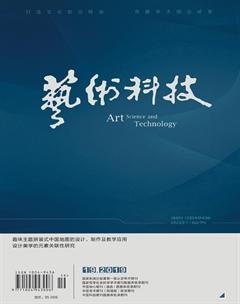布依族“斑布”技藝的生態智慧探析
摘 要:中國傳統染色技藝歷史悠久,與紡織技術的發展相輔相成,布依族的“斑布”技藝獨樹一幟。其傳統工藝中體現的生態智慧,既是展示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信的窗口,也與當下的綠色發展的生態理念相得益彰。
關鍵詞:布依族;染織技藝;綠色發展
扁擔山鎮位于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西部,縣境內東與丁旗鎮和城關鎮毗鄰,南連黃果樹鎮,西、北兩側分別毗鄰關嶺縣坡貢鎮和六枝特區落別鄉。山野上的各種植物如蘇木、紫蘇、蘭草以及苧麻都是傳統“斑布”染織的主要原料,豐富的水源也為漂洗染布提供了方便,當地的布依族服裝至今仍自給自足,與他們所生活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
明清以前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藍染的記載只有“瑤斑布”一條,一般認為“斑布”分“織為斑布”和“染為斑布”兩種。“斑布”產生與發展應當認為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因此,對“斑布”的藍染技藝及其生態智慧進行研究,是對傳統文化中的當代價值的挖掘;同時,倡導學習傳統文化知識,重拾民族文化自信,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實現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1 我國染色技藝的悠久傳統
我國的染色技藝有著悠久的歷史,主要分為礦物染色和植物染色兩種。礦物染色是指原始社會時期使用赤鐵礦粉末使麻布著色的辦法,多數礦物染料會對人體造成毒害,而植物染料的運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危害。據《夏小正》中“五月……啟灌藍蓼”[1]的記載可知,藍草是栽培歷史最悠久的染料作物。《天工開物》中也提到“凡藍五種,皆可為靛”,[2]北方的藍草以菘藍為主,而南方則多是馬藍。
宋代地理名著《嶺外代答》[3]記載:“瑤人以藍染布為斑……而镕蠟灌入鏤中”,此時的藍染已經出現了“蠟染”的字樣,但“防染”技藝應為傳統的樹脂防染到蠟防染的變遷過程,畢竟蠟的有效利用是一個過程,這也是各民族技藝文化相互交流的過程。
傳統染色多采用浸染法,通過將織物浸泡在染缸中進行著色,晾干后成色的方法,包括直染法、媒染法、還原法等。梔子、姜黃、地黃等一些可溶解于水中,且染液能直接吸附到纖維上的植物色素,就可以采用直染法。古籍中關于其染色方法的記載多描述為“煮以染”。另外,可根據某些植物中顏色在酸堿性溶液中的溶解度不同,來提取顏色進行染色,如制取含紅花素的染料。直接染色法工藝簡單,制備成本低,染色方便,卻容易掉色,牢度不高,因此在反復染色的過程中出現了“媒染法”。
媒染法即通過媒介幫助溶解或提高某些染料的染色牢度的一種方法,使用媒染法著色的植物主要為茜草、蘇木、紫草、黃蘗等。最早記載將丹秫用媒染法染色的是《考工記·鐘氏》,[4]羽毛在其中不同的浸泡次數,可形成從淺黃到絳紅的十分廣闊的暖色調,丹秫也是唐代以前染紅色的主要原料。由此可將這一工藝追溯到先秦時代。
還原法則適用于經還原氧化作用后才能染色的不溶性植物染料。藍草就是還原氧化植物染料,藍草中含有的靛甙經過水浸漬后可以染著織物上,再經過空氣氧化形成藍色的靛藍。
我國古代人民還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染色三纈”,實際上是分別通過用涂蠟、扎縫和夾板3種手段使織物被遮蓋的部分與染液隔離,從而使染過后的織物形成各種圖案和花紋。本文以布依族的“斑布”染織為主,對這些染色技術進行探討。
2 布依族的染織傳統
布依族的染色傳統可以追溯到古越族的“文身”習俗,西南地區的棉花種植可能早于中原地區,布依族對棉制面料染色的條件得天獨厚,染料以藍染和紅染為主。按照工藝的制作流程主要分為紡線織布、打藍制靛、蠟去花現三部分,最后根據需要做成傳統的民族服飾。
2.1 凹子寨的布依族的“斑布”染織技藝
布依族民族服裝制作所需要的染織技術包括:土布紡織、蠟染、扎染、吊染、繡花等,加之布依族本身對藍色的崇尚以及板藍根的種植,使得藍草在布依族的染織中占有了獨特的地位。
凹子寨的傳統技藝多以織布為主,“織為斑布”就是用“扎染”、夾纈的方法將線放入或用“吊染”的方法放入不同的染缸,染出多種顏色,再通過紡車將線繞在紡錘上,為排線做準備。
所謂排經線,就是將不同顏色的棉線按照需要順序進行排列,一根根穿過排線的“綜框”,綜框的縫隙數根據織機的大小有70-120個不等,數量越多,能織的布就越寬。穿過綜框的線要用繞線軸卷起來,并通過木棍固定后架在織布機上。織布的過程中“經線”在手動梭子的帶動下與“緯線”交織,最終織過布并用繞布軸卷起。織布機上的“開口綜框”越多,織出來的布自帶的花紋也就越好看。需要在此強調的是,在線上染色后再制成的布,帶有斑駁的顏色,加上各種織成的花紋,這樣的布就是前文所述的“織為斑布”,而“染為斑布”則在這一地區更為常見。
斑布蠟染的工序一般分為練布、點蠟、染色、脫蠟與清洗等部分。所謂練布,即在繪蠟之前,先將布料用草灰漂白洗凈,然后上漿、磨光,目的是使布質地變硬并且平整,方便涂蠟。
點蠟就是將蜂蠟置于陶瓷碗中,在底部加熱使蠟融化,再用蠟刀蘸蠟作畫。回收蠟的使用更是資源循環再生的體現,染色是將畫好的織物放入已經發酵過的染缸進行浸染,在染色的過程中要不斷將布取出,染液與空氣接觸進行氧化,剛取出的布呈草綠色,待氧化過后變成藍色。
脫蠟與清洗基本上是染布的收尾工序,這一步驟一般直接在河邊進行。首先把染好的布放在大盆中接水漂洗,去除浮色,然后將燒好稻糯草灰倒入大鐵鍋里加水煮沸,用木棍把染布輕輕地放入沸騰的水中,反復上下翻動,加速蜂蠟的脫離,最后挑出放入河水中清洗揉搓。脫在鍋里的蜂蠟用小盆冷敷法,使它冷凝在小盆外壁便于回收,即得到前文提到的回收蠟。
最后一步的清洗,就是先將脫蠟的染布在桶里清除浮色,再拿到河邊漂洗、晾干。在最后的漂洗過程中,好的染布基本不會對河水造成污染,而且所有的清洗過程不用洗衣粉,也就沒有二次污染。
2.2 布依族傳統染色技藝中藍草的使用
這里所指的藍草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板藍根,其種植時間一般為三月,種一次可以保持三年,藍葉的采摘一般都會在6、8、10月進行。《黎平府志》中就寫道:“藍靛名藍草……九月、十月間割葉入靛地,水浸三日,藍色盡出……以帶紫色者為上。”[5]布依族傳統的“采藍制靛”工藝,是先在河邊挖一個深坑引入河水,然后將采下的藍葉全部浸入水中,同時投入木板、石塊壓住藍葉,讓其沉入坑中發酵,這種方法叫“漚池”。同時,用尖頭的棍子插入池中扎出一些“氣孔”,以防止藍草發酵不均。《天工開物》明確記載,“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執竹棍攪動,不可計數”。[2]這也是防止發酵不均的手段之一。
“漚池”程序完成后,池中水將呈現黃色,并有白色沫子冒出,此時就到了“熟池”階段,這時要將藍草從池中取出來,把藍草架在池上,用清水沖淋入池,待藍草淋干。接下來的工序就是間斷性正反攪拌,據說有“靛打七套,五套扭頭”的說法,等到第二天經過沉淀后,放出藍靛池水面的清水,用布把靛泥兜出來,然后控干水,包好并收藏。若靛底光亮、細膩、瓷實,則質量上乘,若靛底暗澀、粗糙、易脫,則為次品。
做好一缸染料之后,要將靛泥收好,不時用靛泥去“喂”這缸染料。另外,要抽空去攪拌,布依族人把染缸當作孩子一般照顧著:要知冷知熱,看顏色察味道,像“養孩子”一樣每天養著它。染池最好的狀態就是最上面一層的顏色微微發紫,這時的染池就算是“喂飽”了。由于染池需要不停地“喂”,喂的又是取出的靛泥,因此制作染料的過程也沒有任何的污染物排放,這一池子染料可以用上幾十年,用得越久,染出的布的效果就越好。
3 布依族傳統染色技藝的生態性
布依族的染色技藝是我國傳統染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天人合一”的傳統觀念影響下,人們對自然充滿敬意,用料考究,注重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近現代工業化盲目追求利益產生了巨大差異,當下,強調生態保護成為人們的共識,從傳統文化中挖掘生態因素是文化傳承和生態保護的雙贏選擇。
3.1 布依族傳統染織中綠色發展的特點
布依族傳統染織的過程具備結實耐用、綠色天然、原料可循環3個特點。
從織布的角度來看,手工織出來的布經緯線就比較多,結構更加緊實,這就使得身上的布十分耐穿。就染色的角度來講,傳統還原染色法染出的衣物真正做到了不掉色、不脫色,色澤持久,這樣延長了傳統服飾的壽命。
由于傳統的植物染料多和藥材有關,古法制染可以做到從炮制染料到染出的各個環節對生產者不會產生多大的毒害,而且整個過程中很少有污染物的排放。最終染成的布顏色持久、不脫色,而且因為有植物的浸染,還產生了類似“中藥”的效果,不僅保護衣物防蟲、防霉,而且一些草藥成分對穿戴者本身也有好處。布依族人的便服常年都穿在身上,不僅舒適而且用“板藍根”染的衣服也會產生一定的保健作用。
原料的可循環性一方面體現在染料缸中的染料通過“靛泥的喂養”可以持久利用,“靛泥”本身也是上一個環節廢料的再利用。另一方面,脫蠟環節融化下來的蠟,被再次凝固回收做成回收蠟,這樣的蠟在理論上基本上沒有消耗,實則減少了原料的浪費和植被的破壞,使人與自然處于一種和諧的生態平衡當中。
3.2 傳統生態智慧的當代價值
布依族的染織技藝,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布依族的思想中體現為“一體”觀念,即布依族古歌《造萬物》中所講的“萬物由布靈的軀體變成,布靈與天地、布靈與萬物、萬物與萬物之間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因此,在這一樸素唯物觀的指導下,布依族認為自身與萬物“平等”的觀念,并不存在物我之分,從而延伸出要順應天時,要敬畏生命,要物盡其用地傳承智慧。其蘊含的“天人合一”可以給當代所提倡的生態思想帶來一定的啟示。
順應天時:藍草一般在夏季,日常管理較為簡單,所以剛好與水稻的種植時間錯開,并不耽誤農事。對于蜂蠟的使用,一方面是依靠油菜花、蠶豆花養蜂取蠟,后來由于不養蜂,更是將“回收蠟”反復使用。另外,其他作物收獲后的秸稈作為燃料,燒完的草木灰也可以很好地運用在藍染中,真正做到取用有節。
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觀念在敬畏生命方面強調萬物平等且相互聯系。在布依族的觀念中,魚蝦、藍草都是平等的,靛泥隨后也重新回歸染缸,靛泥完全是純天然的植物成分,在生態的循環中損害其他生物的生長環境。因此,在人們活動的改造下,山、水、林、草、田可以形成一個立體的循環系統,促進生態環境的有序發展。
實踐傳承:布依族的文化中服飾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表現,對布依族的女性來說,學習染織技藝,不僅是對傳統技藝的繼承,而且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方式。筆者希望,一些企業成立科研機構,研究傳統植物染料的產業化問題,通過學習和科研,將傳統中古人的智慧與現代相結合,走上生態綠色生產之路。
參考文獻:
[1] 戴德.大戴禮記1(卷二·夏小正)[M].盧辯,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19.
[2] 宋應星.天工開物(彰施·第三卷·藍靛)[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72.
[3] 周去非.嶺外代答2(卷六·服用門·瑤斑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64.
[4] 考工記17(卷上·二十四)[A].顏師古(唐).關中叢書[M].杜牧(唐),注,宋聯奎,校.陜西通志館,1936.
[5] 黎平府志(點校本)[M].黎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校注.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1420.
[6] 朱梭明.百越史研究[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156.
[7] 伍忠綱,伍凱鋒.鎮寧布依族[M].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4:179.
[8] 張新民.區域·傳統·文化[M].成都:巴蜀書社,2011:532.
作者簡介:張浩洋(1995—),男,河南洛陽人,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數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