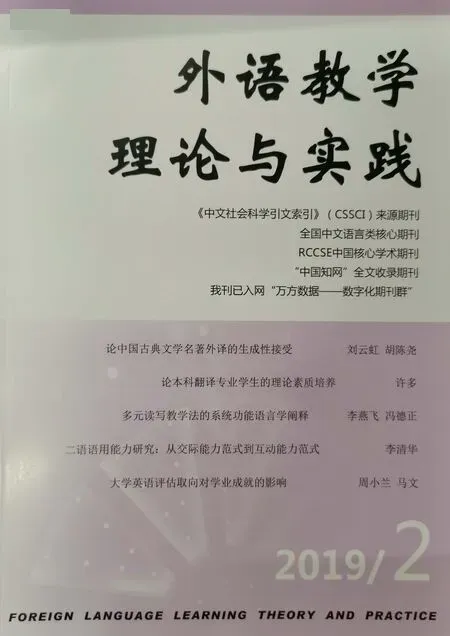教育語言學研究在中國: 領域與方法*
四川外國語大學 楊金龍 上海外國語大學 梅德明
提 要: 教育語言學自1972年誕生至今,已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相對于國外教育語言學異軍突起、百花齊放的迅猛發展勢頭,我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則存在研究領域單一、相關實證研究匱乏的窘境。文章通過梳理和分析國外教育語言學的發展概況,認為在面臨戰略轉型的新時期,我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應聚焦于教育中的語言問題,以雙語教育、語言服務、外語教學的生態觀、移民/特殊群體的語言權利與教育、漢語的對外傳播等話題為切入點,并對部分研究方法進行了介紹。
一、 引言
教育語言學(Educational Linguistics)從產生到成熟,直至成為語言學領域的新興學科,迄今已有四十多年歷史。教育語言學的主要關注點是教育中的語言問題,包括教育過程中的語言發展與使用、語言學習者的權利與文化認同、二語/外語的教與學、國家語言戰略與規劃等研究領域。以“Educational Linguistics”為關鍵詞在Google Scholar檢索發現,自1972年“教育語言學”誕生至今,國外公開發表的相關文獻已超過1 500篇,所涉及的研究視角包含學科綜述、語言政策與規劃、語言測試與評價、二語/外語的教與學、多語地區的語言使用與權利、語言身份認同、語言的經濟價值分析等多類話題。相比之下,國內語言學界的相關研究多停留在對該學科的綜述與介紹階段,所討論的話題局限于二語習得、大學英語教學、外語教師教育等視角,研究廣度仍相對匱乏,與之相關的實證研究極度欠缺。本文認為,中國幅員遼闊、少數民族眾多,語言學習與使用情況豐富,適合我國語情特點的教育語言學研究仍有很大的發掘空間。文章擬通過梳理和分析國外教育語言學的發展概況,著重討論適合新時期我國語情特點的研究領域,并對與之相關的部分研究方法進行介紹,以期為我國教育語言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思路。
二、 教育語言學的學科概況
2.1 學科發展
“教育語言學”一詞最早由Bernard Spolsky提出。Spolsky認為,應用語言學受其名稱的限制,所研究的領域過于寬泛而缺乏清晰的研究主方向。此外,應用語言學中最主要的研究領域——語言教學過于關注語言學的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而對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與語言教學密切相關的其他學科知識探索不足。懷揣著對應用語言學學科發展現狀的不滿與探索精神,Bernard Spolsky在1972年第二屆應用語言學年會上首次提出“教育語言學”一詞,隨后在新墨西哥大學教育學院設教育語言學博士專業,并于1978年出版第一本教育語言學專著EducationalLinguistics:AnIntroduction(教育語言學導論)。
同期(1976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學院在Dell Hymes的帶領下設立教育語言學博士專業,開設社會語言學、教育語言學、心理語言學、二語習得、語言與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等課程。本世紀初,該校Nancy Hornberger教授扛起美國教育語言學大旗,認為教育語言學已經具備獨立學科的基本條件,將教育語言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三點(Hornberger 2001): 1) 語言與教育相結合;2) 以問題為導向、以教育實踐為出發點;3) 視語言的教與學為關注焦點。2008年,Nancy Hornberger主編EncyclopediaofLanguageandEducation(語言與教育百科全書)共計10卷本;2012年主編EducationalLinguistics:CriticalConceptsinLinguistics(教育語言學: 語言學的關鍵概念)共計6卷本,大量專著的出版為教育語言學在世界范圍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源。
上世紀九十年代,功能語言學派代表Halliday(1990)對教育語言學的研究領域與范式做出進一步闡述,認為教育語言學不應僅被視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其研究領域應以主題為基礎(theme-based),采取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范式。Halliday(1990)通過教與學兩方面對教育語言學的研究視角進行舉例,將教育語言學的研究范圍具體化。Halliday(1990)認為,從教學角度來講,教育語言學研究可討論教材的語言與語域問題、課堂話語研究、語類研究等;從學生的學習角度來講,教育語言學可討論語言用途、語言學習環境(尤指校外的語言學習環境)、功能語法及語篇等問題。
2.2 學科定位
目前,就教育語言學的學科定位問題,語言學界一般持以下四種觀點: 1) 教育語言學等同或隸屬于應用語言學,側重對外語教學的相關研究。持此觀點的學者多為教育語言學研究的早期引領者,相關研究成果多出現在教育語言學學科“身份未定”的時期。眾所周知,應用語言學這門學科在成立之初即是以研究外語教學為主,狹義的“應用語言學”實際上就是指外語教學。從“教育語言學”的字面意思來看,這門學科所談論的中心問題就是教育當中的語言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應用語言學的研究焦點有相似之處。2) 教 育語言學是教育學與語言學兩大學科的“交界學科”(interdisciplinary)。持此觀點的學者(如Van Lier, 1994等)強調語言學與教育學之間的交互關系,認為教育語言學所關注的問題應包涵兩大方面,即涉及語言理論與實踐的教育學問題、涉及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語言學問題。這兩大問題分別是教育學與語言學所關注的話題,因而教育語言學應為教育學與語言學的交界學科。3) 教 育語言學是教育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相融合的“多界學科”(multidisciplinary)。該觀點認為(如Splosky 1978),教育學與語言學的相關理論知識并不足以解決教育語言學所涉及的全部課題,其研究問題還需要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知識進行補充,因此,教育語言學具有“多界學科”屬性。4) 教 育語言學是基于且超越上述學科的“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教育語言學的研究特點是以問題為導向,即Nancy Hornberger(2001)所提到的“領域寬而焦點窄”,或Halliday(1990)所提到的基于主題(theme-based)的“超學科”研究。近幾年來,我國不少學者也就教育語言學的“超學科”特性進行了探討與展望。
本文認為,首先,教育語言學在產生之初即是從應用語言學中獨立出來,雖然其主要研究領域與狹義的應用語言學有所交集,但教育語言學除了關注外語教育以外,還對語言教育政策、課堂話語分析、語言身份認同、生態語言與保護等話題有所涉及,其研究領域與關注焦點更具針對性,因此,將教育語言學等同于應用語言學的觀點有待進一步討論。其次,不論是Halliday(1990)所提到的主題式“超學科”研究,還是Nancy Hornberger(2001)所提及的“領域寬而焦點窄”,均是在探討教育語言學的研究范式與方法問題,而非學科定位問題。教育語言學的研究特點雖是以問題為導向,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輔助,但其研究焦點明確,關注的是教育過程中所產生的語言問題。若以上述第四個觀點定位教育語言學,則難免將教育語言學陷入“多領域而無焦點”的窘境。最后,將教育語言學定位為交界學科或多界學科也并不能夠完全體現其特點。例如,若視教育語言學為教育學與語言學的交界學科,則既可將學科落腳點定位在語言學,稱其為“教育語言學”,也可將學科落腳點定位在教育學,稱其為“語言教育學”,致使學科焦點模糊(梅德明,2012);若視教育語言學為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多界學科,雖可涵蓋教育語言學的絕大多數課題,但同時令該學科從學理上過于寬廣而缺乏界限。因此,教育語言學雖具有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特點,但其核心課題應始終聚焦在教育中的語言問題,即學科落腳點應定位在語言學,僅對Spolsky(1978)、Nancy Hornberger(2001)等學者所提到的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進行一定的借鑒。
2.3 研究領域
從教育語言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幾位代表性學者對教育語言學研究的理解和關注點各有側重。最早提出“教育語言學”概念的學者Bernard Spolsky利用新墨西哥州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勢,長期從事雙語教育研究,對多語地區的語言生態與保護(Spolsky, 1970)、多語環境下二語學習者的語言身份與認同(Spolsky, 1991)、多語地區的語言政策與規劃(Spolsky, 2009)等話題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與討論;教育語言學的另一位領軍人物Nancy Hornberger則擅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其成果多強調雙語/多語教育中的社會文化因素、雙語讀寫能力研究、語言的生態觀等(Hult, 2011);Leo van Lier所從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聚焦于語言學習的符號與生態觀,認為語言的教與學不應僅關注學校內部,而應從學校、社區、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進行生態考量(Van Lier, 2004);無獨有偶,英國的教育語言學家Stubbs也強調從社會、文化、歷史視角來研究語言教育,用批判的眼光評價雙語環境中所出現的語言權勢問題(Stubbs, 1991)。近幾年來,Francis M. Hult主編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教育語言學專著,為有志于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源。例如,Francis M. Hult與Bernerd Spolsky合編的TheHandbookofEducationalLinguistics(2008)中涵蓋了教育語言學研究的五大領域,即教育的語言與文化因素、語言教育政策與管理、雙語讀寫能力發展、語言習得和語言測試;兩年后,DirectionsandProspectsforEducationalLinguistics問世(Hult, 2010),該書從語言教育政策、語言多樣性、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四大板塊出發,對教育語言學的課題走向進行了展望;2011年,Francis M. Hult與Kendall A. King合編EducationalLinguisticsinPractice一書,對雙語/多語地區所面臨的教師認同、課堂語碼轉換、學生的讀寫能力發展、難民家庭的工作語言、語言多樣性的保護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2.4 研究方法
傳統意義上的外語教學或二語習得研究,多從師生的教學/學習方法、情感態度、認知加工等方面入手,通過心理語言學相關理論、教學理論、學習理論進行分析,運用測試、問卷等手段進行量化統計,質性研究方法多作為輔助手段以提高研究的信效度。相對而言,教育語言學的相關課題在研究過程中采用質性方法的比重較大,研究更傾向于從社會文化、個體認同感、語言權利、語言生態等方面入手,采用人類學研究方法收集數據,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知識綜合分析。從教育語言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幾位學科代表人物均傾向于采用質的研究方法開展教育語言學研究。例如,Bernard Spolsky多從社會學、社會語言學、交際民族志角度出發,提倡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語言教學與語言規劃問題;作為資深的人類學、社會語言學研究專家,Dell Hymes側重用文化人類學的理念來研究語言教學問題,尤其關注不同的語言、文化習俗對雙語學習者產生的限制與困境;隨后扛起教育語言學學科大旗的Nancy Hornberger致力于少數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社會弱勢群體的語言文化研究,同樣傾向于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側重對雙語/多語地區的語言教學實踐與語言規劃進行討論;長期從事教育語言學研究的英國學者Stubbs也聚焦于語言教育過程中的社會、文化、歷史因素,常采用課堂觀察、個案研究的形式進行資料收集。綜上可見,相對于傳統的外語教學或二語習得研究,教育語言學相關課題更加關注研究個體的社會文化環境,傾向于通過質的研究方法收集各方數據,運用自下而上的視角進行分析,具有較明顯的社會學轉向。
三、 國內教育語言學研究展望
我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雖起步較晚,但近年來與之相關的研究也逐漸興起。2010年5月,“中國教育語言學研究會”在上海正式成立,至今該會已成功舉辦七屆。CSSCI來源期刊《外語與外語教學》于2016年第三期特設教育語言學專欄,也從側面體現出國內核心期刊對教育語言學的關注。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多以文獻綜述、外語教學、二語習得、教師教育等話題展開討論,研究廣度仍有較大發展空間。例如,在2016年第七屆中國教育語言學研究會上,會議仍圍繞大學外語教學改革、外語專業人才培養等議題展開,對符合國內語情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發掘不夠。
3.1 研究領域
Halliday(1990)提出,教育語言學的研究領域應以主題為基礎(theme-based),采取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范式;沈騎(2012)認為,教育語言學的學科特性是以問題為導向,將實踐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雖是以問題為導向,但所探討的問題終究不能廣泛無邊,正如梅德明(2012)所提,教育語言學的研究問題“若什么都可以,必然什么都可以不了;什么都能干,必然無一能干好”。本文認為,在戰略轉型的新時期,我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應始終圍繞“教育當中的語言問題”這一核心,除涉及上文所提的傳統研究領域外,或許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 英-漢雙語教育。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為貫徹施行“引進來”方針,國家、企業、學校和家庭各個層面過于重視英語教育,致使孩子接觸英語的年齡越來越早。語言與社會文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不同的語言承載著不同民族的知識與文化精髓。過早讓孩子接觸英語,而對母語教學關注不足,是否會使孩子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認同感、甚至母語的使用(如語言磨蝕)等方面出現消極效果?新時期的中國已由“引進來”向“走出去”逐漸轉型,將中華文化傳向世界的歷史重擔在此時期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平衡國內學生教育的英、漢教學比重,無疑是當下語言教育政策的重要議題。
2) 少數民族語言-漢語雙語教育。當前,我國大部分民族地區實行少數民族語言-漢語雙語教育政策。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由于漢語的權勢地位高于少數民族語言,部分少數民族學生及其家長更傾向于增加漢語的授課比重,以提高學習成績、高考錄取率。然而,在課堂中過多使用學生并未熟練掌握的漢語作為教學媒介語,是否會影響教學效果?國外有學者(如Mohanty, 1994;Tove Skutnabb-Kangas, 2008)認為,過早將兒童暴露在第二語言的學習環境中,兒童的學習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會出現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不能完成學業任務等現象。再者,若盲目增加漢語授課比重而忽略本民族語教學,在多大程度上會導致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在未來出現轉用甚至瀕危的狀況?諸如此類問題仍需我國學者進一步考證。
3) 語言服務。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語言是實現“五通”的重要基礎之一,是“促進人文交流,實現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也是服務互聯互通建設的重要支撐”(沈騎,2015)。“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必將促進沿線國家之間人員的流動,屆時沿線國家的交通、商業、教育、旅游等各行業之間的交流勢必增加,與之相關的語言服務壓力也隨之提高。由此,李宇明(2015)提出,“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然而,長久以來我國的外語人才培養模式過于單一,造成英語人才過剩而其他“小語種”人才短缺的窘境,能夠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語言服務的人才尤為不足。如何充分發揮全國各地的地理、人文環境優勢,培養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語言服務工作的外語人才,無疑是近幾年小語種人才培養戰略的攻關課題。
4) 漢語的對外傳播。當下,世界范圍內刮起“漢語熱”浪潮。在國內,各大院校招收外國留學生的數額比例逐年上升;在國外,開設孔子學院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于英語的國際“霸主”地位,漢語的國際影響力仍亟待提高。留學生在學習漢語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認同問題、母語對漢語的遷移問題、漢語教師的自身發展問題等,都可成為該領域深入討論的話題。
5) 外語教學的生態觀。談及外語教學,傳統的研究話題往往圍繞外語教學法、外語學習者的認知加工過程、外語教師教育等展開。外語的生態教學觀則強調將學習者在校內、社區、家庭、學習者個體差異等因素視為一個整體。課堂中如何使用與調整教學媒介語;如何充分利用新媒體、電子游戲、新科技對外語學習的輔助性作用;學習者的社區、家庭生活對其外語學習有何影響(社區的語言景觀、社會文化條件等因素);學習者自身的語言認同感等話題,是國內教育語言學研究的新突破口。
6) 語言能力測試與評價。作為外語人才的重要儲備力量,我國中小學生的外語能力關系到國家的外語人才發展、國家外語能力的戰略發展。然而,當前我國的中小學外語能力培養體系中尚無統一的外語能力標準,相關描述僅體現在不同階段的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和教學要求之中,而外語能力標準不明確又間接導致目前中小學的外語評價體系相對混亂。由此,我國的中小學外語培養體系在縱向不能與大學外語教學進行有效銜接,橫向又不能照顧到我國東西部師資、生源的差異,致使我國的中小學外語教學長期呈現“費時低效”狀況。當下,我國的“走出去”戰略方針要求我國在培養外語人才的過程中,不僅應注重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等傳統語言能力,同時對其跨文化交際能力、創新能力、學習能力等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y)有了更全面的要求,外語人才的能力構成趨向個人綜合能力、語言能力、交際能力、學習能力、創新能力等多維發展態勢。因此,關于中小學生的外語能力及評價體系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7) 移民、特殊群體的語言權利與教育。目前,便利的交通條件致使世界范圍內人口流動空前增大。我國東、南部發達城市(如上海、蘇州、廣州等)的人口結構趨于復雜化。一方面,外國移民、留學生人口不斷增多;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本國務工群體也移居工作城市。因此,國內外移民子女的語言權利與教育問題已成為議題。此外,與國外相比,我國關于特殊群體的語言教育研究(如手勢語研究、聾啞學生的語言習得等)仍十分薄弱,亟待相關學者的進一步探究。
3.2 研究方法
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即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本質差別在于其理論欲求不同(張培等,2013)。質性研究的主要理論欲求是通過歸納,進而發現規律;量化研究的主要理論欲求則是通過推理,進而對研究假設進行論證。Bryman(2004)曾就歸納與推理作出區分: 歸納是數據在先,理論在后;推理則是理論(假設)在先,數據、結果在后。
傳統的應用語言學傾向于以理論為導向,采取自上(理論)而下(實踐)的研究范式,將語言學的理論應用于實踐,近似于Bryman所提的“推理”;教育語言學的學科特性則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以實踐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沈騎,2012)。這就意味著教育語言學研究并不以某一語言學理論為中心,通過理論解釋實踐;而是以語言教育中的現實問題為研究中心,將與之相關的理論、研究、實踐等融合在一起,近似于Bryman所提的“歸納”。如此一來,國外教育語言學研究多采用以質性為主的方法就不足為奇了。結合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我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可圍繞前文提到的語言教育熱點問題,從研究對象自身的內部因素、其所處的外部環境兩個路徑予以剖析。現相應地介紹兩種研究方法:
1) Q方法(Q-Sorting Method)
在語言的教與學過程中,參與者自身的內部因素可通過Q方法進行剖析。Q方法首創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心理學界。近幾年來,該方法已運用于社會學、管理學、語言學(如Lo Bianco, 2015)等多個領域的研究當中。與科學實證主義傳統下的量化研究相比,Q方法以“發現”作為其研究的最終目標,更加強調個體主觀性與個別性的價值(趙德雷、樂國安,2003),其研究多用于理解“How”或“What”等問題,而非解釋“Why”的問題。Q方法的操作過程拒絕了問卷、量表、測試等方法中對人群抽樣的依賴,而選擇對問題抽樣,通過研究對象的主觀排序(Queue)來獲取其內心的真實想法。根據Q方法的操作特點,研究者可對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語言學習群體(尤其是移民、少數民族)的心理因素、跨國語言教師的文化沖突等相關研究課題取得更深入的突破。
2) 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研究適于對研究對象所處的周圍環境進行全方位考量。民族志研究最早源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人類學界(如Malinowski、Mead等)。數十年以后,該方法開始逐漸進入社會語言學、教育學者的視野。民族志研究善于從文化角度闡釋個體的行為、互動及其周圍的事件(Agar, 1983),從而達到在自然、持續進行的環境中分析個體或群體的行為的效果(Watson-Gegeo, 1988)。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與側重點可對我國多元文化地區的雙語教育、“一帶一路”與語言服務、外語教學的生態觀等研究課題進行更全面的解析。以多元文化地區的雙語教育研究為例: 長久以來,我國絕大部分的多元文化地區受經濟、交通、環境等因素的制約,雙語教育中“費時低效”的問題尤為突出。民族志研究方法可對該地區雙語學習者的文化認同、語言使用環境(如語言景觀)、學習生活環境等方面進行更全面的剖析,“自下而上”地對該區域的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提供研究素材。
社會文化視域下的教育語言學研究除了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外,還包括其他研究方法,例如敘事研究、個案研究、話語分析研究、行動研究等,研究者在明確研究問題前提下合理選擇不同的方法論。
四、 結語
在科技、交通日益發達的新時期,雙語、甚至多語的語言社會環境日益普遍化,影響語言學習效果的因素決不僅限于課堂教學內部,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開始關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學習者個體等課堂教學以外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傾向于從語言教學的社會文化視角入手,對語言的教與學進行綜合考量的教育語言學無疑具有相當明朗的發展前景。本文通過梳理和分析國外教育語言學的發展概況,對適合新時期我國語情特點的部分研究領域與方法進行介紹,希望能為我國教育語言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