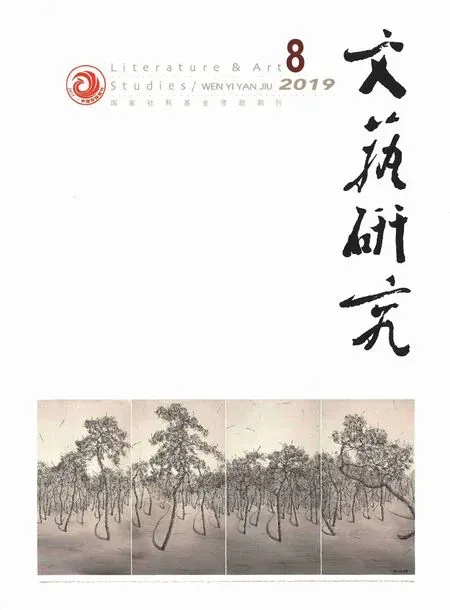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情性”的古今之變
——從儒家政治哲學(xué)到“情本體”美學(xué)
馮 慶
一、傳統(tǒng)情性論與“情本體”的古今張力
“情性”是儒家政治哲學(xué)最為核心的概念之一。在儒家經(jīng)典里,有時“情性”或“性情”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出現(xiàn);有時“情”“性”二字各自有著不同的意涵。
荀子曾對“情性”的整體概念進行定義: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惡》)①
在此,“情性”指的是身體觸碰外間世界并產(chǎn)生愉悅感的一種人固有的自然傾向,顯得像是對生命在世狀態(tài)的整體概括②。
荀子還曾將“情”“性”分而論之: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zhì)也;欲者,情之應(yīng)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jié)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jié)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jié)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③
盡管荀子多連稱“性情”或“情性”,將“情”或“欲”視為“性”的子概念④,但在這段話里,荀子顯然是將“性”和“情”安置為人生的不同心靈狀態(tài)階段:“性”是人的“自然狀態(tài)”,是“情”未發(fā)之時的狀態(tài);“情”是這種自然狀態(tài)的質(zhì)化呈現(xiàn),是其未經(jīng)文飾的表達。“情”的呈現(xiàn)必然是由于“欲”的方向指引。“欲”是人之所不可盡去的,但可以用“心”去節(jié)制,這種節(jié)制的實踐,則是“偽”——人為的規(guī)范。由此而論,對荀子的情性論的美學(xué)式關(guān)注,實則會引出一套修身的倫理學(xué),乃至于制度立法的政治哲學(xué)⑤。荀子認識到,情欲的無法滿足是世間常態(tài),而人必須生活在“群”當(dāng)中,遵守各自的“分”,因此“禮義”也就必須存在。而其不至于偏移的基礎(chǔ),則是“心知”的好惡是非之辨。圣人的“心知”能力由此可以為世間立法,這就是情性二分論所通達的政治哲學(xué)問題域⑥。
在董仲舒筆下,荀子的觀念和孟子一脈的天道性善論得以結(jié)合,構(gòu)成了中國儒家政治哲學(xué)關(guān)于民人情性問題的典型政治哲學(xué)表達:
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栣眾惡于內(nèi),弗使得發(fā)于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栣也。人之受氣茍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圣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zhì)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zhì)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⑦
人之自然之“性”稟受陰陽二氣,進而有“貪”“仁”兩種志氣,“天”既然讓陰陽二氣保持平衡,那么人之“心”也應(yīng)當(dāng)限制情欲,使“貪”“仁”保持平衡——“性”的自然之氣稟也將在這種“心”的看護中逐漸朝向“與天道一”的境界邁進;重要的是,和荀子一樣,董仲舒尤為強調(diào)一個在先的圣王作為立法者,他能夠憑借制度教化的施行,引導(dǎo)這種性情的潮流在正確的渠道中運行。
根據(jù)對荀、董二人情性論的概括,可以看到,在傳統(tǒng)儒家語境里,情性論本質(zhì)上是關(guān)注“立法”與“治理”的倫理政治哲學(xué)。然而,在當(dāng)代語境里出現(xiàn)了一個重要的轉(zhuǎn)向:儒家思想關(guān)于情性的討論空間為源出于西方的美學(xué)所接管,關(guān)于情性的政治哲學(xué)命題則被轉(zhuǎn)譯為基于人之普遍感性的美學(xué)命題。李澤厚的美學(xué)思想是這種轉(zhuǎn)向的典型代表:
人在物質(zhì)操作的長久歷史中所積累的形式感受和形式力量,由于與整個宇宙自然直接相關(guān),便具有遠為巨大的普遍性和絕對性……這里所說的存在和形式感并不是理性工具,而是直接與感性交融混合的類比式的情感感受,這種感受是一種審美感受。它的特點是與對象世界具有實際存在的同一性。它是與宇宙同一的“天人合一”。⑧
李澤厚這一論斷中顯著體現(xiàn)出康德、馬克思乃至海德格爾的思想沉淀,也充分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美學(xué)的基本訴求:讓身體感性借助審美直觀能力與理性達成統(tǒng)一,為人類心靈賦予盡善盡美的內(nèi)容,讓個體融入整全宇宙秩序中。用傳統(tǒng)儒家哲學(xué)尚未被轉(zhuǎn)譯的話語來說,就是借助“情性”不斷“感應(yīng)”天地,整飭內(nèi)心,實現(xiàn)對“道體”的通貫,直至“天人合一”:
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yīng),所應(yīng)復(fù)為感,所感復(fù)有應(yīng),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⑨
當(dāng)然,傳統(tǒng)儒家的教化方案還需要“善惡之理”的客觀基礎(chǔ)來進行調(diào)適。甚至,是這種對“善惡”的理論考慮,而非對“天地”的神秘溝通,構(gòu)成了情性修持論的核心要素: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⑩
在這個意義上,現(xiàn)代美學(xué)和傳統(tǒng)儒家哲學(xué)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切割了面向“自然”的感性生活和面向“善惡”的理性生活。傳統(tǒng)儒家哲學(xué)基于“善惡”的考慮而試圖提出的對情性進行約束調(diào)教的理念,恰恰構(gòu)成了現(xiàn)代情性論美學(xué)必須要超越的對象。這種超越并不是否認“善惡”的客觀性,而是將“善惡”之理置于人之自然生存的感性進程中,使其化為審美經(jīng)驗的附加物。在長期的審美經(jīng)驗的積淀中,人們能夠養(yǎng)成“一種動物本能性”,憑借這種審美直覺“合道德而超道德”。因此,情性論的美學(xué)修持不光可以“以美啟真”,還能“以美儲善”甚至“以美立命”?。
李澤厚把美學(xué)視為“第一哲學(xué)”,其理論基礎(chǔ)是“歷史中的人”或者說“內(nèi)在的人化”?這一哲學(xué)人類學(xué)觀點。這種觀點假設(shè),在歷史性的此在生存過程中,“宇宙自然”持續(xù)對人的身體施加力量,激發(fā)其審美情感,才能夠讓其由最初的單純感受不斷上升為對整全的成熟感受。沒有這樣一個歷史化的過程(無論是集體的發(fā)展過程還是個體的成長過程),也就沒有作為情性修養(yǎng)計劃的“美學(xué)”的用武之地。
其實,這種歷史化的人類觀,是由康德訴諸審美鑒賞力不斷激發(fā)道德進步的啟蒙史觀所奠定的:
理想的鑒賞具有一種從外部促進道德性的傾向。——使人在自己的社交場合溫文爾雅,這雖然并不能等于是說,把他塑造成道德上善的(有道德的),但畢竟通過在這種場合使別人愉悅(受到喜愛或者贊賞)的努力而為此做好了準備。
人由于自己的理性而被規(guī)定為與人們一起處在一個社會中,并在社會中通過藝術(shù)和科學(xué)來使自己受到教化、文明化和道德化……人必須被教育成善的……?
重點在于,李澤厚會把這種過程上升為本體論化的哲學(xué)原理,與儒家傳統(tǒng)的“仁”或者“情”的本體概念進行對接。比如,李澤厚曾借馮友蘭的話說,“康德只講‘義’,理學(xué)還講‘仁’”——中國人會“從現(xiàn)象中求本體,即世間而超世間”?。因此,盡管李澤厚的理論中有著揚棄傳統(tǒng)儒家哲學(xué)本體化“善惡之理”的動機,其對道德情感體驗過程的重視和再度本體化,又顯得是對傳統(tǒng)情性論的揚棄和發(fā)展。
當(dāng)然,“仁”或者“情”在傳統(tǒng)儒學(xué)中的本體化,與現(xiàn)代美學(xué)的基本架構(gòu),在理論上難以調(diào)適。李澤厚也意識到,理學(xué)對“仁”的把握確實蘊藏了歷史本體論美學(xué)的視角,但其中又有著一種曖昧的雙重意謂,無法與現(xiàn)代理性與感性二分的哲學(xué)框架相協(xié)調(diào):
像“仁”這個理學(xué)根本范疇,既被認作是“性”“理”“道心”,同時又被認為具有自然生長發(fā)展等感性因素或內(nèi)容。包括“天”“心”等范疇也都如此: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超自然的,又是自然的;既是先驗理性的,又是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既是封建道德,又是宇宙秩序……?
李澤厚相信,這種感性因素和形而上學(xué)因素并舉的雙重性,使得理學(xué)的心性理論結(jié)構(gòu)格外不穩(wěn)定,隨時會因為義理上的曖昧而引發(fā)現(xiàn)實中的倫理爭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澤厚認為,只要揚棄掉其中“追求超驗理性的失敗”,回到某種“道始于情”的“原典傳統(tǒng)”,就能夠進一步整合出一種“以情本體為核心的中國樂感文化”,由“人際世間的倫常情感”轉(zhuǎn)換出“超世間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感”,通過消解“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的觀念,“回到感性存在的真實的人”,也就是回到“自然情欲”這一生存性本原?。
綜上所述,李澤厚強調(diào)作為人類歷史生存體驗的情性本體,本質(zhì)上是要以其承擔(dān)感性維度的價值基底,從而建構(gòu)一種與節(jié)制情欲的傳統(tǒng)觀念截然相反、而有助于現(xiàn)代生活情感解放的新派倫常體系。在這個意義上,李澤厚那作為“第一哲學(xué)”的美學(xué),對傳統(tǒng)儒家政治哲學(xué)的顛覆遠遠大于繼承。
在近年的《舉孟旗行荀學(xué)——為〈倫理學(xué)綱要〉一辯》一文中,李澤厚指出,有必要延續(xù)荀子、朱熹的路徑,用規(guī)范性的“四端”(仁義禮智)補足作為自然感受狀態(tài)的“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這種思想填補的工作,將使得具有“更普遍的人類性、世界性”的儒學(xué)在未來實現(xiàn):
中國傳統(tǒng)以塑建“情理結(jié)構(gòu)”為人性根本,強調(diào)“好惡”(情感)與“是非”(觀念)同時培育、相互滲透,合為一體……它也可說是一種儒學(xué)內(nèi)部的“儒法互用”,即以情潤理,范導(dǎo)行為……今天需要對此傳統(tǒng)分析、解構(gòu)而重建之,即以情本體的宇宙觀和宗教性道德來范導(dǎo)和適當(dāng)構(gòu)建公共理性的現(xiàn)代社會性道德。?
這種以“情”導(dǎo)“義”的觀念設(shè)計是否可行,姑且不論。從理論上說,如果要讓經(jīng)驗性的“情”作為本體之“性”,由其歷史發(fā)生論和感性生存論上的優(yōu)先性推論出其價值尺度上的優(yōu)先性,那么也就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何過去的儒家思想家總是強調(diào)對“情”的克制而非放縱?如果這個問題不得到澄清,那么,當(dāng)代圍繞“情本體”展開的樂觀主義的審美道德啟蒙設(shè)計,也就將缺乏說服力。因此,我們有必要再度回到荀子和朱熹,思考他們的思想中哪些成分構(gòu)成現(xiàn)代情本體美學(xué)渴望吸收的理論資源,哪些成分又會始終和現(xiàn)代文化主流意見構(gòu)成不可調(diào)和的張力。
二、荀子、董仲舒情性—禮法論中的“圣人”維度
基于一種對萬物秩序的整全判斷,荀子相信,人之天性有同有異。人之“同求”和“同欲”——對應(yīng)孟子所說的“性善”——未嘗能夠推導(dǎo)出穩(wěn)定的政治結(jié)構(gòu),因為在成全情性、滿足欲求的過程里,人和人之間有著智愚高低的差別。如果任由自制力差的、私心重的愚昧之人縱欲無度,則會造成社會共同體失去規(guī)范性,走向人人相爭的危機局面: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shù)也。人倫并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群眾未縣也,群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荀子·富國》)?
基于這種實際的政治考量,荀子相信,“情性”是自然欲望的呈現(xiàn),與人之“惡”的“自然狀態(tài)”直接對應(yīng),這種“惡”是“不待學(xué)而知”(楊倞注語)?的先天稟賦。正是這種“性情”本身存在的“惡”或者說不足,使得良好的道德倫理訴求顯得尤為必要:
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愿厚,惡愿美,狹愿廣,貧愿富,賤愿貴,茍無之中者,必求于外。(《荀子·性惡》)?
關(guān)鍵在于,大多數(shù)人認識不到自己的情性存在著先天的不足,或是無法控制自己縱欲的自私?jīng)_動,進而無法祛除自然情性中的“惡”,走向人為的“善”;因此,荀子認為,應(yīng)當(dāng)由少數(shù)圣人“積思慮,習(xí)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這種工作和“陶人埏埴而生瓦”的制作技藝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由此,“情性”和“禮法”形成了一組范疇:情性是需要得到克服的人之自然身體屬性;社會化、政治化的“禮法”,則必須承擔(dān)“養(yǎng)情”的功能,讓自然情欲獲得外在的規(guī)勸,這樣一來,容易滑向“惡”的情性——其實質(zhì)應(yīng)當(dāng)是“樸”,作為尚未得到完善的先天狀態(tài),需要和禮法結(jié)合,在質(zhì)文互救的秩序里,生成良性政治生活秩序:
(禮)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fù)情以歸大一也。……兩情(吉兇憂愉之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禮論》)?
由此看到,荀子情性—禮法觀的重點在于,“禮”的制作者——圣人——是塑造萬民樸質(zhì)情性的首要動力。在由“質(zhì)”向“文”、由“情性”入“禮法”的教化秩序中,圣人憑借其對天地萬物的分辨知識,扮演著核心角色。那么,圣人是什么樣的人呢?
圣人與常人的區(qū)別,在于圣人有“伏術(shù)為學(xué),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的心志,如果能夠做到這點,則“涂之人可以為禹”;當(dāng)然,荀子深刻地指出,“未必然”能夠讓一切人都選擇積學(xué)為善的生活態(tài)度?。對于大多數(shù)人,這種“規(guī)范倫理”的基礎(chǔ)也不是孟子性善論中帶有主動積極意味的“德性”,而是帶有消極意味的外在教育—認識機制?。由圣人立法到“人類”的全體文明化,之間需要一個漫長而現(xiàn)實意味濃重的強制化、等級化的教化過程,與樂觀主義的“人類自身的自我教化”?有著根本差異。
荀子對常人之情性的現(xiàn)實判斷,引發(fā)了情性論問題域的第一道難關(guān):“美”或“善”是基于人之自然情性,還是立足于后天由圣人人為設(shè)立創(chuàng)制的標準?孟子會堅持人之自然屬性本善,荀子則只會用一段虛構(gòu)的對話,表達他對大多數(shù)人憑借自然情性自發(fā)趨近美善的悲觀態(tài)度,但同時,又強調(diào)某些“賢者”掙脫這個悲觀現(xiàn)狀的可能:
堯問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荀子·性惡》)?
情性嗜欲的放縱,會讓人遠離真正的美善;或許,唯有“賢者”能具有“美”的“情”——方向正確的“情”。荀子相信,這種正確的方向,來自對“分辨”之“知”的修習(xí),而“知”的心法,就在于“虛壹而靜”: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荀子·解蔽》)?
“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要求修習(xí)者暫時拋開既有的好壞得失判斷,進入客觀思考狀態(tài),顯得像是康德所說的“無功利”態(tài)度,也很類似現(xiàn)象學(xué)所說的“回到實事本身”;“兼知之”則體現(xiàn)出懸置個體主觀視角、以全景視角“壹”的態(tài)度把握真知的訴求,這種“靜”的心態(tài),類似西方哲學(xué)對“一”的整全理智直觀(nous),同時也是君子——“未得道而求道者”——擺脫身體情欲造就的偏離之知、憑借正確實踐理性通向善美目標的修習(xí)“心法”。圣人則是這種心法修習(xí)的終點狀態(tài),他們已經(jīng)徹底完成了“虛壹而靜”的修行,進而能夠與宇宙之整全知識相融契:
坐于室而見四海,處于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jīng)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荀子·解蔽》)?
“君子”則只是這種心法的“修煉中”狀態(tài),他們時刻保持自我規(guī)訓(xùn),整飭情性,但在智慧的境界上與圣人有本質(zhì)差異:
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dāng)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dāng)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dāng)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yīng)當(dāng)時之變?nèi)魯?shù)一二,行禮要節(jié)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圣人矣。(《荀子·儒效》)?
如廖名春所說,士與君子的特征在于“行”,而圣人的特性是一種極高的“知”和“明”——盡管前者嘗試以“行”來成為后者?。“君子”能夠在行動中修正自己的情性方向,但其思維并不周密,其關(guān)于人事與萬物的知識也并不整全。而“圣人”則透過“知”把握萬物之理,甚至是上升到“明”的絕對知識層面,進而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也同樣具有高超的辨識能力,把政治事務(wù)處理得有如順應(yīng)四時一般自然而然。由這種圣人通過極高智慧所設(shè)立的禮法,也就不同于一般的世俗約定,而是具有穩(wěn)定意義的“自然法”。賢人君子需要通過“學(xué)”的修身過程,在“行法”中不斷朝向圣人的境界邁進,以求最后達到知天地而立大法的境界。
這其實就是后世“知行合一”的君子賢人教養(yǎng)論所要傳達的義理。“知行合一”要達到的理想,則是“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對萬物之“情性”的正確辨識,和對自身情性的完全理性控制,則是這種理想境界的必要條件: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圣。……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所謂賢人者,行中規(guī)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所謂大圣者,知通乎大道,應(yīng)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于風(fēng)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圣矣。(《荀子·哀公》)?
君子雖“仁義在身”,在禮法的習(xí)俗慣性中生活,卻未嘗懂得更為精微的萬物本體之道,所以在面對突發(fā)的例外狀況時,難免“辭不爭”;賢人行事均中節(jié)而不離規(guī)矩,但同樣沒有把節(jié)度背后的理論基礎(chǔ)闡明的立場和訴求;“大圣”則在智性上達到極致,能夠給予萬物之情性以分判定位,發(fā)現(xiàn)其中的是非取舍之理。這種“理”貫通天地自然和人事百態(tài),百姓、君子乃至賢人卻幾乎不可能看透這種整全之“理”,這是荀子透過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視角洞察到的冷峻真理。思孟學(xué)派渴望讓“圣”本體論化為一種德性狀態(tài),并經(jīng)由《中庸》影響到宋儒的理學(xué)建構(gòu)。這種試圖把情性在智性層次上的不齊本相從現(xiàn)世政治狀況中抽象出來,并用普遍化的“德性”加以涵蓋修繕的態(tài)度,與荀子的現(xiàn)實主義冷峻視角可以說是大相徑庭。因此,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評思孟學(xué)派“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所謂“無類”,就是沒有區(qū)分人之內(nèi)在品性的差異。
“圣”能夠憑借極高智慧洞察萬物之整全,并為世間設(shè)立情性協(xié)調(diào)之法,是一種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高級境界,而不是一種常人天生具備的德性潛能。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與荀子這一洞識相比,現(xiàn)代美學(xué)試圖建立“情本體”,讓一切人的“潛能”在生活中“積淀”并通向“天人合一”,其實是要讓不同資質(zhì)與才分的人都憑借未加區(qū)分的日常生活審美實踐中的自我啟蒙,努力“成圣”。這種審美實踐,顯然不同于君子的“虛壹而靜”及其相應(yīng)的求學(xué)求知態(tài)度,而毋寧說只能與陶冶情趣維度的“樂教”相通,進而只能停留在李澤厚所謂“樂感文化”的層次。當(dāng)然,荀子也承認,多數(shù)人情性的治理要竅是“樂”,但是,圣王的“制禮作樂”,才是讓“樂感文化”真正成為社會基底的原因:
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fēng)易俗,故先王導(dǎo)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yīng)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荀子·樂論》)?
圣人對“樂”的制作,才是“樂教”的根基,也就是說,圣人對至高自然秩序的音樂性理解,是面向眾人的文教制度的出發(fā)點。如果沒有倚靠在圣人對自然秩序的洞識之上,禮樂也將失去其權(quán)威性。除非我們基于某種現(xiàn)代人類學(xué)的描述,相信民眾本身就有禮樂和同的天然美好情性。但是,這種樂觀的態(tài)度很難面對現(xiàn)實的拷問——何以在文明化的過程里,人性卻逐漸喪失了這種天然美好的情性呢?顯然,那種對人類最初的美好潛能的描述,或許只是一個盧梭式的“自然狀態(tài)”假設(shè)而已。
在《春秋繁露》集大成的儒家情性論體系里,對具有至高智慧的“圣王”的重視更為明顯——唯有經(jīng)圣王教化的人性,才可謂之最終的“善”;相較之下,所謂的自然之“善”,其實只是“禽獸之性”的質(zhì)樸起源狀態(tài),沒有受過圣王之教,這樣的“善”也就不成立;不存在萬民原初情性就盡善盡美的道理: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于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圣人之善也。……夫善于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于禽獸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圣。圣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圣人,圣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dāng)善。善之難當(dāng)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dāng)之,過矣。質(zhì)于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zhì)于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于禽獸者許之,圣人之所謂善者弗許,吾質(zhì)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zhì)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以善;吾上質(zhì)于圣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圣人過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性者,天質(zhì)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zhì),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zhì)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
即便有現(xiàn)代民主社會在“政治正確”上的“加持”,“情本體”的美學(xué)也很難回答傳統(tǒng)儒家提出的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問題:該由何種情性的人來體察天地自然之理、樹立道德尺度、制作禮樂教化,以陶冶人民的性情向善發(fā)展?對此,現(xiàn)代美學(xué)的回應(yīng)是:在歷史的積淀當(dāng)中,人本身會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成長,發(fā)育出成熟心智。歷史中的漫長實踐過程和經(jīng)驗傳承,能夠以文化陶冶的方式讓一切人實現(xiàn)自我完善,這種經(jīng)驗主義的“樂感文化”,會比由圣人所制作的禮樂更加可靠,因為其中彰顯的是多數(shù)人長期積累起來的經(jīng)驗智慧。基于歷史經(jīng)驗的審美經(jīng)驗,就此成了新的立法手段,而歷史中的每一個人,也就未必不能靠個體實踐中的經(jīng)驗積累和集體生活中的經(jīng)驗分享,達至和圣人同等的境界。但我們明白,這一朝向未知未來的“善良”推論,顯然至今未得到歷史經(jīng)驗的核實。經(jīng)驗知識的不斷積累,未必最終能夠推出盡善盡美境界的普遍實現(xiàn)。
儒家政治哲學(xué)并不懷疑“情”之于人性的自然實存意義,而十分重視對“情”的考察和看護?。只是,他們警惕“情”的放縱可能造成負面的倫理政治問題,所以設(shè)置出一個更高的智慧主體,憑借至高理性,對多數(shù)人的情欲加以節(jié)制。就此而論,儒家政治哲學(xué)和現(xiàn)代美學(xué)之間的實質(zhì)性張力,未嘗出于“禮法”和“情欲”這二者的沖突(盡管其最終表現(xiàn)形態(tài)看似如此),而是出于超拔于眾人的圣王智慧和人類全體歷史中所積累的經(jīng)驗知識二者對倫常世界立法權(quán)的爭奪。古典儒家政治哲學(xué)認為,高明圣人對自然—人事之整全道體的把握和分辨,是最值得信賴的大前提,“情本體”美學(xué)則相信,唯有多數(shù)人歷史—審美經(jīng)驗的積累,能給人性的自我啟蒙和社會的總體進步帶來穩(wěn)定動力。
三、從理學(xué)情性論到現(xiàn)代美學(xué)
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在傳統(tǒng)儒家情性論和“情本體”美學(xué)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中間,有著一段漫長的讓“圣人”這一立法主體逐漸抽象化、法則化的觀念運動過程。荀子的禮樂—情性論并不“玄學(xué)化”?,而是有著十分鮮明的務(wù)實特征。其施行圣人禮教,除了維持共同體的穩(wěn)定之外,還有著“節(jié)用裕民”?等現(xiàn)實關(guān)懷,其思想模式以實踐理性為主導(dǎo)。這一模式貫穿了整個秦漢時期。魏晉以降,隨著佛教思想的浸潤,抽象地談?wù)撉樾缘脑捳Z日益增多;儒家試圖通過重構(gòu)情性論,在與佛老諸家的論辯中找回優(yōu)勢地位,進而,“性與天道”這一過去少有人談?wù)摰脑掝}成為思想生產(chǎn)中的核心議題。從李翱《復(fù)性書》開始,一種關(guān)于性善情惡的本體論理論開始出現(xiàn),相信人可以憑借自身修習(xí)“由動向靜復(fù)歸,由現(xiàn)實向先天復(fù)歸”的“心法”也不斷涌現(xiàn),直到北宋理學(xué)強調(diào)“生而謂性”“性道一體”,“將善惡觀與天理論連接起來”?,一個抽象的先天之“理”及其相應(yīng)的道德修行,變成了理解情性問題的樞紐;《中庸》“修道之謂教”的君子修行法門,被擴大為士大夫自我整飭情性的“敬而致之”態(tài)度,二程所謂“內(nèi)圣外王”之法就此普及開來;而張載則認為,圣人的高度在于其能夠“盡性知天”,以至誠回歸至高天理,在“時”之中把握真正的普遍性?。
可以看到,在理學(xué)的語境里,“圣人”作為“體道”之人直接面向世間表述“道”,而非在把握“道”后回到現(xiàn)實政治差異環(huán)境中因材施教、以禮化民。理學(xué)中的這種形而上化的情性論和“體道化”的圣人論,在朱熹解周敦頤《太極圖說》時,體現(xiàn)得尤為顯著: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zhì)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于陰,神發(fā)于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圣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人皆分有“五常之性”,唯有圣人能夠“全體太極”,給予這種氣質(zhì)以規(guī)定的渠道,由此保證人之情欲不至于越軌。和荀子一樣,朱熹認為圣人的意義是探知太極之道,懸之以為法。但問題在于:太極之道和人事禮法之間,應(yīng)當(dāng)是何種邏輯關(guān)系?分殊之性始于太極,那么,要讓萬事之氣得到調(diào)整,是否必須首先本體到位,把太極之“理”徹底澄清,才能讓“法”獲得依據(jù)?如果說對于圣人是這樣,那么,圣人“全體太極”的致知之學(xué),又是否能為其他人所模仿?
吳飛認為此處并非在說“陽的原則是善與陰的原則是惡”,而是說“惡,更多是陰陽失調(diào)所致,陽過多與陰過多都會導(dǎo)致各種問題”,進而,在中國的思想譜系里,“由于身心之間不是西方式的二分,身體和身體的欲望都沒有遭到過多的否定”?。往前推一步,我們也可以說,荀、董以降儒學(xué)限制身體情欲的現(xiàn)實動機,或許也在這種原理化的“陰陽失調(diào)”的情性論解釋當(dāng)中失去了重心。正如徐復(fù)觀所說,荀子“不著重在‘生之所以然’的層次上論性”,盡管其亦有相關(guān)“所以然”的論述,但始終圍繞政治共同體中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來討論情性問題?,而甚少直接援引形而上“道體”來為現(xiàn)實立法策略辯護,這或許是“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上古共識。而理學(xué)在會通佛老之學(xué)后,則強調(diào)要以“自然只是一道”的態(tài)度來引導(dǎo)“形而下界”的世事經(jīng)綸:人之性情及其欲求計度,必須與形而上的“天地之氣”圓通為一理,“只要此情意計度合乎理,則此理便會發(fā)生作用與造作”?。圣人所立的“人極”基于“天理”,而“天理”則可以通過“修道”而企及。置身禮樂、陶冶情性的人間生存狀態(tài)的重心“圣人禮法”逐漸被更高位格的“天理”所凌越,通過“性”之修習(xí)通達“天理”的“我”則能自生自養(yǎng)其天然之性,使得“情”也在“道”的整全呈現(xiàn)中流溢為“中節(jié)”之用: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dāng)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jié)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dāng)行者而品節(jié)之,以為法于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圣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fā),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fā)皆中節(jié),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以這種理學(xué)情性論為代表,以圣人為中介制作禮法、合群辨稱的傳統(tǒng)儒家政治哲學(xué),轉(zhuǎn)化為了讓天下人直接面對天理道體進行自我修繕的道德形而上學(xué)。用汪暉的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內(nèi)在化”道路?。相較于荀子、董仲舒的思想,理學(xué)家所設(shè)計的面向士人階層的“致學(xué)”目標,不再敬守賢人—君子—士—民之“分”,而更多要求一切人都嘗試透過心性工夫的修養(yǎng)而“成圣”。張載就曾直言不諱攻擊上古儒家在“成圣”問題上的拘謹:“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圣人,此秦漢以來學(xué)者之大蔽也。”朱熹則進一步消解圣人和常人在本來稟性上的差異:“凡人須以圣賢為己任。世人多以圣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然圣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賢為己任。”?
相比荀子“虛壹而靜”所要求的純粹知性狀態(tài),在由常人向圣人進發(fā)的心性修養(yǎng)工夫論視域里,人之七情六欲開始占據(jù)更加復(fù)雜的地位,以至于有人認為在朱熹的學(xué)說中,“情感居于核心地位……以性為心之本體,但真正體現(xiàn)性的,是情而不是知……情才是存在本身”,所謂“心兼性情”的體用二分,實則落實了“情感在心靈中的地位與作用”?。這恰恰也是現(xiàn)代美學(xué)的出發(fā)點——讓變動不居的情感本體化,成為在世生存的依托。這也就是李澤厚強調(diào)朱熹思想意義的原因。
的確,理學(xué)的“工夫論”具有開出過程哲學(xué)的潛能,與審美積淀論有契合之處:
“工夫”只不過是扮演信任內(nèi)在的“理”、推動“理”、并促進其活化的角色……理學(xué)之“工夫”……不是單純的“意識性”行為;而是以“自然”為志向的“意識性”行為……若“工夫”被賦予達成使“理”顯現(xiàn)的此一目的,則“工夫”必然會面臨自我消滅的命運。?
理學(xué)傳統(tǒng)強調(diào)的修持情性并通向“圣人”的“工夫”,也可能在現(xiàn)代語境里被闡釋為一種讓自然之理進入自身、并推動生命實現(xiàn)其潛能的歷史哲學(xué)——其最終目的“成圣”也就和審美積淀論中試圖實現(xiàn)的“天人合一”發(fā)生了意義拼貼。宋儒的情性修養(yǎng)工夫論及其把天理視為“歷史事件”展開過程的觀念?,讓傳統(tǒng)儒家情性論發(fā)生裂變、并最終延異出“情本體”現(xiàn)代美學(xué)的思想轉(zhuǎn)折獲得了一種理論依據(jù)。朱熹不再重視具有極高智慧的“圣王”的制作權(quán)威,把禮樂文藝的確定性和正當(dāng)性交托給“天理”之下的觀念化之“義”,并讓私人情欲在這一概念的符號之下獲得一種靈活變通的合法性?,這是一種理性化、法則化的態(tài)度,為現(xiàn)代個體的感性生存基礎(chǔ)提供了“隔代遺傳”的基因。只是,朱熹對“天理”的判定中還存在某種超自然的神秘特征,亦即李澤厚所謂的“宗教”因素,這種特征使得理學(xué)實踐的范圍集中在士大夫階層,民眾只需被士大夫的道德氣質(zhì)“感化”,而不需加入到“工夫”的踐行中。試圖體現(xiàn)“人”之價值的現(xiàn)代啟蒙美學(xué),則必須對此加以揚棄。
中國現(xiàn)代美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王國維在評述荀子情性論時,曾以懷疑主義態(tài)度,對“圣人”提出疑問:
……其說之矛盾,其最顯著者,區(qū)別人與圣人為二是也。且夫圣人獨非人也歟哉!常人待圣人出禮義興,而后出于治,合于善,則夫最初之圣人,即制作禮義者,又安所待歟?……胡不曰“人惡其亂也,故作禮義以分治”,而必曰“先王”何哉?
在我們今天的語境里,這一追問顯得格外“自然而然”。在現(xiàn)代“正當(dāng)?shù)纳鐣W(xué)”視野之下,“圣人”的設(shè)定顯得像是“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是一個非必要的偶然因素。甚至有人會擔(dān)心,一旦引入這個因素,作為現(xiàn)代民主生活尺度的“普遍”與“穩(wěn)定”就必然遭到破壞。
的確,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中,很難找回荀子訴諸“圣人”的政治語境。即便出現(xiàn)了真正的“圣人”,也未必能夠在當(dāng)今時代獲得什么權(quán)威。但至少,儒學(xué)節(jié)情修性的基本態(tài)度及其對人性本質(zhì)差異的現(xiàn)實洞察,依然具有現(xiàn)實解釋方面的活力。哪怕是朝向“天理”,也依然有常人“主敬”和士人“主靜”的不同態(tài)度。而“仁”在形而上與形而下維度之間徘徊的曖昧特征,恰恰也使得對天地之理的客觀認識和對人間紛繁情性的調(diào)節(jié)實踐,二者之間維持著某種貫通未斷的理論氣脈,“圣人”之智性觀物和仁德立法的一體性,則是這一氣脈未斷的首要樞紐。
問題是,一旦圣人與常人的客觀之分不再得到承認,承擔(dān)“仁”的“禮法”和“天理”就會變成失去特殊身體性的抽象的形式主義法理,看似具有了某種普遍性,卻無法對常人的情感進行權(quán)威的秩序化調(diào)整,道德倫理生活也將陷入混亂的危機。尤其是近代以來,視“物”為“理”的儒學(xué)天理觀在視“理”為“物”的“世界公理”面前,必然會淪為不切實際的“宗教”或“神話”。如此,儒學(xué)情性論不再有效,其形而上維度被迫讓渡給密切關(guān)注“物”及其“時勢”的現(xiàn)代歷史哲學(xué),自身則只剩下庸俗倫理道德教條的一面,成為被激進文化運動輕松掃蕩的“孔家店”存貨。
從儒家政治哲學(xué)到現(xiàn)代美學(xué)的古今之變軌跡中,可以看出,民眾地位的上升,是導(dǎo)致哲學(xué)情性論發(fā)生重心轉(zhuǎn)向的核心因素。與荀子和朱子相比,現(xiàn)代“情本體”的最大特征就是其應(yīng)和現(xiàn)代民主自由生活的訴求。莊士敦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在一個民主制國家里,不存在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樂和禮’的立足之地,而且與禮樂相關(guān)的那些古代中國的神秘思想在一個進步的現(xiàn)代國家里會成為人們的笑柄。”的確,正是現(xiàn)代民主的基本信念,讓關(guān)于“圣王禮樂”的信念變成明日黃花;帶有神秘體驗性質(zhì)的“工夫論”,今天也有遭逢“去魅”的危險。正統(tǒng)儒學(xué)如果不經(jīng)歷一番“情本體”的美學(xué)改造,或許會就此失去其現(xiàn)實生命力。但我們也可以嘗試回到荀子的現(xiàn)實主義眼光,審視如今的審美民主化、生活化道路,思考其是否有過于樂觀且天真的內(nèi)在缺憾。
①③?????????????? 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17頁,第487、506—507頁,第207—208頁,第517頁,第519頁,第517—522頁,第419—420、432—433頁,第524頁,第525頁,第467—468頁,第469頁,第154—157頁,第635—640頁,第110—111頁,第450頁,第209—212頁。
②? 余開亮:《先秦儒道心性論美學(xué)》,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第129頁。
④? 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3頁,第150—155頁。
⑤? 陳昭瑛:《荀子的美學(xué)》,(臺灣)臺灣大學(xué)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頁,第226—227頁。
⑥ 陳來:《從思想世界到歷史世界》,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26頁。
⑦? 董天工箋注、黃江軍整理《春秋繁露箋注》,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150頁,第147—152頁。
⑧??? 李澤厚:《哲學(xué)綱要》,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26—233頁,第158、384頁,第368頁,第51—68頁。
⑨⑩ 呂祖謙撰、嚴佐之導(dǎo)讀《朱子近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第31頁。
? 康德:《實用人類學(xué)》,李秋零譯,李秋零主編《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114、115頁。
??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248頁,第253頁。
?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xué)——為〈倫理學(xué)綱要〉一辯》,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
? 馬育良:《中國性情論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9、145—152頁。
?林桂榛:《天道天行與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與天道”論考原》,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頁。
?向世陵:《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xué)的分系與四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44頁。
? 楊立華:《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xué)述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92—104頁。
? 朱熹:《太極圖說·解附》,《周敦頤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頁。句讀略有改動。
?吳飛:《論“生生”——兼與丁耘先生商榷》,載《哲學(xué)研究》2018年第1期。
? 徐復(fù)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203—204頁。
? 錢穆:《朱子學(xué)提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第45頁。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18頁。
?本段張載、朱熹引文,均轉(zhuǎn)引自藤井倫明《朱熹思想結(jié)構(gòu)探索——以“理”為考察中心》,(臺灣)臺灣大學(xué)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40—41頁。
? 蒙培元:《朱熹哲學(xué)十論》,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14頁。
?藤井倫明:《朱熹思想結(jié)構(gòu)探索——以“理”為考察中心》,第51—54頁。
? 趙金剛:《朱熹的歷史觀:天理視域下的歷史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版,第275—2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