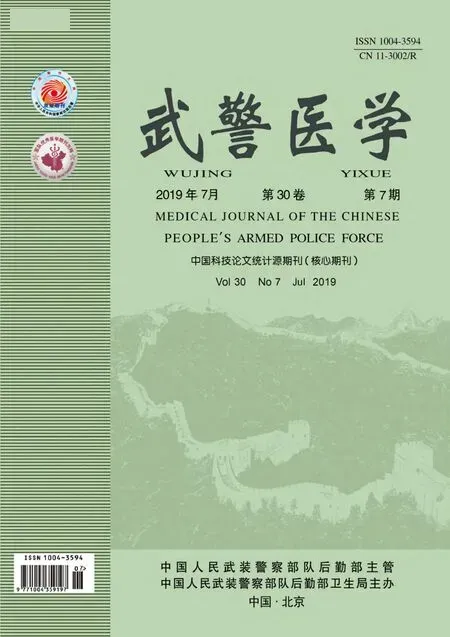創傷性腦損傷基礎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程世翔
創傷是指機械力能量傳導至人體后造成機體結構完整性破壞的損傷,其中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亦稱為顱腦創傷)在神經外科學和創傷外科學中均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已成為全球青壯年致死、致殘的主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急救醫學及危重癥監護技術的迅速發展,各項救治指南的相繼出臺和完善,極大促進了TBI臨床救治水平的全面提高,救治成功率大幅提升,TBI總體病死率已由50%降至30%,其病理機制和神經再生修復的基礎研究也取得可喜成果,為臨床救治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然而,TBI病死率仍高居各類創傷之首,其中重型TBI(severe TBI,sTBI)患者仍有30%病死率,10%輕型TBI患者會遺留永久性神經功能障礙。此外,我國TBI基礎研究與發達國家比較嚴重滯后和不足,國內各地區由于經濟發展和醫療水平差異明顯,臨床救治水平也參差不齊。基于此,筆者就TBI最新流行病學特點、國內外救治指南進展和基礎研究現狀進行介紹,并對研究熱點和研究新方向加以展望,以期提高我國TBI救治水平。
1 流行病學特點
2016年全球新增TBI 2700萬人,發生率為369/10萬(比前30年增長3.6%),致殘率為111/10萬,主要致傷原因是墜落傷和交通傷[1]。全球不同地區TBI發生率差異顯著,高發生率地區主要位于中歐(857/10萬)、東歐(772/10萬)和中亞(495/10萬)。2016年我國TBI發生率為313/10萬,與美國(333/10萬)、日本(263/10萬)等國家相比差別不大,但與過去30年比較上升達33.1%,主要是由于交通事故傷(占比53.0%)和墜落傷(占比28.6%)所致[2]。
2 臨床救治指南和專家共識
近十余年來,各國神經外科醫師和科研人員對TBI的病理生理進程和臨床救治方案進行持續探索,陸續頒布和完善了一系列救治指南和規范,主要包括:2007年美國sTBI救治指南(第三版)[3]、2012年日本sTBI救治指南[4]、2012年美國輕型TBI救治指南[5]、2017年美國sTBI救治指南(第四版)[6],以及2018年美國兒童輕型TBI診斷治療指南[7]。該系列指南逐步健全了全球TBI臨床規范化診治體系。在此期間,我國學者和臨床醫療工作者也積極開展了結合我國TBI特點的臨床規范化救治技術,陸續于2008年發布《中國顱腦創傷病人腦保護藥物治療指南》以指導合理應用腦保護藥物[8],2009年發布《中國顱腦創傷外科手術指南》以規范手術方式[9],2010年發布《神經外科危重昏迷患者腸內營養專家共識》以指導腸內營養支持[10],以及2011-2015年發布的《中國顱腦創傷顱內壓監測專家共識》《顱腦創傷去骨瓣減壓術中國專家共識》和《顱腦創傷長期昏迷診治中國專家共識》[11-13],使我國TBI救治取得了長足進展。隨著救治指南的不斷修訂,不同版本的救治標準也不盡相同,這充分表明TBI診治的復雜性,我們只有對最新指南進行充分理解和合理應用才能有效地指導臨床工作。
3 研究熱點與發展方向
基礎研究是開展臨床工作的試金石或是風向標,臨床工作的不斷進步與完善離不開相關基礎研究提供的理論和實驗證據,因此了解TBI基礎理論研究熱點和動態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國內外在腦科學尤其是TBI研究領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研究方向涉及模式動物TBI模型建立、病理學分析、細胞與代謝變化、基因及其基因組學改變、蛋白質及其蛋白質組學改變等多個方面,期盼能獲得可喜的成果,開拓TBI的研究新思路。
3.1 基于體液生物標志物的TBI診斷和治療新靶點研究 臨床上診斷TBI嚴重程度和預后指標主要包括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CS)、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OS)及臨床癥狀等,然而這些指標的評價標準相對簡單,與患者自身情況并不完全相符,主觀判斷會造成診斷的偏倚,而生物標志物的研究是對客觀評價TBI的重要補充方式[14]。目前TBI體液生物標志物的樣本類型主要包括:(1)腦脊液,可直接反映腦內生化改變,但獲得途徑為腰大池引流或腦室外引流,屬于有創檢測;(2)血液,優點在于較腦脊液更易于獲取,但存在濃度較低、受高豐度蛋白干擾、中樞神經系統(CNS)特異性低等缺點;(3)其他體液(唾液、尿液、淚液等),有研究指出,部分CNS來源的蛋白(例如,神經突觸核蛋白-α)可能最終分泌入唾液[15],但濃度與TBI病理生理進程的關聯性及其具體機制還知之甚少。
目前已知的某些生物標志物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TBI患者損傷程度及預后康復等情況,例如:S100β和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可評估sTBI患者預后,但對輕型TBI預后的特異性和敏感性不高[16];TBI后膠質纖維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水平的升高與顱內壓增高、GOS評分低、腦灌注減少等相關[17];髓磷脂堿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MBP)、Tau蛋白等血清學指標均在TBI的動物及臨床實驗中被研究,對預后的判斷也有一定指導意義[18, 19]。然而,上述生物標志物均為針對某一類神經細胞(神經元、神經軸突、少突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等)損傷或TBI的某一種病理生理進程(血腦屏障通透性破壞、神經炎性反應等),目前尚無任何一個體液生物標志物被很好地應用于臨床,依然缺乏大規模、系統化的研究與驗證。
3.2 基于炎性反應和可控性壞死的TBI致傷新機制研究 TBI急性期CNS經歷了一系列重要的分子事件,其中神經炎性反應是繼發性腦損傷病理改變中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既往研究認為TBI后受損腦組織通過釋放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等炎性因子加重神經細胞繼發性損傷,而TBI患者腦內小膠質細胞通過表達C-C趨化因子(C-C chemokine)募集外周循環中的炎性細胞,后者通過受損的血腦屏障入腦參與TBI后的炎性反應,加重神經功能損傷。然而,最近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炎性反應在促進神經修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闡明和揭示TBI后炎性反應的具體分子機制對臨床診斷、預后評判及治療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研究表明,TBI通過激活細胞死亡信號通路,加劇神經細胞死亡、炎性反應和神經功能損害。如何減少細胞死亡進而保留更多的神經元,以獲得更好的神經功能預后是TBI的研究重點之一。傳統觀念認為,細胞凋亡是調控細胞死亡的主要方式,細胞壞死不可被調控。然而,可控性壞死及其調控通路的發現和確認,為逆轉細胞死亡開創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潛在的治療途徑。近期研究發現,可控性壞死是TBI早期細胞死亡的主要形式,具有可逆轉、能延遲的特性,能夠擴大TBI治療時間窗,其中受體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3,RIP3)是調控炎性反應和可控性壞死的關鍵蛋白,通過RIP3/TNF-α信號通路募集下游底物MLKL并使其磷酸化,破壞細胞膜完整性,導致細胞膜破裂和炎性反應[21]。TBI后24 h內給予RIP3特異性阻滯劑Nec-1干預可明顯降低TBI小鼠壞死細胞數目,發揮明確的神經保護作用[22],但可控性壞死和炎性反應的相互作用關系目前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深入研究可控性壞死的分子調控機制,有望為TBI治療提供更多的潛在新靶點。
3.3 基于定量蛋白質組學的TBI檢測新技術研究 自人類基因圖譜繪制完成后,生命科學的研究進入后基因組時代,其中定量蛋白質組學技術以其高通量、高覆蓋和高精度特性成為蛋白功能研究的利器。在此基礎上利用生物信息學技術系統發現某種疾病中改變或失調的信號通路,可闡釋該疾病發生發展的分子機制。由于CNS的復雜性導致其系統性研究受到很大阻礙,而包括蛋白質組在內的多種組學技術正在快速推進神經科學研究相關領域的發展[23]。在TBI研究中,通過應用同位素標記相對和絕對定量(iTRAQ)結合質譜定量策略能夠對受損細胞或組織蛋白進行精確定量,重塑TBI激活腦內分子的全景細胞網絡,并結合表型變化趨勢,驗證關鍵調控因子和效應分子的表達豐度變化[24]。然而目前,該技術多應用于TBI細胞模型和動物模型中,但隨著該技術在神經科學領域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后續蛋白質組學技術有很大機會被應用于臨床研究,預計該新技術方法必將加速生物標志物的發現和篩選,也會在TBI嚴重程度分類及臨床精準治療方面提供支持。
4 總結與展望
TBI后腦組織和神經細胞經歷缺氧、氧化應激、炎性反應、細胞凋亡、組織壞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及其潛在的分子機制形成了一個復雜而有序的網絡。以往的基礎研究對TBI病理生理進程有了更加深入地認識,但目前對TBI的臨床治療貢獻仍然十分有限。今后的基礎研究應更多向臨床轉化邁進,并且能夠以整體觀來分析和解決TBI發生、發展及預后問題,更為全面深入地研究TBI后神經細胞壞死、氧化應激損傷、線粒體損傷、生物標志物等諸多問題,同時也要重視干細胞的基礎與應用研究。相信在未來,基礎研究的成果能夠更加有效地指導和提高TBI臨床救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