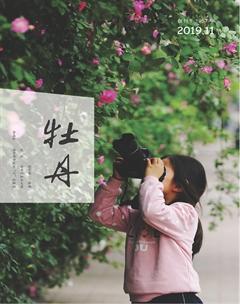簡論先鋒電影類型之記錄電影
本文所論述的記錄電影實際上被稱為“先鋒紀錄片”,既然是“先鋒”,就應區別于一般的、通常意義上的紀錄片。這種區別主要是美學上的。具體來說,凡是紀錄片都要求客觀地記錄現實生活,但先鋒紀錄片更強調一種生活的“陌生化”處理。他們從日常生活或常見的自然景象中收集素材,再通過蒙太奇手法將其重新組合,展現在人們眼前的現實世界似乎變了一個樣,變得富有詩意。不同于一般紀錄片注重內容的傳達,先鋒紀錄片將重心移向對形式的探索,這也是所有先鋒派類型的共同追求。電影眼睛派作為先鋒派類型之一,就有著對鏡頭角度和運動的多方位運用。而在藝術語言上,先鋒紀錄片尤其是“城市交響樂”,特別強調音樂的節奏與畫面的配合,其作品大多像是一場“視覺音樂會”。
一、“城市交響樂”
一些電影創作者把他們的攝影機帶到戶外,捕捉城市景觀中充滿詩意的一面。他們的電影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城市交響曲”。
這一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紀錄電影流派,也被稱為“第三先鋒派”。與之前的其他先鋒派電影相似的是,它們也否定電影的敘事性。有所區別的是,它們以更加符合電影手段的精神面對可見的物質現實世界。該流派電影的特點包括:情節一般發生在較短的時間內(通常是一天之內);內容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方面,包括社會各階層的日常活動(如工作、餐飲、娛樂生活等);通常通過造型美、音樂美和節奏美使電影產生意義。“第三先鋒派”雖然未能完全脫離早期先鋒派電影的影響,但是它把先鋒派電影拉回到了現實主義創作道路。
1926年,在法國工作的巴西導演阿爾貝托·卡瓦爾康蒂(Alberto Cavalcanti)拍攝了一部名為《只有時間》(Rien que les heures)的電影,成為“城市交響樂”電影在歐洲拉開帷幕的標志。這部充滿詩意的紀錄片展現了巴黎這座城市從黎明到黃昏一天的生活,有美好的一面,也有破敗的一面,有富人,也有窮人,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是再普通不過的城市生活:商店老板開門,人們在咖啡店喝咖啡聊天;惡棍打死了一個女人,老婦人蹣跚著踱過街道,等等。這一系列沒有任何關聯的情節被編織在一起,沒有別的,只有時間的流逝。
“城市交響樂”電影的另一部杰作是由讓·維果(Jean Vigo)導演,維爾托夫的弟弟鮑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擔任攝影的影片《尼斯印象》(? propos de Nice),主要表現的是法國南部海濱城市尼斯一年一度的狂歡節景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對于富人們和老城區窮人們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的尖銳對比。法國電影史家薩杜爾指出,這部電影既有布努艾爾式的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也有維爾托夫理論的影響。例如,影片中表現一位闊太太坐在海濱涼椅上的場景,她身上的服裝從薄裙、套裝、連衣裙直到裸體,在不斷地變化。像這種大膽使用蒙太奇的超現實主義場景還有擦鞋工人為游客擦鞋的鏡頭突然變為擦一只光腳。應該說,這是一部獨具社會意義的紀錄電影,讓·維果在影片中表達了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因此也被看作是“觀點紀錄片”的一個簡單雛形。
電影作為當時最為前衛的一種大眾媒介,城市作為工業文明的依托體,“城市交響樂”成為二者相碰撞的產物。這類描寫和紀錄普通城市生活的電影,實際上表現出城市的現代生活節奏。火車和汽車不停轉動的輪子、運轉的機器等科技的成果的展現、現代人越來越匆忙的腳步等,匯成了一曲速度、節奏與運動的交響樂。
“城市交響樂”電影在20世紀30年代建立了基本模型,也創造了美學高峰,記錄了人類城市生活的心理圖景。當鋼筋混凝土與大塊玻璃編織著人們每一天的風景,當鐘表兢兢業業地每日提醒著人們上班下班的時間,這種曾經激動人心的藝術樣式在時間的流動中漸漸沉沒。
二、電影眼睛派
1929年,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的上映電影《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在開片的字幕宣稱:這部影片致力于創造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性的電影語言,與戲劇和文學完全分離開來的絕對的電影語言。這種語言就是“攝影機眼睛”。這部影片的所有鏡頭都是在強調“看”這一行為的連續性,如將攝影機的鏡頭和人眼疊印在一起,充滿了隱喻意味。
20世紀20年代早期,維爾托夫就已經開始宣傳他的“電影眼”(cine-eye)理論了,他認為并不完美的肉眼應該讓位于更具有優越記錄能力的攝影機鏡頭。具體地說,他認為攝影機就像人的眼睛一樣能把看到的世界呈現在銀幕上。但攝影機又遠遠勝過人的肉眼,因為“電影時空的靈活性使它不僅能紀錄客觀世界,同時還能通過復雜的剪輯手法描寫和表現主觀印象”。因此,維爾托夫把故事片看作“電影鴉片”(cine-nicotine),他認為故事片是虛偽的,不真實的,會削弱觀眾對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認識。凡是劇情片拍攝所需要的人為扮演、化妝造型、布光照明、搭棚布景等手段,維爾托夫都極力地反對。但他卻提倡用蒙太奇的手法來進行剪輯,將拍得的來自生活的原始素材通過蒙太奇的重新組合達到某種藝術的真實,從而獲得藝術感染力。1922年,維爾托夫成立了《電影真理報》(Kino-Pravda),開始將他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life caught unawares)成為他的座右銘,甚至是影像的基礎。
三、逼真性——是技術主義還是寫實主義?
紀錄片的最大特點應該是紀實性,即逼真地反映生活。然而先鋒紀錄電影在要求攝影機真實記錄生活的同時又大力倡導蒙太奇技術的使用,這不免讓筆者提出疑問。
著名電影理論家邵牧君認為,在西方形形色色的電影流派中,可根據美學本質將其歸結為技術主義和寫實主義兩大派,他們互相對立,又互相補充。前者以蒙太奇理論為基礎,后者的理論基礎則是場面調度。
可以說,先鋒紀錄片的本質是詩意。這不僅僅與先鋒紀錄片導演們的內在特質密切相關,例如,讓·維果被稱作“電影界的蘭波”,伊文思被譽為“先鋒電影詩人”,也離不開獨特的拍攝手法和蒙太奇的運用。在《持攝影機的人》中,不尋常的拍攝視角往往帶來視覺驚喜。例如,將攝影機放在鐵軌下,觀眾就看到了火車像是從頭頂駛過的畫面。停機再拍的簡單技巧則讓觀眾看到電影院里的椅子竟“活”了起來,可以自己折疊、打開。后期剪輯更是具有改變平常世界的神奇力量。例如,逆動技術讓跳水者從水里又返回至高臺。
先鋒記錄電影將記錄手段和蒙太奇手法相結合,旨在制造日常生活的幻覺。生活本身是真實的,人們對待生活的態度可以是詩意的或批判的。紀錄片不一定就是機械地對現實生活的客觀記錄,它還可以發揮藝術家的主觀能動性。這不僅是藝術的美學,更是生活的美學。
(四川電影電視學院)
作者簡介:萬雨潔(1990-),女,四川樂山人,碩士,研究方向:戲劇影視、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