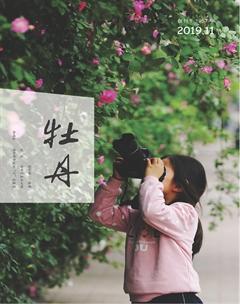因情而俠:“情俠”與“俠”的區別
俞思媛
馮夢龍輯錄《情史》,列卷四為“情俠類”。因為與中國傳統俠文化所體現的精神氣質有著高度的吻合,所以屬于俠類文化;馮氏命之為“情俠”,是因為此類俠者行事為人皆出于情,即“因情而俠”,由此可見馮氏的情俠觀:肯定、贊美情與俠,尤其強調情對俠的重要影響。
《情史》中情俠的一般特點,諸如勇敢追求、突破禮法、放誕風流、成人之美、知恩圖報等,都與中國傳統俠文化高度契合。但兩者的本質是否契合,還需要認真梳理,厘清俠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含義,從而歸納其精神特質。
一、傳統俠文化之“俠”
俠:俜也。從人夾聲。胡頰切。(《說文》)
甹:亟詞也。從丂從由,或曰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甹。(《說文·丂部》)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有俠者官職曠也。(《韓非子》)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韓非子》)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韓非子》)
從歷史上看,俠最初表現為一種“私劍”模式,這是由先秦時期韓非子所提出來的。戰國時期的俠,是脫離宗法軍隊之外,散布于豪門卿士的食客。他們是身份相對自由的武士,受到社會的贊美。韓非子也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認為應該“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可見游俠在當時大動蕩的社會中是很重要的社會力量。然而自漢景帝始,開始誅殺豪俠,俠就不再是社會的主流了。《漢書·敘傳(下)》記載:“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臺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漢書》學習《史記》體例設有《游俠傳》,但從《后漢書》起,史書便不再為游俠列傳了。
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很具體地描述了游俠所具有的的品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心中的俠者形象,是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的俠者,這在司馬遷的《史記·游俠列傳》與《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是顯而易見的。《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游俠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他贊賞誠信踐諾、伸張正義、重義輕財、追求自由的美好品質。在此,俠與義已經較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司馬遷對俠的評價標準是建立在義上的。
歷史上的游俠被統治者大力打壓之后,活躍于詩人與作家心中的俠逐漸成為我們常見的藝術形象。學者陳平原認為,哪怕如司馬遷這樣卓越的史學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也難免在《史記》中注入自己的主觀想法。因此,當描述俠客的任務落到文人作家手中時,俠這一形象所帶有的主觀色彩必然大大增強。也因此,有學者說道:“隨著時代的推移,俠的觀念越來越脫離其初創階段的歷史具體性,而演變成一種精神、氣質。”唐代詩人創作了大量俠客形象,表現出了瀟灑不羈、叱咤風云的特點。比如李白《白馬篇》:“殺人如翦草,劇孟同游遨。”之后,唐傳奇、明清小說,到后世的武俠小說,俠的形象越發鮮明。尤其在武俠小說中,俠文化進一步發展,具備了道德追求,諸如郭靖、喬峰等都具有深刻的家國情懷。
梳理了俠文化的發展過程與其在歷史上的含義演變,依然很難對“俠”做出精確的定義,但從中概括出俠的精神特質,卻是可以嘗試的。另外,想要全面地把握俠的精神,“游”的精神也應當被考慮在內。《史記集解序》司馬貞索隱:“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學者王學泰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也十分強調“游民”之“游”,指的是脫離當時社會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們;而“游俠”之“游”,是出于游俠自身的個人選擇,一方面表現為對抗現行體制的勇氣,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報國之志。縱觀以上,筆者認為,俠的精神特質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對自身來說,其追求自由、敢于反抗、放誕不羈;二是對他人來說,其誠實守信、重義輕利。
二、“情俠”:因情而俠
“情俠”的一般特點與俠的精神特質是高度吻合的。但“情俠”與俠在主角分布、行為模式、行為出發點方面又存在很大區別,“情”是“情俠”的核心。
(一)主角分布
《情史》中“情俠類”的主人公們,從階級分布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包括了唐玄宗、僖宗等君主,也有袁盎、葛周、裴晉公、寧王憲、李紳等文官或將軍;相比之下,更為出彩的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如馮蝶翠、邵金寶、瑞卿等身份卑微的妓女,還有已為人妻或妾的戴綸妻、沈小霞妾等。
從性別分布看,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而且女性的形象更為突出耀眼。如果不是《情史》,我們很難想象身居正統的帝王、官僚,會成為江湖上才有的俠;也很難想象,一個個地位低下的柔弱女子,能夠在俠的世界里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所以,“情俠”者的分布遍及社會各個階層,也無所謂性別,相比于“武俠”或是歷史上的“游俠”,都是值得人們注意的一點。
(二)行為模式
《情史》“情俠類”所記敘的情俠者,脫離了“武”這一硬性條件。不管是高高在上、擁有軍隊的帝王將相,還是普普通通、手無縛雞之力的平民百姓,他們在故事中大多都沒有使用武力。誠然,故事中昆侖奴武藝高強,其在幫助家主的時候運用了她高超的武藝,但卻不并引起對方激烈的對抗。雙方對抗被輕巧略過,只有昆侖奴勝出的結局。武藝使她神秘,也是她成人之美的重要條件,但武藝卻始終不是故事的核心。與之類似,在感恩回報的故事類型中,也有個別主人公,比如葛周的幕下之臣甲,他有高超的軍事才能,大破敵軍之陣,但其軍事才能也不是故事所描述的重點。甲之所以為俠,不是因為其“武”,而是因為他憑借“武”完成了對有恩于他的將軍的回報。總而言之,“情俠”為人處世,皆用平常行為,一言一行便足夠,無需用武力來解決矛盾。
(三)行為出發點
《情史》中的“情俠”者,一切行為皆為情所激,為情而發。這一點,是“情俠”區別于一般俠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點。情首先是愛情。在相悅而助的這一類情俠中,不難看出女主人公對男主人公的愛情。因為對愛情的渴望與追求,她們獲得了打破世俗禮法、追求自由愛情的勇氣,而這一行為,卻完全不需要武力,只是一餐一飯、一朝一夕的相伴。“情俠”者成人之美,也是有感于他人的純真愛情。一般的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所見不平顯然有很多,其拔刀相助的方式或多或少要借助武力。但“情俠”成人之美,是懷著對他人愛情的感知與美好祝福,默默成全。他們所不平的,顯然更有針對性,也更動情,才能做到成人之美。但情的含義也可以有所延伸。感恩回報的“情俠”,是因為對方包容、成全了自己的愛情而產生了感恩之情,因而以一腔熱血,真誠地回報。可以說,故事的出發點依然是愛情,但這番“情”最終會發展為主仆之情、君臣之情。
三、結語
“情俠”區別于一般之俠,這也是馮夢龍獨創一個有情江湖的原因。在這個世界里,“情俠”有著他們獨特的行為原則——情。一切因情,一切為情,“情俠”圍繞情表現出了不同的行為模式,而達成俠的主要手段,則是“助”與“報”。
馮夢龍在《情史》“情俠類”所描繪的這個有情的世界,直到如今,依然令人神往。他贊美情,把一切有情的、為情而激發的普通個體,都稱之為“俠”,可見在馮夢龍心中,情是為人處世的核心原則。他認為,情是具有感化功能的,“無情化有,私情化公”。至于俠,是保證情得以延續的手段,與“武”卻沒有必然的聯系。并且,俠也是情的必然結果,因為情的激發與振奮,人人皆可成為俠,成為值得書寫的主體。
(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