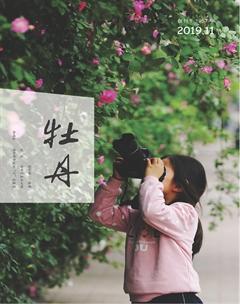論白居易詩中的女性觀
高婷
詩人白居易(772-846年)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時期。作為唐朝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對社會各階層的女性給予了較為廣泛的關注。白居易創作的2800余首詩歌中,有170余首是以女性題材為主,是中國古代對女性命運關注最多的詩人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對女性同情、憐憫、欣賞的態度構成了其鮮明而進步的女性觀,對后世影響深遠。
女性形象是古代文學創作中重要的部分,貫穿整個文學史發展歷程。在白居易多達170余首女性題材的詩中,根據描寫內容、人物形象的不同,可以把白居易詩歌中的女性形象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以楊貴妃、王昭君為代表的宮廷女性,第二類是以織女、農婦為代表的普通勞動婦女,第三類是以妻子女兒、初戀湘靈為代表的內心情感世界中的女性;第四類是后期著力渲染的女妓、女尼、女冠等。本文基于這四類女性形象,對白居易的女性觀作出探討。
一、早期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女性觀
白居易早期的女性觀有著深深的儒家思想烙印。在其女性詩文上,既有“女禍論”的思想,又有涉及勞動女性生存之苦、關注宮廷女子生存命運的問題,對儒家倫理綱常規范下的女性之責,表現出同情、憐愛的態度,有著進步的女性觀。
唐人就有對女性禍國的看法,后人亦多論及唐代女性禍國事,如趙翼云:
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后稱制命,殺唐子孫幾盡,中冓之丑,千載指為笑端。韋后繼之,穢聲流聞,并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橋,以傾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弒中宗。宮闈之禍,至此而極。
李唐王室相續綿延的“女禍”,引發了唐代文人的關注。“女禍論”成為中晚唐輿論的興奮點。與大多數中晚唐詩人群體一樣,白居易的女性觀也難逃“女禍論”的范疇。在遵循儒家傳統女性觀的基礎上,又常常游離于情感和理性之間,呈現出矛盾而多元的特點。以楊貴妃為例,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年)作《長恨歌》。關于這首詩的創作緣起,可在白居易摯友陳鴻的《長恨歌傳》里管窺一二: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任,鴻與瑯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
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
由此可見,白居易創作《長恨歌》的初衷是“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存在一定的女禍論思想。然而隨著李楊愛情故事的展開,詩人的情感有所轉向。由最初的批判演變為對李楊愛情不得善終、有情人不能眷屬的感傷,體現出一定的矛盾。但是,在另幾篇涉及宮廷女性的詩歌如《胡旋女》《李夫人》《上陽白發人》等中,女禍思想卻是全文的題旨。《胡旋女》詩前小序中所言“惑君心”。詩中有云: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可見,白居易把安史之亂的罪因歸結于楊貴妃狐媚惑主、君王不圣,有意勸諫君王遠離妃子,直言女色禍國。而《李夫人》專為“鑒嬖惑”所作,借周穆王惑于盛姬,漢武帝惑于李夫人,意在告誡唐憲宗切勿重蹈前朝漢室覆轍:“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白居易作為現實主義詩人,其思想主要是儒家仁政思想影響下的折射,他對勞動人民飽含同情。白居易女性觀的進步意義表現在他對女性命運的關注。既包括婚姻命運,又涵蓋生存命運。人物既涉及上層宮廷女子,又囊括下層貧苦婦女。
白居易在《昭君怨》里抒發了對王昭君悲劇命運的感嘆: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
只得當年備宮掖,何曾專夜奉幃屏。
見疏從道迷圖畫,知屈那叫配虜庭。
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白居易背離了一般詩人站在國家興亡的道德至高點上抒情言志的慣例,而將視角切入到女性個體命運上,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性,具有前瞻意義。《上陽白發人》中白居易借真實的歷史事實重現了后宮制度迫害下普通宮女的悲慘命運,給予她們深切的同情。“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發歌!”白居易欲以直言勸諫君王。他不僅關注到宮廷上層女子的悲劇,也為普通宮女同情地吶喊,為普通宮女的權益奔走呼號。
白居易除對宮中女子難以主宰婚姻命運的同情,也關心底層貧苦的勞動婦女,同情她們的生存遭遇,發出“念此私自愧”的感慨。這些勞動婦女既有《觀刈麥》中的農婦,又有《繚綾》《紅線毯》中的織女。這些勞動女性都以一種固定的弱勢群體的身份入詩,是其“唯歌生民病”創作思想的體現。《觀刈麥》描寫了底層勞動婦女的生存壓力:“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學者楊聯升在其《中唐以后稅制與南制稅制之關系》一文中也說道:“唐初田制為均田,稅制為租庸調,租庸調基于均田制,而二者皆襲自北朝,此向來學者所習知。中唐以降,田制大壞,兼并盛行,租庸調一變而為兩稅。”此等政治變革加重了百姓的生存壓力。白居易作此詩,不僅諷喻當時的苛捐雜稅、土地制度,更旨在反映民生疾苦,同情勞動婦女的生存命運。《繚綾》《紅線毯》《陰山道》都刻畫了女工之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和壓迫者之間尖銳的矛盾。
白居易能站在百姓立場上,真切地反映社會現實和庶民百姓的疾苦,清人劉熙載中《藝概》寫道: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饑寒窮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仁者愛人,白居易對其他人尚且如此同情,對待自己的親人,更表現出真情厚意和無限的愛憐。
白居易于元和三年(808年)與楊氏結婚。新婚燕爾之際,作五言古詩《贈內》以明情志,詩中有“生為同室親,死為同塵穴。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和“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之句。白居易開篇就表明了自己的婚姻理想,即“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表達了愿與妻子偕老的忠貞愛情觀念。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43歲,正在下卦居喪。其時詩人困居窮鄉、內心孤寂,唯有妻子相伴身側才能得以慰藉。遂作七言絕句《贈內》,傾訴對妻子的一腔深情,“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反映了詩人對妻子的珍愛之情。這種感情既不同于初戀的朦朧,也不同于熱戀的熱烈,而是共經患難后的珍惜之情。詩人怕妻子追憶往事,徒增傷悲,對妻子的憐愛之情在聲聲叮嚀中表露無遺。
白居易與楊氏共有5個子女,但只有在白居易45歲時妻子誕下的二女兒羅子長大成人。他在《羅子》一詩中寫道:
有女名羅子,生來才兩春。
我今已年長,日夜二毛新。
顧念嬌蹄面,思量老病身。
直應頭似雪,始得見成人。
詩中寄予了一個父親對女兒最真摯的期盼。羅子20歲嫁到談家,婚后兩年誕下一女,白居易唯恐女兒和女婿因生女孩而情緒懊喪,興高采烈地為外孫女取名“引珠”,并在引珠滿月時,親赴談家作《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把自己的欣喜憐愛之情濃縮于的詩句,詩云:
今日夫妻喜,他人豈得知?
自嗟生女晚,敢訝見孫遲。
物以稀為貴,情因老更慈。
新年逢吉日,滿月乞名時。
桂燎熏花果,蘭湯洗玉肌。
懷中可有抱,何必是男兒?
二、晚期佛道思想影響下白居易的女性觀
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與價值觀往往是儒、釋、道三種思想與價值觀的融合體。出仕時,奉儒守官,仕途坎坷時,佛、道的出世思想占主體地位。受仕途命運的影響,貶謫江州后,白居易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轉變。由前期“兼濟天下”的儒家思想,轉化為后期的“避世保身”的佛、道精神。白居易后期與女尼、女冠交往甚密,他“換盡舊心腸”。選擇了“不入朝廷不入山”的中隱之路。
唐朝道教發展最為繁盛。自高宗尊老聃為玄元皇帝以來,歷代帝王競相尊崇。并尊老子《道德經》為圣經,以道教開科取士。孟子說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社會上道教之風盛行。例如,李白曾受道箓于齊,平生所作詩歌,幾盡篇篇涉及仙道色彩;賀知章頭配黃冠還故鄉;李沁潛心遁入衡山學道。一時風會所趨,白居易受風潮鼓動,亦與女尼、女冠交游甚密。其在涉及女尼、女冠的詩中多表現出與她們同聲共氣的惺惺相惜之情。如《贈韋煉師》詩,白、韋二人的“心似灰”,有著惺惺相惜之情。詩云:
潯陽遷客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
上界女仙無嗜欲,何因相顧兩裴回。
共疑過去人間世,曾作誰家夫婦來。
雖然白居易的涉妓詩中不乏有感情真摯的部分。但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退居洛下之后,受道家精神影響,開始秉持及時行樂、輕物貴己的縱欲主義思想,創作了大量游冶聲色、狎妓宴請的詩篇。女妓意象有明顯的“物化”傾向,體現出一定的局限性。
白居易曾攜家妓與牛家家妓合宴,如《與牛家妓樂雨后合宴》中寫道:“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規勸牛家要及時行樂:“世上貪忙不覺苦,人間除醉即須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時從我游。”《追歡偶作》中則體現了白居易認為女妓只供聲色娛樂的態度:“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在《不能忘情吟》中將放樊素與鬻駱馬并列:“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在其詩《酬裴令公贈馬相戲》亦云:“欲將赤驥換青娥”。
白居易雖是關注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詩人,但后期也表現出“看雪尋花玩風月”及時行樂的局限性。
三、白居易女性觀的成因
白居易的女性觀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雜糅,既有社會文化背景的因素,又有詩人個體生命經歷和多情文人氣質的影響
唐朝處于多元文化交匯時期,儒、釋、道三種思想雜糅。作為儒家思想正統的繼承者,白居易受儒家思想影響尤甚。學者王拾遺在《白居易世界觀芻議》一文中指出,白居易首先接觸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的思想,但白居易對佛家、道家的論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論述去衡量,而不是無所辨析地囫圇接受。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立身準繩。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道:“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這一原則也指導了白居易的詩論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但同時白居易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濡染。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在《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系》中說道,白居易“外雖信佛,內實奉道”。白居易也在《游悟真寺詩》中自言:“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道家的修養形成了白居易獨特的行為方式和人生思考。略觀其詩,不難發現,白居易的女性觀和道教思想也有不謀而合之處。道教講求重人貴生。《老子想爾注》曰:“生者,道之別體也。”將“生”提至“道”的高度來體認。白居易為社會各階層女子鏗鏘發聲,沿襲了老子《鬻子》里“貴柔守雌”的思想。
白居易個體的生平行藏和生命情境,凸顯出其政客和文人的雙重身份,使其女性觀也深受浸染。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官授周至縣尉。這段經歷使他深感民生多艱。促使了他儒家民本主義思想的形成。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官拜左拾遺充翰林學士。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道:“仆當此時,擢在翰林,身是諫官。”他始終踐行兼濟之道,將關注的角度更多切入到貧苦的勞動婦女身上。早在元和初年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懲惡揚善、補察時政、為民而歌的創作理想:“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傷唐衢二首》中,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寄唐生》中指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上達天聽,以達人情,白居易詩中體現了為民請愿的儒家仁道主義思想。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用作者個人的才性氣質來品文識人。三國思想家、政治家劉邵的《人物志》論述了“人本氣生,性分個殊”之理。《人物志》中記載:“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征,則聲變是也。”白居易作為一個“鐘于情”者,他在《不能忘情吟》詩中小序里說道:“予非圣達,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創作《長恨歌》前,白居易與友陳鴻、王質同游。王質促請他道:“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這種情思滲透于白居易的女性觀中,使他對女性有著更多關注,看待女性時也能更多地關注到女性命運。白居易多情的文人性格的形成,與他青年時期失敗的初戀經歷不無關系。
湘靈意象成為貫穿白居易大半生的寫作內容。據筆者統計,白居易所作湘靈詩13首。白居易寫給湘靈最早的一首是其29歲時所作的《寒閨夜》,最晚的一首是52歲任杭州刺史時所作的《潛別離》,時間跨度長達23年。這一情結伴隨著詩人走過春秋寒暑,《感秋寄遠》中有“佳期與芳歲,牢落兩成空”;《冬至夜懷湘靈》中有“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可見白居易的情感態度對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尤以《長恨歌》為甚。詩人創作初衷本欲“懲尤物,窒亂階”,但情之所至,難免折射己身,推己及人。詩句鋪展間,筆鋒一轉,由諷喻轉向感傷。
總而言之,與同時代詩人相較,白居易關注女性命運,其鮮明而進步的女性觀為后代文學創作和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安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