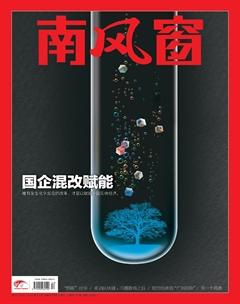以混改賦能中國實體經濟
楊露

國有企業并不是現代的產物,早在古代就已經論及國家壟斷重要產業的意義。
在中國,國企改革是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一路走來,國企貢獻擔當成績斐然,它們是經濟和社會強大的“基礎設施”,支撐中國經濟渡過各種險灘暗礁。因此,無法否認,國企在非競爭領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功用。
回顧中國國資改革,“抓大放小”已成為過去時。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國企改革有了新的深意。顯然,借助混改所形成的資源互補和機制建設,才能將國企真正改造成為能夠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
以管資本為主的監管體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的公司制改革,共同為國企混改創造了條件。“混”是手段,“改”是目的。混改賦能,已呈千帆競發之勢。
從“抓大放小”到混改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企改革就吹起了號角。彼時,民營企業進入了市場并與國企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產品大量增加導致過剩。而國企經營面臨效益下降和虧損,國民經濟運作也困難重重。
中央在國企改革政策上,提出了“抓大放小”。大型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化經營或將其合并成國家控股的大型產業集團,同時將大量的中小型國企關閉或者民營化,采取多種形式放開搞活。
在“抓大”架構內,政府對大型國企實行企業化,把競爭機制引入國企,是想讓其成為真正的企業,將政治、社會和其他功能分離出來。而“放小”架構內的民營化,大大推進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且對中國整體國民經濟形態發生了結構性的影響。在此之上,達成了“國有”和“非國有”之間的一種平衡。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2003年成立,國資委在中央所屬非金融企業中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的職責,實質性地推進了國有資產戰略性布局調整。從世紀之交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國企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使得中國經濟得以輕裝前進。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一樣,經濟增速顯著下滑。國企資產龐大但利潤率畸低,在經歷了2003年以來的緩慢增長之后,績效也再次出現明顯的下滑。因此,2009年關于國企改革的中央文件密集發布,致力于推動國企薪酬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以便減輕全球危機帶來的負面沖擊。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看來,中國自漢武帝“鹽鐵論”以來的兩千多年歷史,就一直存在著“三層資本”的大結構: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底層是自由民間資本,中間層則是國家跟民間互動合作的部分。
三層結構經濟體的獨特優勢,它們能夠預防大的危機,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與此同時,國企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政企不分、行政壟斷的痼疾嚴重制約了自身發展,擠壓民企發展的空間,造成了國家經濟資源錯配等。
目前已先后推出四批一共200多家國企混改試點,在前三批50家試點中,已經有70%的混改試點企業基本完成或即將完成“混”的任務。
因此,中國面臨的問題屬于現存結構之上調整和改進的問題:哪些企業需要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哪些需要讓渡給民營企業?哪些可以二者共同合作?其中,可以改進的地方很多,但主要還是圍繞著那“三層資本”的大結構來實現平衡。這種平衡在被打破后又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改革調整,以達到新的平衡。
全面深化國企改革已不能再拖。2013年國企改革啟動,上海率先在混合所有制等方面做出了各有特色的嘗試。“做強做優”國企是改革目標,行政監管與市場監管雙管齊下。
下游的市場機制與產業鏈中上游密不可分。許多國企所在的壟斷行業屬經濟命脈,大多數行業追根溯源都能發現和原材料、能源、運輸等價格有關,并對企業成本和公眾生活具有直接影響。而引入競爭不僅可以提高行業效率,還能倒逼國企改革,使其真正明白躺在“壟斷紅利”日子到頭了。
此前的國有企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表現得相對保守。但以聯通混改為標志的混改推出,種種跡象表明國企改革將加速。在三大運營商的市場競爭中,中國聯通所處的弱勢地位最為明顯,政府希望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中國聯通的競爭實力,激發市場活力。國企引入民營資本背景的戰略投資,在不同股東之間形成了只有“合作”才能“共贏”的共識。
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目前已先后推出四批一共200多家國企混改試點,在前三批50家試點中,已經有70%的混改試點企業基本完成或即將完成“混”的任務。
國資,打造賦能平臺
國企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鐵路、電信、電力等壟斷領域的混改正邁出新步伐。另一方面,面對科技進步大方向,市場演變大格局,行業變革大趨勢,市場對國企提出了更大的考驗。
今年5月,第四批混改試點正式啟動,一共160家。第四批試點在領域上,不局限于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等重要領域,既包括傳統制造業領域的國有企業,又包括互聯網、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有企業。
由于國企大多在產業鏈上處于重要地位,充分挖掘國有資本的潛力,將會帶動整個產業的協同發展,有助于進一步形成配套完善的產業集群。
以我國大飛機研制為例,大飛機研制難度大,研發周期長,資金投入多。波音、空客的成功經驗表明,商業大飛機制造企業必然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商飛未來的發展計劃中,想要利用大飛機產業基金吸引其他資本參與到大飛機產業鏈來。對商飛來說,將來最直接的混改就是上市融資,也是最有效的產融結合形式。
以上海的中國商飛為中心,鎮江、常州、鹽城、合肥等長三角地區制造業較為發達的城市,開始圍繞大飛機等項目展開積極布局,先后建立了各自的航空產業園區。類似的產業聚集效應也在集成電路、產業互聯網等關鍵領域逐漸發生,如果國企加大改革和技術創新力,在此發展邏輯下將有機會形成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正由消費者端向產業端滲透。在許多大的傳統產業端,國企坐擁資源,由它們來從底層改造傳統行業生態,建設產業互聯網平臺,可以成為傳統行業價值鏈的有益補充。這些投資是一些市場化的短線資金所無法支撐的,但這一類的產業對中國的整體發展而言至關重要且不可替代。
但創新充滿變數,必然伴隨巨大風險,而體制問題是所有國企都會遇到的普遍問題。在企業內部關系上,國企管理權帶有行政色彩,在程序和權限上則追求穩妥與安全。如何跨越這道屏障?最終,還是要推進現代企業制度改革。
今年年初,國家電網就提出,未來將初步建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互聯網企業,推動電網與互聯網深度融合。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吸引社會投資。
從國企混改的另一大功能來看,國資通過打造一些平臺式企業,還能賦能民營中小企業,比如在日化等領域,民企小而分散,缺乏創新資源,而產業互聯網平臺為企業帶來的活力和創造力,其重要性遠大于單純的資金投資。國有企業資源、信用的優勢,與民營企業體制機制優勢進行互補,為產業鏈上下游客戶提供真正有價值的服務。市場機制與國資優勢一起,構成了這一輪混改的“雙輪”,缺一不可。
呼喚“混合所有制企業家”
去年年初,國資委產權局副局長郜志宇曾透露,在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呈現以下特點: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達73.6%;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國有企業次之,占比為62.6%;公益類企業最低,為31.1%。
混合所有制使得這些國企有了一個成功的載體進入市場,解決了國企和民營企業市場融合競爭的問題,把市場的機制引入到國有企業里來,也解決了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僵化的內部機制的問題。
讓國有企業具有市場化的競爭力和活力,必須讓經營機制市場化。但國企的一大問題在于,內部變相私有化現象嚴重,國家管理國企的“代理人”更像官員,而非企業家,并且對國企具有無限的權力,使得它很容易演變成國企管理者的企業。
如今,混改要更加深化,當務之急是必須采用市場化的原則來選擇或任用企業領導人,培育一大批德才兼備,既有大局意識也有市場搏殺能力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家”。
在“盈利”的問題上,公眾也并不相信國企是真的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獲利,更多的人認為它是憑借壟斷來聚集財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關鍵在于要求管理者對全體股東負責,而不是對其中的某一個股東負責。
在此之上,公司的法人治理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去行政化的同時增強市場化。公司的法人治理必須堅持現代企業制度原則,董事會是經營決策機構,股東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決策機關。個別大股東不允許過度干預,任何人都被要求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發揮作用,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那么,混改需要什么樣的國有企業家?中國經濟能保持如今的基本面,更多靠的是具有價值創造的企業家中流砥柱般的支持。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企業家分為套利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家,套利型企業家靠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掙錢,而創新型企業家專注于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環境則有更高的要求。
顯然,混改還有一個核心,就是要保護或者發揚企業家精神。在20世紀90年代,企業化走出了法人化這一步。如今,混改要更加深化,當務之急是必須采用市場化的原則來選擇或任用企業領導人,培育一大批德才兼備,既有大局意識也有市場搏殺能力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家”。
在此前長期相對“封閉”的環境里,國企員工在很多方面都沒有完全適應市場化的環境。一個良好的經營機制應當能充分調動企業員工的活力和積極性,把人“搞活”。當國企員工,尤其是核心員工擁有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建立長期激勵計劃,他會自主轉變思維意識,甚至增強危機意識。
價值創造離不開企業的效率水平和創新能力。只有那些善于運用國資優勢和市場力量的企業領導者,在人才激勵等市場化機制下,才有機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讓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優勢在混改中得到實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和推進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需要,它可以讓國有資產回歸公共財產的本質,而不是僅僅躺在“政府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