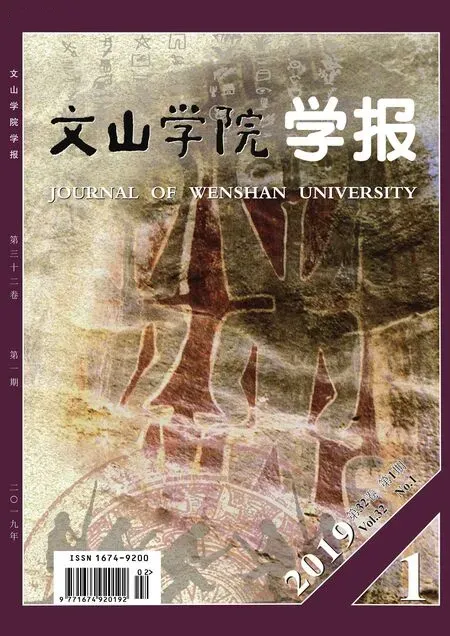云南建水團山民居建筑中的儒家文化
劉雪寧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國的歷史文化,一半由墓葬帶入地下,一半殘留在地上的“居所”之內。從原始社會的石窟洞穴,到奴隸社會中的茅茨土階、干闌木架和磚墻瓦檐,封建社會中的戰國臺榭、秦城漢闕和木構殿堂,乃至于近現代由鋼筋水泥構建的摩天大樓、玻璃棧道,被稱為“高級動物”的這一群體的原始動物性中的“領地意識”,在中國人對“居所”的選擇、構筑以及表現形式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對人類來說,一旦確認個體或者群體在某地留居的必然性,在“能力”允許的前提下,尋找或建筑“居所”就成為了必須,這不僅僅是為了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也是為了標記領地、彰顯存在,為整個族群的生存、繁衍和發展奠基。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作為“居所”存在的建筑物,能夠被稱作“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產品……是構成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1]49。
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加之地域遼闊,其建筑樣式不僅會展現出受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影響后的時代特征和個體特點,而且會在不同自然環境和民族文化的沁潤下,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風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中,“建立在漢民族地主經濟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在國家的發展中,始終占有主導地位”[1]3,而維系這一主導地位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文化滲透,即通過思想同化,實現民族“大一統”,為鞏固漢民族的正統地位服務。這既是孔子開創的儒學能夠獲得統治者的支持與肯定、并自先秦之后始終保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對19和20世紀的大多數外界觀察者來說,中國人的房屋看起來首先是一個家廟”[2]的主要原因。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學便成為了漢民族進行族群識別、塑造民族意識的思想基礎,并以其強大的包容力和滲透力,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不同地域少數民族的審美標準、價值追求和倫理觀念,而建筑物這一作為物質實在的文化載體,則擔當起了記錄和展現各民族文化心理轉變、文化融合的過程及其主要內容的重任。
一、云南建水團山民居總體概況
漢代,漢武帝在司馬相如《難蜀父老說》的支持下,決心在云南設立郡縣,并為實現“遐邇一體,中外提福”[3]的“大一統”理想,“一方面用武力鎮壓云南各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則積極推行儒家‘用夏變夷’的文化戰略。”[4]借由朝貢、和親、入覲、納質、戰爭援助等方式,漢朝統治者不斷擴大儒學傳播的途徑,促進中央與地方的文化交流,效果顯著。如云南昭通市發現的東漢時期的《孟孝琚碑》中提到,當地僰人孟孝琚“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5]96,可見此時儒學經典已經在云南各地傳播開來。還有記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云南掌權大姓爨氏的《爨龍顏碑》,在提及爨氏先祖時,言其“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后之盛,敷陳五教”[5]232,即稱其先祖用儒學中的“五倫”來輔佐夏朝統治者,而爨氏之后,云南也確實出現了“白蠻文化,漸摩中州,同化華族”[5]346風潮。由此可見,由云南本地大姓無意間發起的學儒、用儒風潮,在中央統治者的刻意推動之下,成功實現普遍化、日常化,并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云南地區的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
(一)云南建水傳統文化氛圍
建水,古稱臨安,元和年間南詔國筑城時曾稱為慧歷城。慧歷是古彝語,從意義層面上可以理解為“建在水邊的城市”。直到大理國設立建水郡,并將其劃為爨氏封邑,才定漢語名“建水”。元代沿用該名,定建水州,明代則為軍務之需,“于此設臨安府和軍事指揮機關臨安衛(下轄8個千戶所近9 000人的軍隊),拓地改建磚城,故有‘臨安’之稱”①,至今已有約1 200年的歷史。位于云南邊陲的建水是漢代“馬援古道”,唐代“安南通天竺道”“步頭路”和“通海城路”,乃至于宋元沿用至明清時期“官馬大道”等重要通路的必經之地。其上接滇西南絲綢之路,下連滇東南交趾郡(今越南)、寧遠州(今越南萊州)、老撾路,不僅是云南與各界交流的交通要地,還承擔著中國西南地區的邊境沖衢這一重責大任。
便利的交通所帶來的,不僅是繁榮的經濟,還有多彩的文化。建水城敞開城門的開放態度在迎來送往的過程中,無意間為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提供了理想的場所。不同地域、民族乃至于國家的文化在建水城中匯聚、雜糅,再以此為源流至四面八方,中央統治者也因此將建水作為向云南推行儒家思想、實現“用夏變夷”文化戰略的主要切入點。
公元1274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中書省,并“先后在中慶、大理、臨安、永昌、鶴慶、姚安、威楚各地建文廟,置學田,設儒學提舉”[1]5,至明朝,作為一種教育方式,廟學在建水地區已經相當普遍,當地一時科考成風,掌權的普姓土司更是對儒學推崇備至。“普氏土司發布文告,均用漢文書寫,并在土司衙門上懸掛對聯‘九重錫命傳金碧,五馬開基至漢唐’,‘承國恩化洽三江茶甸,奉御賜八百里納樓’等”[6]。中央政府的刻意推行,加之地方首領的推崇,儒學消無聲息地實現了對建水文化結構和社會記憶的重構,其具體表現如下:
其一,少數民族主動參加科舉,以入仕為榮。這一點從建水本地遺留的諸多牌匾可見。“如‘父子進士’(雷學尹、雷整建父子建)、‘父子登科’(為羅晟、羅珦父子建)、‘兄弟進士’(為廖大亨、廖履亨兄弟建)、‘叔侄進士’‘父子三進士,兄弟兩翰林’(為倪高甲、倪思蓮、倪思淳建)等”[7]。既然做了牌匾掛在顯眼處,便說明這是值得引以為傲并昭告天下的喜事,由此可以看出建水人對考取功名的追求。其二,建水居民對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等觀念的高度認可。建水著名古建筑朱家花園祠堂正門上刻有“二十四孝”主題的木雕,當地古建筑的門扇、窗欞、雕駐或上下檻上,也常見各類與“孝悌”“仁義”相關的字畫、警句。其三,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地方風俗的出現。《臨安府志·風俗》卷七中記錄了建水極具中原地區特色的各類風俗習慣,包括祭祖敬香、寒食節的插柳于檐、七月七的乞巧以喜和中秋的呈瓜果于庭以祀月等,并以“士者四民之首,出以樹卿大夫之望,處以為善,而化鄉人風俗之轉移,恒必賴之”[8]作結。建水地區濃厚的儒學氛圍,由此可見一斑。
(二)團山民居情況簡介
建水城西十三里,有一座 “全村240戶877人,張姓就有178戶677人”[9]的典型家族式、同姓聚居的村落,這就是團山。歷史上的團山是彝族的居住地,彝族人稱其為“突舍爾”,意為“藏金埋銀之地”。據傳張氏先祖早年放牛時無意間發現了這個地方,見其草木豐茂,山明水秀,當即決定遷居至此,發跡后又在此地建祠立宗,這才有了之后的團山民居建筑群。
團山村中的張氏祠堂內,有一副強行對仗的陳述式對聯——“張姓始祖發籍于江西鄱陽許義寨先輩正宗,氏族興旺遷移在云南建水團山村后世立祠”,用短短兩句話說明了張氏家族的歷史。據史籍記載,明洪武年間,明太祖義子、征南右副將軍沐英從將軍付友德,率幾十萬大軍至云南平亂,后親自留鎮,為合禮制,大批軍屬隨之入滇。公元1384年,一方面為推行屯田,一方面為“用夏變夷”文化戰略服務,朝廷又“移中土大姓以實云南”,一時之間,建水涌入大批漢族的富家大室,張姓始祖張福應是其中之一。初至時,張氏一族暫居藍頭坡,輾轉三遷才定居團山。清康熙、雍正年間,建水個舊掘出錫礦,一時之間商賈云集,采礦業取代了傳統的農耕,成為當時最熱門的行業。加之建水人多地少,當地的貧困戶被迫轉至個舊的錫礦打工,以謀生路。張家人抓住了這一重要的歷史機遇,創辦了“盛極一時‘天吉昌’集團,集采、選、冶為一體的錫礦大商號,兼營棉紗、百貨進出口等貿易,轉口貿易的生意做到了昆明、成都、上海、香港和越南海防。由此,團山張氏的經營和財富的積累達到巔峰,成為雄震一方、明噪滇南的‘團山幫’”[10]。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樣,當留居某地成為必然,那么在“能力”許可的范圍內,人類對“居所”的需求就是第一位的,中國人尤為如此。《黃帝宅經》中曾提到:“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則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當張氏家族積累到大量的物質財富、并認識到“返鄉”可能性之渺茫后,傳統的“尋根”心理便開始催促他們動土建宅,實現“齊家”理想。此后不過數年,在這遠僻邊地建水旁的小山村里,由一座座既能展現家族傳統、歷史和文化,又兼具風雅、威儀和美感的私宅大院共同組成的、規模巨大的傳統民居群落拔地而起,在歷史風塵中承載著張氏家族的全部記憶,挺立至今。
團山村中的民居建筑大多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磚木結構為主,現有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大宅十五座,寨門三座,寺廟三座,宗祠一座。首先,從建筑布局看,團山民居均按照向陽背陰的基本原則,坐西朝東,白墻灰瓦高低有致。私宅合院通常對外封閉,以墻、廊圍繞各間,富足者家宅院落不止一個,通常重重相套,向縱深或橫面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大戶人家的宅院被分給村民,由幾家共住一院,為生活便利,多在院中壘墻作隔,也就破壞了原本由環天井的四合樓廊形成的“跑馬轉角樓”這一特色形制。相鄰院落通常有所間隔,因各家院落多方正有序,故村中道路不必專門安排,只需于各大宅間的空缺處鋪上磚石,砌墻補缺,串聯成道即可。其次,從宅院布局來看,團山村民居的布局呈現出明顯的雜糅色彩,既有在云南傳統民居中極具特色的“四合五天井”(司馬第)、“三坊一照壁”(張家花園)、“跑馬轉角樓”等主要形制,又有江西天井民居的影子,還有設有瞭望哨和槍眼的防御工事(鎖翠樓)。另外,團山民居各院多遵循風水中的“藏”字訣,將正門建于正房兩側小天井旁的漏角間,或通過建筑物進行遮蔽(以照壁為多),來人需繞行才能進入中庭。最后,從建筑裝飾來看,團山村200多戶人家中,一半都保留著斗飛檐、雕梁畫棟的明清大宅門。其上的“斗拱彩畫應用群青、粉蘭、白色、金色、黑色等撞色平刷,無過多蘇彩技法,這樣的色彩使用方式正是滇南彝族搭配色彩的方式。梁、坊間彩畫分三段式,飾硬卡子,小包袱,包袱內飾精美字畫。字畫布局得體、秀拔優美,均是滇南知名畫家王永清、呂彬、武士麟所作。”[11]民居建筑中多置花園,兼有大小天井數個,以應風水中“聚財”一說。其門樓樣式不一,但門扇均有雕花刻字,并鎏金描彩。窗飾則以欞穿和花式窗兩種為主,其上多刻祥禽瑞獸或與福祿壽相關的吉祥圖案。庭院照壁、梁柱、天花板和回廊上繪滿各類詩詞、繪畫和楹聯,多典故和寓意,彰顯著主人的文化素養和價值追求。
團山民居建筑不僅體現了張氏族人深厚的經濟底蘊,成為考察中國近代地方民營工商業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也是中原漢民族文化與滇南少數民族文化相遇后,由張氏族人繼承、融合、凝聚而成的物質遺產,具有極深厚的文化底蘊。
二、建水團山民居中的儒家文化
云南建水與儒學歷史淵源使得團山原住民對儒學有著極高的認可度和接受度,而后移民至此、深受儒家文學熏陶的張氏族眾又因其豐厚的經濟基礎,在村中事務和日常生活決策等方面取得了主導地位。在此背景之下,儒學不斷深化與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實現了對當地居民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等深層文化心理的重構,而這一隱秘的思想轉變,則涓滴不漏地由團山民居建筑記錄下來。
(一)建筑布局
團山民居建筑以二進院為主,兼有一進院、三進院樣式,形制結構基本相同,其中以張家花園建筑最具代表性。
張家花園由寨門、一進院、三進院、花園祠堂和碉堡組成,共119間房、大小天井21個,是一組城堡式的私家園林。一進院樣式為“三坊一照壁”,三坊均由兩層三間的廂房組成,與“三疊水”照壁合圍成院。正對照壁的一坊高于側坊,裝飾紋樣也更為精致華麗(團山民居建筑群中均如此設計),是為正廳。其左右兼有耳房和天井,是主人待客的場所。二進院以正房為核心,由廈廊連接各側耳房,前為花廳,與正廳相背,四合成正方形的天井,集居舍、庫房和廚房等功能為一體。三進院則以供奉祖宗牌位的長輩正房為中,左右立花園祠堂,庭中建水池,池邊圍雕花石柱,由回廊圍連成規整的矩形。
儒家文化強調人倫次序和尊卑等級,常以“別尊卑,明貴賤”“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等說法來鞏固封建制度,從而維護君權。統觀張家花園的建筑布局,可以明顯看出其房間位序服務于人倫次序的特點。首先,張家花園建筑群落沿庭院縱深軸線形成明確的空間序列,正廳、祠堂、長輩正房等重要場所均建于中軸線上(始祖為中),其余各處則按照“前公后私”(前一院對外開放,用于接待外人,后兩院則為自家人服務),“前下后上”(地位卑賤者或晚輩處前,地位尊貴者或長輩居后)的原則位居次軸,依橫向對稱,拱衛中軸建筑。其次,民居中主廳、祠堂等主要建筑通常基地較高,門前有欄桿或階梯,其紋飾施以重彩,花樣繁多,顯得雍容華麗;而側房則紋飾簡單,規格樣式近似,色彩較主廳清淺,以護衛狀突顯“中心”。最后,張家院落整體經由最外側圍墻對外封閉,三進院各院亦有門作隔,下修極高門檻以作提示。各院主、側廳,加之照壁或前屋后壁,以天井為中央作四合狀,院落有缺處建“漏角”作為下人居所,從而形成對外封閉的、嚴密嵌套的矩狀空間,與漢式建筑中體現出的“方正有序”“勿太密,親則疏”“克己復禮”等強調階級、中庸和禮制的儒學思想不謀而合。此外,在房間分配上,團山村呈現出高度的儒家禮制特色,家族嫡長子居正廳右側,次子居左,未出閣的女子則居側坊二層,與家族中的男性間隔開來,其他家眷則以長幼、男女、家族貢獻等為準,另作細分。下人所住的“漏角”于中庭是不可見的,出行需自側邊小門繞行,客人則多住于一進院側坊中,以示尊卑之別,親疏之分。平日里,各院門通常閉合,避免互相打擾。若家中需舉辦重要活動或在其他必要情況下,才將院門全部打開,使各院相連成一體,這種安排“更加體現了一種穩定的、長幼尊卑不可逾越的人間秩序”[12]。
(二)禮制建筑
在儒家文化之中,“禮”是一種以宗法血緣意識為核心的規范體系,在封建時期具有與法律等同的效力和性質,是統治階級用以維護君權、管理大眾的禮儀規范,其內容幾乎囊括了封建統治下天人、等級、人倫等全部社會關系。而能夠體現這一宗法禮制的建筑,就被統稱為禮制建筑。
張氏宗祠是團山村中張氏族人議事、祭祖、調解糾紛和舉行重要互動的主要場所,始建于清代乾隆四十八年,正堂中懸“繩武其祖”匾額,下嵌“百忍宗族”石碑3塊,上錄自張氏始祖張福以下各張氏支系名列。祠內還靠墻放有“張祖祠銘志”(1996年10月10日)、“飲水思源——重修張氏始祖墳墓碑序”(1994年)兩塊碑文,前者記有后輩驕子、村民生計、社會狀況(“文革”)等內容,后者為捐錢重修祖墳名錄,因時值團山村多處重建,此二碑本置何處無從得知。祠堂門扇飾有“壽”字紋樣及各類吉祥圖案,中門處貼有門神,其衣飾紋樣以紅綠色為主,上有金色龍紋,款式依漢制。與祠堂相對的照壁上有內嵌石碑,上書“祭祖歌”,全文如下:
維我始祖 發籍江西
貿易到滇南 遷居于建水
卜宅團山 造成了巨族之鄉
世世代代 維美書香 百忍家風 耀彩千秋俎豆馨香
正如上文提到,團山歷史上是彝族的聚居地。彝族供奉祖先的方式是通過在家里專設木柜“幾”,用以放置供奉祖靈的神龕、祭品,便于家族祭祀,而宗祠,則是典型的漢族禮制建筑,這一建筑的產生,也和儒家文化的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從根本上可以被視作一種血緣宗法意識。即將衍生在血緣關系上的親情視為整個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基石,從而以此為標準劃分家庭、親緣之間關系的親疏遠近,由于對宗族血緣的高度重視,漢族才出現了“祠堂”這一建筑樣式,用以強化“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13]的思想,對離開故鄉的張氏一族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之所以用石碑記事,定時祭祖,并在祠堂各處反復提及“百忍”家風和始祖歷史,都是為了“以共同儀式來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強此集體記憶,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實質紀念物來維持集體記憶”[14],使后輩謹記“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15]。
(三)裝飾藝術
基于團山村各家不同的經濟水平,民居建筑中的裝飾藝術也存在工藝、材料、數量和大小等方面的區別,但表現出的儒家思想內涵卻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主要表現為“親君子”的文化追求、“開枝散葉”的家族理想和“天人合一”的價值觀念三大主題。
1.“親君子”的文化追求
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格,內有“達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15])外具“文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16]114),既通詩書,又知禮樂,可以說是“修身”完備的“圣人”了。而對于如何成為君子,儒家文化從個人行為舉止、儀容儀表和文化修養等各方面都做了細致的要求,而正如孔子說的那樣,“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16]25,其源頭在于學詩。
團山民居建筑裝飾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遍布屋壁、天花板、門楣、木枋和窗檐等地的書法詩畫作品,“書法2 977幅……題材眾多、內容豐富、構圖精美的繪畫計有2 617幅”[17]。從形式上看,團山民居建筑裝飾中的書法作品均為白底黑字,楷草篆隸皆備,少數在結尾拓有方正的紅章印,其內容不詳。詩畫作品中,除門扇上偶有門神、珍禽圖以彩繪,其余山水人物、花卉異獸、梅蘭竹菊等作品均仿漢族水墨畫,以扇形、圓形、匾額等形狀的木框作底,于白底上用墨色賦詩作畫,詩畫通常并與一處,以畫解詩。從內容上看,團山民居建筑群中的書法詩畫裝飾以漢族古文、詩詞為主,兼有簡短的單字、詞語、格言警句和“百忍”家訓等,多褒獎忠孝道德,強調禮義廉恥,或告誡后人潔身自好,知節懂禮,顯示對“君子”風范的明顯偏好。
此外,團山民居建筑群中還出現了滇南民居中尤為少見的檐梁斗拱、柱礎石欄等構件,并以木雕、石刻各類紋樣裝飾其上。紋樣分各類,其中植物類的以梅、蘭、竹、菊為主,而事物類的則以琴、棋、書、畫為先,并兼有許多故事性、諧音性的圖案主題。如團山民居建筑檐枋上常見的“麒麟吐書”,源自孔子出生時,有麒麟降至孔府闕里人家,口吐玉書以告眾人孔子之非凡的傳說。又如團山民居屋脊上常見的龍魚,通常為一對,龍頭魚身,魚尾高蹺,取“鯉魚躍龍門”之意,此外還有“漁樵耕讀”“加官進爵”“連升三級”等極具現實意義的木雕圖案。在儒家文化中,梅蘭竹菊被稱為“四君子”,琴棋書畫則寓“君子四德”,而“學而優則仕”的入世觀念亦是儒家的一大核心思想,其主要內容就是提倡入仕,以考取功名為榮,團山居民中濃厚的“親君子”之意不言而喻。
2.“開枝散葉”的家族理想
上文禮制建筑一部分中提到過,儒家文化對宗族血緣關系是極為重視的,“開枝散葉”的家族理想正是這一族群思想具體化、生活化的展現,其中既有對家族富足、源遠流長的期望,也有后輩可光耀門廳,先輩可壽年永固的渴望,是儒家文化與人的原始渴望相遇之后碰撞出的火花。
團山民居建筑裝飾中對這一家族理想的表現十分豐富。只“門”就有許多講究,“安裝于堂屋和廂房的隔扇門常以四扇或六扇為一堂,寓‘四季平安’‘祿祿有福’,每扇門由天頭、上幅、玉腰、下裙、地腳五個部分組成,寓‘五福齊全’”[10]。不論是張家花園內的水池石欄上下的石雕磚刻,還是團山其他各家宅院門窗屋檐上的木刻雕花,其內容都兼有表示吉祥的“如意”“白象”“鯉魚”“龍鳳”、代表長壽的“白鶴”“仙桃”“八仙”“靈芝”和象征加官進爵的“文房四寶”“六祿”“喜鵲”“金鹿”等各類紋樣,表現出辟邪護宅、求福納才等多重寓意。
孟子曾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這一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觀念,在封建社會中,延伸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光宗耀祖”等多重含義。求福可保家人安康,入仕可耀宗族門楣,長壽才有機會盡孝,而這一切的物質基礎都在于足夠的財富積累。也就是說,上述所有的紋飾內容,歸根究底都是“孝悌”在現實生活受到地域、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后的具化。
3.“天人合一”的價值觀念
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觀綿延已久,經由董仲舒的整理歸納,有了較為系統的闡釋,其內容以“人源于天”“天人同類”“天人同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五大思想主題為核心,其闡釋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里主要取“天人同理”之意,即“事各順其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18]。
團山民居建筑至今仍以磚木結構為主,各院均設天井、花廳,除張氏祠堂外,各院大門通常設于院中小天井所在的“漏耳”內,以保證往來者繞行進出。凡有院,必植花草,張家族人甚至于三進院中獨設花園和中庭水池,并在張家祠堂后種有“風水樹”,稱其“萬年青”以寓家族長盛,庇族人平安。村中四處可見遮天大樹,修路時或繞道而行,或專門留以空地,通常任其生長,并不做刻意移植修減。團山村民居建筑群中展現出的這一“澤及草木,恩至水土”的生態觀念,正是“天人合一”理念的變體。
正如《中庸》所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16]16這里的“和”,不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同”,還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順”。以天井聚水以匯財也好,種樹改風水來庇護族人也罷,還有為“親近”自然而將花園中的道路設置的彎彎曲曲、以照壁格擋防止財氣外泄和門前置花草、院中樹成雙等“故意為之”的“風水習俗”,都是以“同而通理,動而相益”為出發點的。正如除皇恩府外,八大廳建筑都在位于一進院中軸線上的門海前側刻有的朱熹書法作品“靜觀魚躍”,和張家花園三進院中水池石欄上所刻“活潑潑地”所說的一樣,人之重點在于敬畏和調和,無畏者無理,自然有逆于天,然后失德。只有有所畏懼的人才能找到“中庸”之道,明白“天道”,即仁德之理。
三、建水團山民居建筑中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及其保護
作為古村落的團山民居是“保留了較大的歷史沿革,即建筑環境、建筑布局、村落選址基本保持原貌,延續了獨特的民俗民風和傳統生活方式,至今仍為人們服務的村落。”[19]3與歷史遺址不同,團山民居至今還是活著的張氏歷史記錄者和云南農村社會文化變遷見證人,是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寶貴資源。在2005年6月21日,團山村被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WWF)批準為2006年世界第100個紀念性建筑遺產保護對象之一,但同時,團山村也被公布為2006年世界百大瀕臨危險的文化遺址之一,其保護呈現出明顯的現實緊迫性。
(一)物質文化遺產
走入團山民居,處處可見文化大革命時期留下的印記,正如張家祠堂中碑文所記載的那樣,在經歷了令人痛心的、特殊的歷史時期之后,團山留下的最值得珍藏和保護的,便是其民居建筑了。不論是其中展現出的滇西建筑工藝特色,還是白族民居中極具特色的“四合五天井”(司馬第)、“三坊一照壁”(張家花園)、“跑馬轉角樓”建筑形制,或是漢族的祠堂、花園建筑樣式、書法字畫和木雕石刻等實物,都是儒家文化與多種文化共同孕育的物質寶藏。
但隨著現代化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團山民居中遺留的物質文化遺產在逐漸的消失。最初是由于政策安排,為扶貧安居,將大宅分給數家村民同住,居住過程中出于分割生活區域的考慮,村民會加建圍墻,破壞建筑物原本形制。加之村民對于古村落的保護并沒有具體的意識,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的原因,不僅安裝防盜門、太陽能和無線接收器等現代設施,還翻蓋磚房,重修水泥路等,從而改變了古建筑和街道的整體結構,破壞了民居建筑群傳統原貌。
2005年后,隨著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的批準,當地政府和村民意識到團山的文化價值,并隨即開展了各種重建保護工作,卻因此為團山民居帶來的另一個隱患——保護性開發的威脅。為盡快恢復團山民居建筑群原貌,并使之保有經濟價值,“重建”是必然的。但重建過程中,施工人員的文化修養,重建時的經濟考慮,都會使得重建后的團山民居建筑群面臨著失去文化內涵的巨大威脅。正如筆者在張家花園窗欞上所見的“金鹿”浮雕,通常相對兩窗紋飾必當一致,以作平衡之勢,但右側窗框全部施以紅漆,并無“金鹿”,湊近便可看出紅漆下“鹿”的浮雕樣式,想必是工人為了上色方便全部涂紅。建筑中的文化體現在每一處細小的紋飾雕刻、色彩配置之中,長此以往,不知會有多少“金鹿”失色,無人知曉。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
除了建筑類的物質文化遺產,團山民居中保留的“活態文化”也是珍貴的特殊資源,正是這些“活態文化”孕育的民風和民俗,使得團山民居成為了“可以親歷的生命史中的一個階段……一個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生命有機體。”[19]4
作為典型移民村落的團山最重要的民俗活動,便是誕生于儒家文化之中的祭祖儀式和“百忍”家風。作為漢民族儒家文化中極具普及度的“孝悌”觀念的具體表現,加之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張氏祭祖儀式的具體內容所表現出的藝術張力、文化多樣性和吸引力可想而知。“百忍”家風兼具“中庸”和“君子”之道,正如朱熹所言:“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于愛;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亂大謀”。“忍”不僅體現出張氏宗族的獨特風骨和對后人的殷殷教誨,也飽含著張氏宗族對歷史境遇、時代變遷、人生的思考,是歷代族人全部生活經驗升華而成的思想結晶。人會逝去,物質會腐朽,而這一思想結晶卻在時代更替中熠熠生輝,在家風家訓中代代相承,成為證明一個宗族存在的、極具史料、文化、民俗等各類研究價值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也是為什么,“莫言人短,莫道己長,施恩勿講,受恩不忘”的張氏祖訓至今還刻在張氏祠堂正對的照壁之上,一旦缺損立刻重修。因為這不僅僅是一段話,還是一個家族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雖然張家祠堂外用以情況簡介的宣傳牌上提到,張氏后人至今還保持著按時祭祖的習俗。但隨著村里長者的逝去,青壯年也多離村讀書,很少回家。缺少傳承者,又沒了繼承人,張氏宗族祭祖的具體儀式流程也隨之簡化乃至于忘卻,而“百忍”家風雖然仍舊是張氏一族的精神紐帶,但其思想內涵卻逐漸干癟,面臨時代危機。同時,村里由漢文化和云南少數民族文化雜糅而成的民俗技藝、節日慶祝方式等民俗文化也在步向消亡。雖然團山村在2013年3月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后,已經成功實現了由單純的古村落向當地極具代表性旅游景點的轉型,但缺少代表性民俗特色來進行精神文化展示,只依靠建筑、文物等物質文化實體支撐,團山村作為文化旅游景點的前路尚未可知。
(三)保護措施
根據團山民居面臨的現實問題,基于對當地文化多樣性的研究分析,現就其物質文化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政府必須展現出領頭羊的氣魄,通過法律手段監管古村落建筑、文物以及文化保護的方式方法,并對民間保護組織進行集體管理,適當給予經濟支持,減少因管理失誤帶來的特殊資源損失。另外,“政府在保護古村落的過程中將擔任重要的角色,但在市場經濟中不是以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干預古村落的發展與保護,而是通過比行政手段更為有效的宏觀引導來實現”[20]。包括及時公布古村落保護區名錄,以官方姿態進行文化宣傳、引導社會輿論發展方向,促進新聞媒體的關注,同時運用行政手段嚴格監測各級古村落保護區,明令禁止對保護區盲目的開發宣傳和重建行為,引導各級保護力量進行合理有序的修復重建、對外開放工作。當地政府則應設立有效的獎勵機制,保證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展。祭祖等活動開展時,在明確不觸犯國家法律、符合社會公共道德并具有積極影響的前提下,當地政府應鼓勵和支持此類民俗活動的開展,并積極宣傳。最重要的是,各級政府都應當將古村落的開發建設活動置于保護規劃的框架內,“實行梯度開發、漸進式開發、對少數資源占優勢的景點實行優先開發,對尚不具備開發條件的古民居和古建筑實行嚴格保護”[21]。從而確保當地物質文化遺產的完整留存。
其次,應充分發揮當地居民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其保護意識,發動居民自覺地進行文物保護、文化傳承。如團山民居的村民自發成立了由13個委員組成的“團山歷史文化名村保護委員會”,并在縣里的協調安排下,拆除了占道的豬圈牛圈,矮房,把古建筑中雕花的青磚墻裙顯露出來,便于旅游事業的發展。除此之外,還應有意識地培養后輩的集體文化心理,廣泛、多次的開展祭祖等儀式活動,加強村民的文化認同感、提高文化自信,從而鞏固歷史記憶和家族情感,形成完整的內部動力機制,做到在保護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再生。
最后,要發動社會各界的力量,把文化遺產保護作為整個社會的任務來執行,形成政府引導、媒體傳播、商家引資、村民自珍、民間自發出力、學者主動宣傳等多位一體、共同參與的、積極的保護開發模式,從而調動一切可用的力量,使資源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減少資金的流失和人員浪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實現“把文化資產轉變為特殊資源,同時確保其文化內核受到最完備保護”的最高目標。
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為光輝璀璨的主流,其分支早已遍布中國大地,而在與不同地域文化匯流之后,則往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光彩。云南建水團山民居建筑就是這一匯流激蕩出的物質實在。在吸取了當地白族民居建筑形制和少數民族建筑裝飾藝術的主要物質、精神內容之后,借當地工匠之手,基于儒家文化的思想基地,張氏宗族在云南邊境創造出了獨特的民居建筑群,并賦予其極強的生命力和文化包容性,進而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的物質文化遺產。在團山民居建筑中,仍然深藏著許多特殊而珍貴的文化資源,等著后來者們的研究和發現。
注釋:
① 參見建水縣政協文史委員編《建水文史資料選輯》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