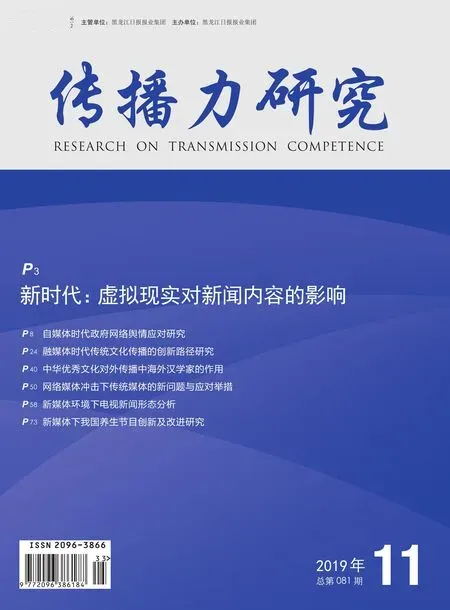大學生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認知及使用行為分析
——基于山西大學城的實證調查
白小豆 太原師范學院 宋藝敏 山西大學
社會交往是人的本質內在要求。在當代社會人際互動的過程中,“既存在收縮化的熟人社會,擴大化的陌生人社會,又存在一個全新的匿名化、身份自定義化的社交場域。三者相互交織,共生共存,構成了當代社會個體的社交圖景。”①近年來,專注于為陌生人社交建立互動關系的軟件應用受到很多青年用戶的喜愛。本文基于山西大學城十所高校開展實證調查,通過微信、QQ、貼吧以及“陌陌”等各類陌生人社交應用平臺發放問卷,了解大學生群體對此類陌生人社交應用的認知傾向及使用行為。
問卷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為人口學變量的測量,包括性別、學校、年級、專業、戀愛狀況、獨生子女與否;第二部分為接觸和使用情況,包括對陌生人社交應用市場現狀的了解、使用時間、使用強度、最常使用的功能以及使用動機等;第三部分主要了解大學生對陌生人社交應用使用安全和信息內容的信任度,對于應用功能設計的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的意向。研究共收回有效問卷329 份。

表1 性別*整體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向
一、大學生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認知情況
(一)市場認知
如圖1 所示,大學生知曉度最高的陌生人社交應用是“陌陌”,其次是“探探”,這個結果也從側面印證了當前陌生人社交應用市場頭部效應明顯。其后,主打心靈交友的“Soul”在大學生群體中也具有較高的認知度,占樣本總體的61.73%,“遇見”、“比鄰”、“一罐”、“如故”、“Same”等應用則顯得較為小眾。
(二)信息安全認知
如圖2 所示,絕大部分大學生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的使用安全存在質疑,普遍認為個人信息在陌生人社交應用上有隱私泄露的風險。
(三)整體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向

圖1 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了解程度

圖2 個人信息在應用平臺上是否受到了很好的保護
由表1 可見,大學生對于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整體滿意度較低。認同“我對所使用的陌生人社交應用整體滿意,會繼續使用”(包括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大學生占使用者樣本總體的20.97%,近半數學生表示滿意度一般,還有29.48%的學生表示滿意度很低。此外,大學生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的整體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向存在性別差異,男大學生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的滿意度和忠誠度更高。
二、大學生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使用情況
(一)整體使用狀況
如表2 所示,近86%的人使用過陌生人社交應用但后來卸載,其中男生群體占總體的44.52%,女生群體占55.48%。而一直在使用陌生人社交應用的大學生占總體的近14%,其中男生占該群體的76%,女生占群體的23.9%,可見,相比于女大學生,男大學生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的使用率和忠誠度更高。
(二)使用時長
表3 數據顯示,持續使用該應用的大學生過去一星期內,每天使用1 小時以內和2-3 小時的占32.61%,每天使用1-2小時的占21.74%,使用時間長達3 小時以上的使用者最少,僅占13.04%,可見大學生群體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粘度并不高。
(三)使用習慣分析
(1)常用功能
樣本對象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自己使用頻度最高的三個功能并進行排序,得出了最常使用功能的平均綜合分數(選項平均綜合得分=(Σ 頻數×權值)/填寫人次)。如圖3 所示,大學生在陌生人社交應用上最常使用的功能為“附近動態”,可見大學生有強烈的了解周圍環境的信息需求。其次是“心動匹配”,使用頻度高于“興趣群組”和“游戲”,說明在陌生人社交應用中,滿足情感需求比娛樂休閑更為重要。
(2)發布內容類型
如圖4 所示,喜歡發布“日常生活”的使用者最多占樣本總體的76.9%,說明盡管大多數用戶認為自己的個人信息在應用平臺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但仍然熱衷與他人分享日常生活,以此進行自我披露;其次是“情感話題”類內容,占樣本總體48.63%,說明情感因素是陌生人社交應用中建立關系的重要紐帶。
(四)使用動機(見圖5)
根據主要使用動機的平均綜合分數顯示,大學生使用陌生人社交應用最主要的三個動機是:“結識新朋友,擴大社交范圍”、“驅散孤獨,消遣、打發時間”和“休閑娛樂,放松心情”。由此可見,交友和娛樂是大學生使用陌生人社交應用的最主要動機。

表2 使用狀況*性別

表3 過去一個星期中平均每天用在陌生人社交應用上的時長分布

圖3 最常使用功能統計

圖4 發布內容類型

圖5 使用動機

表4 在陌生人社交應用使用中的主動性
(五)行為的主動性(見表4)
44.98%的使用者選擇了“不太愿意與人交流,只是瀏覽信息”,可見多數人在使用陌生人社交應用中的主動性并不強,而在選擇“主動與別人交流”的110名使用者中,男生占比高達89.09%,可見在陌生人社交應用的使用中,男生比女生更傾向于主動與人交流。
三、大學生陌生人社交應用認知使用行為理論闡釋
大學生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的認知水平較高,但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信息安全信任度很低,對該類應用的整體滿意度和使用粘度并不高。在認知和使用情況方面存在很大的性別差異。相較而言,女生在使用率、主動性、忠誠度和信任度方面都呈現較低水平。筆者嘗試從相關理論對大學生陌生人社交應用認知和使用現狀加以闡釋。
(一)需求的權衡影響使用行為
學者祝建華在“使用與滿足”理論基礎上提出新媒體權衡需求理論。該理論認為,“當且僅當受眾發現其生活中某一重要需求無法被傳統媒體所滿足、并且認為某一新媒體能夠滿足該需求時,他們才會開始采納并持續使用這一新媒體。”②在本文中,筆者將陌生人社交應用作為新媒體,將QQ、微信等熟人社交軟件作為傳統媒體,探討需求的權衡如何影響用戶的媒介使用行為。
為了深入了解大學生的社交需求和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看法,筆者以面訪和網絡聊天的方式對10 名大學生進行了深度訪談。訪談發現,實名熟人社交是滿足大學生社交需求的主要方式。“我平常使用的社交軟件,一般就是微信和QQ 吧,有時候也會用微博,因為平時生活中聯系最多的就是父母和朋友,基本上都是通過微信聯絡感情,現在QQ 和電話也用的少了”。“社交需求主要還是生活和情感方面吧,而這一塊我不太愿意和陌生人進行交流,把現實生活中的交際關系處理好就足夠啦。”此外,大學生的陌生人社交需求并不強烈,匿名社交承接的更多是負面情緒,這是該群體對陌生人社交應用使用度和忠誠度低的原因。
(二)報償的獲得影響使用意愿
威爾伯·施拉姆曾提出信息選擇或然率公式,這一理論闡釋了某個事物被選擇的可能性取決于費力的程度與獲得的報償。該理論同樣適用于解釋大學生對于陌生人社交應用的使用狀況。
調查顯示,大學生群體對陌生人社交應用的整體使用度和粘度較低。筆者訪談后發現,多數陌生人社交應用在注冊賬號時需要用戶上傳個人照片,提供出生日期、性別等信息,且需經過平臺審核才能注冊成功,使得該應用使用的費力程度增高。而通過陌生人社交應用獲得的需求滿足度認為滿足度一般學生,占41.34%,認為不能滿足自身需求的占15.8%,可見多數學生認為該類應用并不能很好滿足自身的需求,因此對該類應用的使用度和忠誠度并不高。
注釋:
① 許同文:《新陌生人社會的自我呈現與社交邏輯》,《嶺南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4月第37 卷第2 期。
② 鐘家斌:《首都大學生手機報認知使用行為分析》,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傳媒大學,2008年,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