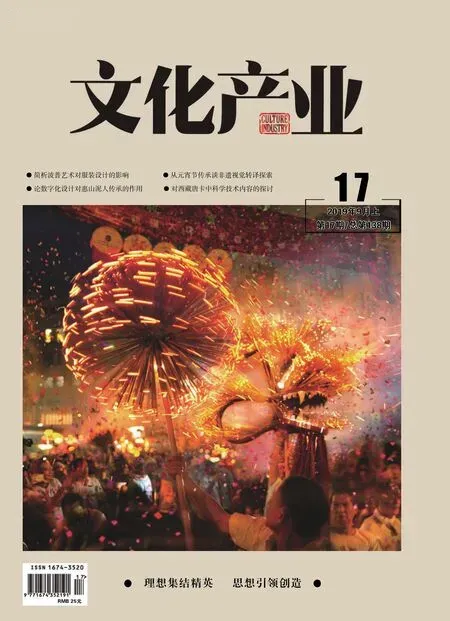學取青蓮李居士
——淺談晚唐詩人譚用之出世入世的矛盾思想
◎王子騰
(上海市控江中學 上海 200083)
譚用之,字藏用,作為晚唐五代直至入宋的獨特詩人,其詩壇地位極其重要。他長于寫景,工于七律,名句“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①廣為流傳。《四庫總目提要》中評“張翼、譚用之善為詩”[1];宋人尹洙《河南集》卷十二載“王(曙)公神道碑銘:譚用之者為之友寢以文稱。”[2]而王曙于景祐元年(1034)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其對譚用之的評價定非虛言;元代大詩人元好問甚至為譚用之留存詩卷全文作注;明人黃佐原亦于其《廣州人物傳》卷四稱:“五代時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為之冠。”[3]明代更是有大量詩人模仿學習譚用之,甚至用其詩集句②。
然而我們對有如此成就的譚用之,知之甚微。通過整理、研讀譚用之的存詩,可以發現其詩歌中表現著濃厚的矛盾思想。其一生周游巴蜀、瀟湘、關中、河洛等地,亦如其詩中所點“學取青蓮李居士”,譚用之不僅周游行跡與李白相似,其詩歌中所表現的入世與出世的矛盾思想亦與李白相似。
一、入世思想:莫學區區老一經
李白畢生渴望建功立業,有著強烈的入世思想。曾寫下“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贈溧陽宋少府陟》)、“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為儒生”(《悲歌行》)等表現出積極求官思想的詩句。幾度出川,三入長安及四處干謁游歷,更是體現其欲建功立業、做帝王師的入世思想。才華不能有所發揮,李白也會發出“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嘲魯儒》)的吶喊,而這正是譚用之所堅守的人生信條。其在《約張處士游梁》中開頭便喊出“莫學區區老一經,夷門關吏舊書生”,告訴友人切莫皓首窮經,定要積極施展自己才華,盡經世濟國之責。對于滿腹經綸卻避世于深山之中的隱士,譚用之嗤之以鼻——“好攜長策干時去,免逐漁樵度太平”。
譚用之一生四處游歷交友甚廣,其交友圈中處士的地位顯得極其重要。處士多指才德兼備卻辭官不仕、隱居深山之人,然而譚用之卻在詩中反復勸其入世乃至用世。譚用之詩《約張處士游梁》單從詩題而論,似乎有與友人相約摒棄功名、歸隱深山之意,然而首聯卻是“莫學區區老一經”的意外之語,萬不可學習古代迂腐冬烘的學究,只知埋首于經書章句之學。這既是對友人的勸勉,亦是自嘲與激勵。另有詩《別何處士陵俊老》,更是反用典故以勸入世。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載:“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君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巢父。”[4]同卷中亦載:”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后隱於市澤之中。堯讓天下于許由……”[5]巢父,許由并稱,均以隱居不仕聞名,然譚用之在此詩中卻將他們作為求索功名的參照物。尾聯“誰人為向青編上,直傍巢由寫一名”中“一名”在唐人語言習慣中特指科舉之名。吳融有詩“始為一名拋故國”(《登鸛雀樓》)、羅袞亦有詩稱頌羅隱“饞書雖盛一名休”(《使兩浙贈羅隱》)。可見譚用之并不掩飾對科考入仕、博取功名的渴望,而反用典故表達入世思想,也正是李白慣用的手法,李白《笑歌行》云“巢由洗耳由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中亦云“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譚用之這種反用巢由之典的詩歌樣式正是對李白詩詞的學習借鑒,李白常于詩中倡導“士當經世濟國”,并不贊同對社會無益的獨善其身。李白在《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明確表態“托意在經濟”,《贈韋秘書子春二首》亦云“茍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假如沒有經世濟俗之志向,即便獨善其身亦毫無用處。譚用之同樣如此:“時人莫笑非經濟,還待中原致太平。”
對那些已經入仕并身居高位的友人,譚用之更是屢求引援。譚用之在《寄徐拾遺》中將自己比作受困于漁人等待解救的白龍,并希望能找到伴和演奏《騶虞》的知音。自己落魄半生、天涯漂泊,贊美徐拾遺有補天大手、深海氣度,渴求得到引薦。“功名盡在長安道”,科舉在晚唐幾乎成了士子的唯一出路,京城的物態繁華、人才濟濟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刺激。“相逢半是云霄客”,而自己卻只是默默無聞一介布衣,只得寄希望于賢士名流的引薦,讓自己得以“鰲逐玉蟾攀桂上”,想著獨占鰲頭、蟾宮折桂之日,也可以“馬隨青帝踏花歸”。然而其科舉之路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一帆風順,“鳳凰聲里過三年”“幾度帝里阻煙波”……因科舉在帝都蹉跎多年,落第期間寓居凈居寺進行夏課備考,干謁行卷不曾間斷,每有得意佳句甚至反復使用,多方投遞。《幽居寄李秘書》中“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在《山中春晚寄賈員外》中又再度使用,譚用之對此句格外滿意近乎自得。對那些春風得意的新晉進士們,譚用之只得投出艷羨的目光,想象著他們“狂歌白鹿上青天”的凌云姿態。
二、出世思想:應看名利似浮萍
作為傳統的儒士,對修齊治平的理想懷揣堅定的渴望。但在現實的殘酷洗禮下,其詩歌又反映出矛盾的出世思想。《贈索處士》詩云:“不將桂子種借天,長得尋君水石邊。玄豹夜寒和霧隱,驪龍春暖抱珠眠。山中宰相陶弘景,洞裹真人葛稚川。一度相思一惆悵,水寒煙澹落花前。”頷聯再度使用玄豹之典,此處卻是表達出世思想。使用同一典故表達完全相反的思想,遠不止這一處。“莫學區區老一經”是明確的入世,在《別洛下一二知己》中卻變成了“應笑區區味六韜”的出世情懷。“直傍巢由寫一名”中表達對功名的思慕,但《閑居寄陳山人》里卻明確表態“應看名利似浮萍”。
曾立志攜長策干時,避免漁樵一生的譚用之,退隱深山又成了他的渴求。“武陵”“桃花”自陶淵明演繹后便成為世人歸隱向往的地方。《貽黃道人》中譚用之構想“他日鳳節何處免,武陵煙樹豐桃花”,想象整日飲酒垂釣的隱居生活,閑暇時在峪中聽鳥雀歡歌。此外,道士也成了譚用之詩中的交往對象,“從此人稀見蹤跡,還應選地種仙桃”(《送丁道士歸南中》)。譚用之本人雖無道籍,卻時常發出“七色花虬一聲鶴,幾時乘興上清虛”(《江邊秋夕》)的道家之語。給友人的書信中,也希望過上“早晚煙村碧江畔,掛罾垂對蓼花灘”(《寄友人》)的閑適隱逸生活。其遇到志同道合的友人時,歸隱之心愈切,寫下“感君巖下閑招隱,細縷金盤膾錯刀”(《途次宿友人別墅》)的詩句。然而這歸隱之心仿佛帶有某種無奈,《月夜懷寄友人》詩云:“劍氣徒勞望斗牛,故人別后阻仙舟。殘春漫道深傾酒,好月那堪獨上樓。何處是非隨馬足,由來得喪白人頭。清風來許重攜手,幾度高吟寄水流。”雖有凌云才華卻無人賞識,與友人分別之后就連志同道合之人也不復存在。春去秋來,只得痛飲狂歌,登樓望月,聊以消遣。四處干謁營求卻一無所獲,在患得患失間反賺得白發滿頭。與友人各在他鄉,相距千里,無從得見,唯將滿腹憂思賦予眼前江水東流。譚用之有時甚至主動招隱別人,“明年二月仙山下,莫遣桃花逐水流”。
三、出世與入世矛盾的原因
晚唐五代的政權更迭以及科舉時興時廢,讓譚用之徘徊在美好的理想與慘淡的現實之間。不論出于客觀還是主觀,譚用之也如其他晚唐士子一般蹉跎科場多年。《寄岐山林逢吉明府》中喟嘆:“鳳凰聲里過三年”;《幽居寄李秘書》中感慨:“幾年帝里阻煙波”;《感懷呈所知》中亦悲鳴:“十年流落賦歸鴻,誰傍昏衢駕燭龍。……早晚休歌白石爛,放教歸去臥群峰。”十多年的漂泊流落,早已將其豪情消磨殆盡。《孟子注疏》卷十二正義引《三齊記》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寧戚疾擊牛角商歌曰:‘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骨干,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旦旦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6]尾聯用此典故,表明自己即將歸隱,亦感慨自己生不逢時的無奈。慘淡的現實讓譚用之的進取之心日漸減損,只得自嘲“官職無才興已闌”(《寄友人》)。個人的體弱多病更是催化了譚用之既想入世又想出世的矛盾思想,“病多慵引架書看”,轉眼時光已逝,年華老去,只得感慨“光陰老去無成事,富貴不來爭奈何”。
對李白的崇拜與學習,也是其矛盾思想的根由之一。“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心,自李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李白始。”[7]龔自珍的評價很是恰當。李白積極入世時便自信地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而當其于現實中屢屢碰壁時,便又說:“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譚用之詩歌中大量滲透著李白式的矛盾思想,當其學習李白積極入世時,其詩歌透露出無限豪情壯志,兩首《塞上》描繪了邊疆沙場的戎馬生活,渴望如李廣一般殺敵報國,創建一番功業。其一尾聯“早晚橫戈似飛尉,擁旄深入異田單”,其二尾聯“橫行總是男兒事,早晚重來似漢飛”,“早晚”的句式在此處飽含著強烈的自信與凌云的氣勢。當現實與理想形成巨大落差時,則又說“早晚煙村碧江畔,掛罾重對蓼花灘”以及“早晚休歌白石爛,放教歸去臥群峰”。此時的“早晚”卻變成了對功名的摒棄與對歸鄉隱居的堅定。李白歸隱后時常想入山訪仙,譚用之亦是如此,“仙舟”“仙桃”“仙山”等詞匯在其詩中被大量提及。甚至李白的俠客思想在譚用之詩中也略有顯現,譚用之《古劍》以七律寫古意,細致描摹了古劍的鑄造過程與逼人的如霜劍氣,并想象執劍俠客氣吞山河的豪情。
當李白滿懷熱情的投身世俗時,其詩中所呈現的欣賞對象便是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諸葛亮(“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生瓊筳”)等治國安邦之良臣。而當其失意灰心時,陶淵明(“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嚴子陵(“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等隱逸之士又常常現身其詩中。譚用之亦是如此,當現實仍給予其希望時,“他日成都卻回首,東山看取謝鯤家”“江上陰云鎮夢魂,江邊深夜舞劉琨”,此時謝鯤、劉琨等便成為他標榜的對象;當現實給予他沉重打擊時,陶弘景、葛稚川等又屢次于其詩中出現。縱觀譚用之一生,看似復雜乃至矛盾的思想,其背后的原因大致與李白相同,均因現實的屢屢受挫而引發一系列激憤之語,最后乃至出世。正如李白所說:“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
【注釋】
①本文所涉詩歌,均參考自《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不再另作說明。
②有明一代用譚用之詩集句的詩人有:程敏政、鄧慶采、江源和郎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