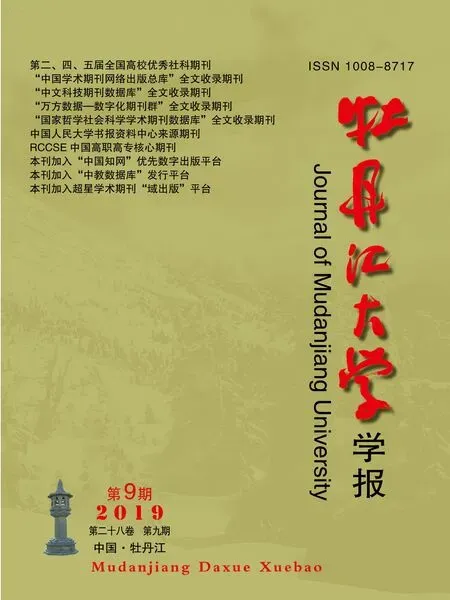論中華民族的“虛化”與建構
馬 宇 飛
(榆林學院政法學院,陜西 榆林 719000)
一、中華民族的“虛化”
(一)中華民族虛化的歷史慣性
王朝國家“家-國”同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不僅是王朝國家的臣民,其政治社會化的生成邏輯,亦是“國”的家族化,即“國”之“公域”與“家”之“私域”之間無涇渭分明的“群己權界”,而是二者重疊互構。“王朝國家,實際上是家庭所有制的擴大,即由財產的家庭占有擴大至‘國家’,形成‘家-國’體制。‘國’是‘家’的放大,而‘家’又是‘國’的縮小,……國家成為某個家庭的私產,即‘家天下’。”[1]“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與我何有哉。”原子化的王朝國家的臣民個體與政治權力中心保持相當距離,他們沒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意愿或能力,有的往往只是對一家一姓之王朝集體無意識的間或順從。“臣民意識到專業化政府的權威,其情感上取向于它,或許不喜歡,或許感到驕傲,其評價它為合法或不合法。但這種關系……是對著該政治系統中輸出、行政或‘向下流’的一面,……盡管存在符合臣民文化能力的有限形式,但基本上是一種消極關系。”[2]同時,異質化、碎片化、“家天下”的傳統社會,王朝國家的“國”之聚合力低下。及至清廷,所謂“皇權不下縣”,族權與紳權的“鄉土秩序”將大量家庭、宗族的糾葛矛盾消解于基層,個體從屬于家庭、宗族,其政治社會化被家庭、宗族、村社等區隔,所謂“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群。……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這割裂、遮蔽了臣民對更高政治共同體的認知與關聯。“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其常言‘天下’,以‘文化中國’之‘天下’兼稱‘國家’,可見其缺乏國際對抗性,折射出其完全不像國家(指民族國家)。”[3]
秦漢之后,以中原王朝為中心觀照天下的層次主要有三:層次一,中原王朝直接統轄的郡(縣),比如,清朝在關內地區設置直隸省、江蘇省、安徽省等內地十八省。層次二,以羈縻、冊封、土司等制度間接統轄的邊疆區,比如,明朝中葉在西藏、云南等西部和南部,在府、縣流官管轄下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置宣慰司、宣撫司等地方行政機構,委任當地民族頭人為長官,即為‘土司’。層次三,與中原王朝以經濟關系——貢物與回賜;禮儀關系——封典為主的兩國間禮儀形式;軍事關系——互相求兵或出兵等為表征的朝貢國,例如,朝鮮、安南、琉球等。這三個層次即為華夏文化澤被的“化內之地”,即為“天下”。但“天下”并非“世界”,因為,“世界”尚有中華無法企及的“化外之地”,例如,異域的大食等。而且,“化內”與“化外”二者之間的界線是相對的,即處于動態的變化中。因此,王朝國家的疆域邊界時有盈縮、模糊不定。作為社會存在的“王朝國家”自身就模糊不定,而且,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生者不遠別,……墳墓多繞村”的王朝國家臣民個體的“認知地圖”里,何談國家認同,何談中華民族的認同?
由此,對于王朝國家時期的“中華民族”,一方面,筆者贊同:晚清之前中華民族的非實體性,即處在由“自在”向“自覺”的過程中,而“自覺”的“中華民族實體”是晚清之后的重新建構;另一方面,誠如史密斯所言:“現代的民族主義‘國族’非憑空而來,而是在原有族群傳統基礎上‘顯影’的‘重新建構’”,即王朝國家時期各個民族事實上“自在”同存共生。因為,晚清之前中華民族的虛化,所以,“國族”,即中華民族的“建構”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是,國家建設,即國家政治組織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設;二是,國族建設,即在不同族屬的國民中間建構一體性的“國族”共同體。
(二)中華民族的日常性虛化
“中華民族”的主要理解之一是:支撐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作為一個族體單位“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其是伴隨著中國民族國家的形塑而形成,而且,是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中流砥柱功用的“政治民族”。但是,中國當下的實際:“則是更多強調‘國族’中的各個民族,尤其是各個少數民族的族體意義與族性,遲滯了國族建構,導致國族建構的虛弱甚至虛幻化。”[4]“改革開放前,我國民眾鮮有機會在國際事務中直接體會到‘中國公民’的現實意義,而且,在國內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種優惠政策與民族制度,使得少數民族身份的現實意義顯著,結果客觀上‘中華民族’被架空和虛化。”[5]例如,我國幾十年如一日地在課堂上、期刊上、報紙上等宣講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介紹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介紹斯大林的“民族”界定,導致一些人產生如下“民族意識”:(1)希求培育和發展“本民族經濟”;(2)力促本民族語言在學校中的使用;(3)排斥其他“民族”成員遷入本民族的“自治地方”;(4)力主通過風俗、宗教、歷史教育等增強本民族的凝聚力與“民族意識”。以上這些又直接吻合斯大林的“民族”定義。而如此宣教的直接結果就是將國人的“民族觀”定位于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而非包含所有國人的“中華民族”。
同時,在黨和國家的官方文本(文件)中常見的政治語言是:中國人民、各民族公民、各少數民族、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中國各族人民、中國(全國)各民族等的表述。而在學界,“現行之民族理論大體都是圍繞維護少數民族權益展開,而相關中華民族的論述卻付之闕如,……吊詭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理論中無中華民族理論。這種民族理論(政策)長期施行,漸成一種特殊政治文化:凡是增益少數民族權益之言行,皆支持、鼓勵,甚至縱容;凡是損益少數民族權益的言行,哪怕是學術探討,皆壓制、批判,甚至打擊。”[6]這導致:其一,原本為“文化民族”“中華民族”的主體構成,即56個族群的“政治民族”意涵日益突出;其二,“國族”之中華民族的概念和實體地位遭到質疑,悖反的是代之以“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統稱”的觀點;其三,原本于新中國初期基本解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問題,在時下的國家建設中反倒又成了問題。此外,從漢族、各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關系角度區劃的“族屬民族主義”的分裂勢力,例如,“疆獨”“藏獨”的身心之游弋。 “一中為忠,兩中為患”,民族認同與國族認同之間的角力,加之“中華民族”的虛化、懸空,這將進一步引致中國國民的身份歸屬感、政治歸屬感等不同程度上的弱化,這又將加劇族際間的“離散化”傾向。總之,“中華民族的虛化傾向明顯,中華民族被解構的風險在增加,任由其發展,中華民族將無法規約各民族群體的訴求,無法發揮對國家統一和穩定的支撐功用。”[7]
二、中華民族的建構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其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以維護祖國統一為根本原則。這是因為,尤其是我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祖國統一、族際團結、社會安寧是全體國民的最高福祉。“團結統一是福、分裂動亂是禍”,正如,“在亨廷頓看來,如果美國不能首先在國內解決‘我們是誰?’這樣一個美國特性(美國國家認同)的問題,那么,在這個充滿‘文明沖突’的世界中,美國不僅將無法匹競其他文明,甚至自己都會面臨‘解體或根本變化’之虞。”如果中國國民缺乏統一的“身份意識”,沒有明晰的國家認同,國家將如馬克思語境下的“一袋馬鈴薯”,最終結果,甚至陷于四分五裂。基于“千年、百年來,維護并拓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如既往地是中華民族甚于一切的政治愿景、道義情感與精神寄托,一如既往地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主流。”對此,筆者認為,時下維護祖國統一、族際團結,“謀篇布局”的體現之一,即是“五個認同”的中國話語。
其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是要弱化中華民族虛化的歷史慣性。通過回溯中華民族千年的歷史景深反推“如何理解中華民族”。例如,“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即是于歷史過程中的各個族群交往、交流,通過“去族群身份”的交融,“滾雪球”般地逐漸形成。亦要消減學界的理論斑駁:即溯源中華民族如何從原生性族群的事實性共生,而且,在此基礎上,順應世界體系“國族”之趨勢,保持“對他而自覺為我”的“連續性”。共性地歷史敘事、共性地集體記憶,彰顯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屬性意義上的多個民族、政治屬性意義上的同一個國族”的政治共同體,是一個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是一種飽經歲月洗練后全體國人共同的價值守望。各個民族在歷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但是,又非凝滯固化,而是在歷史的進程中遷徙流動、通婚互融,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器物制度等方面持續地交相滲透,繼續“交往、交流、交融”。即建構一個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國家”,相應地弱化各個“民族”的個體“民族意識”,以“中華民族”為共性“民族意識”,以此進一步強化各個“民族”之間的互為認同。
(二)同質性“國家建設”
其一,理性吸納“公民模式的民族主義”。“安東尼 ?史密斯將源起于西歐的民族主義歸類于‘公民模式的民族主義’,其強調領土、法制與公民權;而將亞洲等國被動仿效的民族主義歸類于‘族群模式的民族主義’,其強調血緣、語言和傳統文化。”[8]而在蘇聯解體前夕,其主體族群俄羅斯族同少數民族聚居區存在發展落差。引致少數民族受歧視的聯想,俄羅斯族亦因為傾斜性民族政策而心懷不滿。一旦蘇聯解體,所有族群竟都歡呼雀躍!因此,“要在不同人群之間凝聚共同的國家意志,就要保障全體公民不分階層、族群,皆能均等地參與國家生活,均等地享有公民權利。……現代國家成為民族集合體的關鍵,就在于人和人之間打破任何身份限制,通過互相讓渡主權訂立契約,平等擁有并行使公民權,并由此形成公民對民族國家的忠誠。”[9]由此,同質性“國家建設”的出發點,就是由“族群模式的民族主義”理性吸納“公民模式的民族主義”。
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其基礎的政治屬性是“國民身份”,與“國民身份”相對應是法律屬性的“公民身份”。因此,擁有一國國籍之“國人”個體,往往是“國民”與“公民”的二重角色。作為“國人”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的享有,不是基于其“族屬”身份,而是基于同質性的“公民”身份。因此,吸納“公民模式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每個國民都應該享有人人享有的,與最廣泛基本自由體系相兼容類似自由體系相一致的平等權利。“自由只能為了自由的緣故而被限制”。即不能忽略每一個“公民”個體,保障其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語言權、文化權、發展權、受教育權等基本公民權。推進“法治”,完善個體公民權的保護。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安排,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這種不平等可以合理地被期望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這要求,我國在保障全體國民個體“公民權”的同時,并非完全排斥“族際主義”的民族政策取向,而是要務實考量疆域內各個族群之間事實上的發展差距。例如,契合鄧小平“兩個大局”戰略布局政府間橫向資源配置的“對口支援”政策等(“政策”,一般蘊含著特定價值取向與社會設置的規則)。但是,其政策制定之依據,不是基于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而是不同社會成員(或群體)因占有社會資源不同所引致的“社會分層”,以及合作共贏的“區域倫理”等,從而,跳出基于“民族身份”的窠臼。
其二,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加之,“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禮記·王制》),由此,“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的中華文化自信。時下,中華文化的內部,其歷史譜系、神圣記憶正在借用新的符號系統,完成時代特色的重述、重構。“漢族認同少數民族文化為中華文化,少數民族亦認同漢族文化為中華民族文化”。誠然,不可沙文式的強制性認同,但列寧說,自然發生的同化過程是一種進步。綿綿用力、久久為功,例如,在教科書中,以及調整法律、法規、政策中不利于“五個認同”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本符號。比如,教學內容上,我們尊重族群(個體)間的異質性,但我的“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國族”是“中華民族”,我的“民族”是苗族或藏族等,這類似于我的“省籍”是某省,但并不相斥我的“國籍”是中國。再如,以“語言之同質性符號”為例,在民族地區按照現代化教育標準,建設“雙語”(漢語為“國語”)師資培訓學校、職業學校、中小學和雙語幼兒園等;建設“雙語”學習智慧教室與遠程信息化平臺,打造“四個中心”,即“雙語”課程教材研發中心、教學研究中心、教育質量評估中心、教育成果推廣中心。以“教學內容”“語言教育”等為抓手,共享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共享中華民族共有歷史記憶、共享現代文明的發展“紅利”、共同生活在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屋頂”之下。借用柏拉圖“知識就是回憶”之喻,即喚起并清晰于歷時性上,早已存儲于中國“公民”心靈中同質性中華民族的“認知地圖”和“心理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