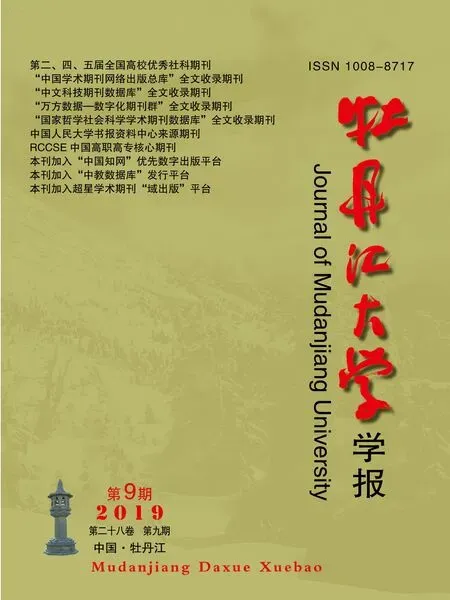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紅葉》:印第安文化的墮落
康 杰 范若孜 王書戎
(中國礦業大學外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1 引 言
印第安人形象在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小說中占有重要地位,印第安人的歷史、神話和傳說是福克納小說創作的重要素材之一。福克納在《紅葉》《公正》《求愛》《瞧!》《去吧,摩西》和《修女安魂曲》等幾部作品中對印第安人形象著墨甚多,描勒了印第安人對于白人入侵他們的家園所采取的應對態度,白人解決印第安人“問題”的方式方法以及印第安人的遷移對約克納帕塔法人的后代所產生的影響,為讀者展演了“約克納帕塔法”王國中印第安人歷史的消亡和白人以及黑人歷史的開端。
《紅葉》是福克納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是一個關于約克納帕塔法印第安人的故事。其時間背景是19世紀初,一個名叫伊塞提貝哈的印第安酋長死了,依照印第安人的古老宗教習俗,酋長生前的馬、獵狗以及貼身黑奴都要為他陪葬。黑奴逃走了,于是印第安人采取了一系列的追捕行動。黑奴最后被印第安人抓住,不得不接受悲慘結局。小說的敘述者在印第安人的視角和貼身黑奴的視角之間來回跳躍轉換,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雙重視角,使我們看到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他們各自與歷史的關系。
2 消極怠惰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文化的墮落反映在方方面面,文化的墮落實際上已經摧毀了他們以前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越來越怠惰,他們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然而,歷史上的他們卻是了不起的勇士,因此,可悲的現實在他們身上就顯得更加悲慘。敘述者將三籃和路易斯·貝里這兩位印第安人描述為:“身材矮胖,有點結實,像城市居民;大腹便便,腦袋碩大,灰褐色寬寬的大臉盤。”[1]518莫克圖貝身上所體現的特征,與傳統意義上印第安酋長所具有的勇士首領的種種特質有著天壤之別。他身高僅有五英尺多一點,體重卻重達二百五十磅。印第安人放棄了以打獵為生的生活方式,開始在種植園里定居下來。惰性主宰著他們的生活,從他們的身體狀況可以看出他們缺乏活動。印第安人的穿著看起來不倫不類,因為他們將自己的傳統服飾和從白人商人那里購買的衣服與飾品混搭在一起。追捕貼身黑奴的兩個印第安人穿著襯衫,戴著草帽,一只胳膊下夾著卷得整整齊齊的褲子,這是福克納筆下的印第安人所共有的一個習慣。莫克圖貝的服飾包括一件雙排扣長禮服、一條襯褲和伊塞提貝哈從巴黎帶回來的一雙紅跟拖鞋。在莫克圖貝的所有穿戴物品中,最能象征印第安人墮落的物品就是這雙紅跟拖鞋,它們意味著印第安人有意識地割裂了自身與土地的聯系。
莫克圖貝繼承了由他的祖父杜姆拼湊起來的汽船屋作為他的住所。小說中的河流象征著印第安人的古老原則:強壯威武和富有活力,當印第安人拋棄這些原則時,他們宛如離開水面的汽船一樣,他們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慢慢地變得支離破碎。當三籃和路易斯·貝里請莫克圖貝帶領他們追捕貼身黑奴時,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位新酋長與這座舊汽船屋之間的相似之處。莫克圖貝肥碩無比,一動不動地坐在木條椅上。他身穿一件絨面呢上衣、一條襯褲和一雙紅跟拖鞋,這雙拖鞋因年代久遠已經開裂,同時又被他那雙肥腳撐得變了形。汽船本應在河流中劈波斬浪,但它卻被固定在磚墻上,里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廢舊物品、生銹器具、鍍金床和斗雞的糞便,船上的木質結構已經腐朽,床上的鍍金也已剝落,百葉窗年久失修,破敗不堪。莫克圖貝就像這艘汽船一樣,本應充滿活力,英勇無敵,但卻因自己的毫無節制和停滯不動,連同整個部落的印第安人,都變得身體超重、遲鈍怠惰和愚昧落后。
小說的第二部分描述的印第安人的簡史表明,印第安文化的墮落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杜姆獲取權力的詳細過程清楚地表明,他篡奪酋長的頭銜是他的部落文化隨后墮落的主要原因。在成為頭人之后,他為部落獲得了更多的黑奴,這也加速了印第安文化的墮落。到他死的時候,對于印第安人而言,照顧黑奴已經成為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在一次討論該如何對待黑人的會議上,部落的長老們決定從事蓄奴和販賣奴隸的生意。正如羅伯特·芬克所言,“這種毫無目的地追求物質財富的荒謬做法已經到了極端不合邏輯的程度。”[2]從販賣黑奴的生意中所獲得的資金成為印第安人加速自身文化墮落的另一誘因。伊塞提貝哈用販賣黑奴賺來的錢出國旅行,國外文明的種種誘惑導致了他進一步的墮落。印第安人越是模仿白人的生活習慣,他們就越遠離自己與荒野的原始關系。為了維持傳統生活方式的表象,他們訴諸于對榮耀和禮儀的盲目忠誠。但是,缺少了荒野對生命的滋養,印第安人的榮耀和禮儀已經成為空無一物的軀殼。
3 充滿生命活力的黑人
與印第安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貼身黑奴與其他黑人的身上卻體現出無限生命活力。貼身黑奴身手敏捷,反應機敏,而且具有長距離奔跑的能力,身體狀況極佳。如若不是身中蛇毒,印第安人可能要花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能抓到他。當他看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時,他會立即采取行動,以此來不斷增強自己忍耐的意志力,有一次他竟然吃了一只活老鼠來充饑。當他被蛇咬傷之后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之際,他才徹底明白自己對生存的渴望是如此地強烈,為了防止蛇毒擴散,他竟砍掉了受傷的胳膊。貼身黑奴在逃跑時“只穿著一條印第安人從白人那里買來的粗布褲子,腰間的皮帶上掛著一個護身符”。[1]534逃離種植園之后不久,他脫下褲子,在身上涂上一層泥,以防蚊子的叮咬。他用泥巴而不用從白人那里買來的衣服保護自己,這一行為頗具象征意味,因為泥巴這一天然的保護層暗示了他與大地的緊密聯系。他的護身符包括兩件物品,一件是半幅伊塞提貝哈從巴黎帶回來的珍珠母眼鏡,象征著他與伊塞提貝哈的終身契約;另一件是一個水腹蛇的頭骨,象征著他與蛇的圖騰關系,他對它們懷有崇敬之情,因為他曾經吃過一條蛇來維持自己的生命。或許他在非洲的童年時期就學會了以這種方式來尊重動物的生命,但是在美國,他的印第安主人的做法肯定也強化了他的黑人導師在這方面對他的言傳身教,因為非洲和美國的原始民族都以圖騰關系來表達對所有生命的尊重。當水腹蛇咬傷他之后,他對它說道:“哦,祖先,”[1]538這也表明水腹蛇即是他的圖騰。蛇是生殖力、運動力和生命力的傳統象征,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貼身黑奴身上所具有的相似特征。他們最相似的特征在于他們與土地的親密關系,一個是身體上的親近,一個是精神上的親近。
位于汽船屋中央的小屋是黑人的主要聚集地,他們在屋里存放著舉行非洲宗教儀式所需的祭祀物品,每當月亮盈虧到某種形狀時,他們就匯聚在這里開始祭祀儀式,在夜幕降臨后將儀式轉移到存放儀式鼓的小溪盡頭,鼓是黑人來到美國之前的非洲生活的最珍貴的象征。他們在荒野中比在種植園中更有家的感覺,他們拒絕割舍與森林的原始神圣關系,因為森林是他們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傳統來源。汽船屋象征一種毫無意義的禮儀,對于印第安人而言,實質上意味著他們自身文化的結束。對于黑人來說,在中央小屋舉行的儀式只是他們在荒野中無拘無束地慶祝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以及各種活動的開始。
4 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對比
福克納通過光明與黑暗、有聲與無聲、運動與靜止的反差來表明黑人的生命活力與印第安人的怠惰散漫之間的鮮明對比。在追捕過程中,光明與黑暗的傳統象征意義在貼身黑奴身上發生了反轉。黑暗通常與惡魔、邪惡、罪惡、毀滅、無知和死亡聯系在一起,但是小說中的黑暗卻為貼身黑奴的逃跑提供了掩護。他總是在太陽下山后開始逃跑,白天的時候他就躲藏起來,因為他害怕光明,此時的光明對他而言意味著暴露、俘獲和死亡。通常情況下,印第安人似乎只有在白天的光照下才感到舒適自在。當他們在黃昏后接近沼澤中的貼身黑奴時,他們變得害怕起來,決定等到第二天早上再抓他。當意識到自己無法逃脫時,貼身黑奴不再對白晝有任何的恐懼。黎明時分,印第安人回到沼澤,發現黑奴仰望著冉冉升起的太陽用自己的本族語唱著一首歌。面對死亡,他頌揚著陽光給予生命的力量。
有聲的和無聲的形象意義也發生了轉變。當三籃和路易斯·貝里討論黑人的無禮和野蠻本性時,坐在他們面前的黑人在中央小屋里默不作聲,從而間接地幫助了逃跑的貼身奴仆。他們的沉默不語表達了他們作為一個族群的團結一致、他們對同族兄弟的忠誠以及他們對印第安禮儀的蔑視。對貼身黑奴而言,聲音代表著被抓和被殺后他將失去的那些東西,最重要的就是他與荒野的聯系。當他靜靜地躺在谷倉里等待主人死去時,他聽到了三種聲音:小溪盡頭黑人們的儀式鼓的咚咚聲,“老鼠沿著溫暖的、老朽的、斧砍的方椽爬過時爪子發出的窸窣聲”[1]533以及伊塞提貝哈的獵狗的嚎叫聲。鼓聲讓他想起部落的慶祝儀式;窸窣聲讓他記起曾經吃過老鼠來維持生命;獵犬的聲音讓他回憶起和伊塞提貝哈一起打獵的情景。
福克納采用運動意象來展示貼身黑奴的生命活力。敘述者反復提到貼身黑奴的奔跑,這是他的生命活力和忍耐意志力的最重要的標志。無論他走到哪里,他都能見證生命的運動。被印第安人抓獲之后,貼身黑奴仍然盡其所能地緊緊抓住生命的律動不放手。他努力地吃東西,不停地咀嚼,但食物從嘴里滑落,流到下巴、脖子和胸口上。盡管恐懼妨礙著他去做這些基本的生命運動,但是他的強烈的忍耐意志力強迫自己的身體去模仿吃喝的動作。福克納采用靜止的意象來描繪印第安人的消極被動和墮落腐化。印第安人喜歡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行動,很少在意時間的流逝。黑奴每次看到追趕他的印第安人時,他們總是一邊磨磨蹭蹭地走路,一邊不停地抱怨追捕的工作。當印第安人把貼身黑奴圍困在沼澤地里時,他們并不急于抓他,“我們會給他時間……明天不過是今天的另一種叫法而已。”[1]540第二天早上,他們一動不動地蹲著,直到黑奴對著太陽唱完歌。時間不會打擾印第安人,因為部落的儀式已經預先注定了黑奴的命運,這也是印第安人墮落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故事由始至終體現了福克納對儀式行為的高度重視:他對黑人抱以同情,同時感到印第安人為了生存也需要繼續他們的儀式,盡管奴隸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舊的風俗。”[3]空洞儀式的停滯不前已經使印第安人的個體人格失去了活力,他們已經無法適應部落中發生的變化。福克納曾說,“紅葉指的是印第安人。它是曾經窒息、壓抑和摧殘過黑人的自然的蛻膜脫落,沒有人能夠阻擋它。”[4]
5 結語
通過印第安人形象與黑人形象的對比,福克納繪聲繪色地描寫了印第安文化無可挽回的墮落。他們的文化如朽木死灰一般,已經墮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他們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是他們自己的世界(沒有白人和黑人),另一個是與白人和黑人共存的世界——他們試圖同時生活在這兩個世界里。從《紅葉》中我們可以看出,印第安人采用了許多白人定居者的方式,尤其是奴隸制。效仿白人的奴隸制是印第安文化墮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印第安人將這些新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種種不適均歸咎于白人,而非他們自己。《紅葉》所體現的諷刺意味在于:印第安人為了維護部落榮耀而采取的行動戲劇性地表明,作為一個部落,他們已經永遠失去了這種榮耀。通過《紅葉》中所塑造的印第安人形象,福克納表明,印第安文化的墮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最重要的兩個原因是白人的侵略性與印第安人的被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