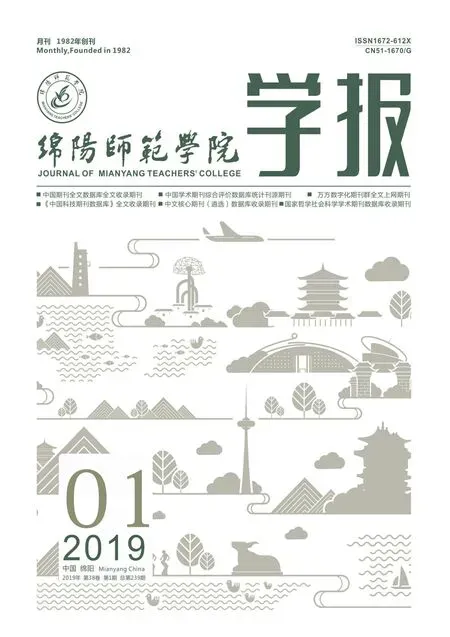王維、李白未交游原因考釋
李 歡
(河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河南開(kāi)封 475001)
通過(guò)對(duì)李白、王維流傳后世的詩(shī)文著作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二人在其詩(shī)文著作中并無(wú)互相酬唱、應(yīng)和之作,更甚之,二人的詩(shī)作中歌詠同一事件的作品也沒(méi)有。考其年譜,二人生卒年極其相似,但是這兩位生卒年高度重合的詩(shī)人竟然毫無(wú)交集,不得不說(shuō)是盛唐詩(shī)史上的一大憾事。據(jù)《李白年譜》記載,白入長(zhǎng)安之因是:“多次謁見(jiàn)裴長(zhǎng)史,因遭人讒謗,故上書(shū)自白。終為裴所拒,遂有入長(zhǎng)安之念……初夏,往長(zhǎng)安。”[1]30此時(shí)為公元730年,入長(zhǎng)安后的李白因求謁未果,生活困頓而不得不于731年初夏離開(kāi)長(zhǎng)安。《王維年譜》載王維“730年,閑居長(zhǎng)安……731年,閑居長(zhǎng)安”[2]53。這是第一次二人有交游的可能。第二次有交游可能的時(shí)間為公元742至744年。公元742年,改元天寶,普天同慶,李白奉召入長(zhǎng)安為翰林供奉,744年被玄宗“賜金放還”,這一時(shí)期,王維亦在長(zhǎng)安為官。總的來(lái)說(shuō),二人有交游可能的時(shí)間段共兩次:一次是在公元730至公元731年,李白初入長(zhǎng)安。另一次是公元742年至公元744年,白奉命二入長(zhǎng)安。二人三年內(nèi)(李白于公元730年夏入長(zhǎng)安,731年秋已經(jīng)在洛陽(yáng),此為一年。742年秋赴長(zhǎng)安,744年三月離長(zhǎng)安,此為兩年。共三年。)竟然毫無(wú)交游痕跡,對(duì)造成這一歷史憾事的原因有進(jìn)行討論的必要。
一、政治地位方面
727年,李白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shū)》中表達(dá)自己的政治理想:“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職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3]1225但是他選擇的進(jìn)身之階并非是受士大夫青睞的科舉之路,而是希望通過(guò)“平交王侯,而一匡天下,立抵卿相”。白入長(zhǎng)安后的交游、干謁之作,也是圍繞著他的這一人生理想進(jìn)行的。通過(guò)對(duì)李白在長(zhǎng)安的諸如《玉真仙人詞》《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zèng)衛(wèi)尉張卿兩首》等贈(zèng)答、干謁之作,可以看出此時(shí)他所來(lái)往的是以玉真公主、張說(shuō)父子、崔氏家族為代表的上層權(quán)貴。除了贈(zèng)答、干謁之作,初來(lái)長(zhǎng)安的李白的詩(shī)作大多通過(guò)比興、寄托的手法來(lái)表達(dá)他對(duì)天子的忠誠(chéng)與自己身不遇之哀,如《長(zhǎng)相思》《秦女卷衣》等。由于此時(shí)的李白人微才名亦不顯,他初次的干謁之行并不順利,寓居于終南山玉真公主別館時(shí)頗受冷遇。《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zèng)衛(wèi)尉張卿二首》揭示出李白此時(shí)期干謁無(wú)門(mén)、生活困頓的窘境,“獨(dú)酌聊自勉,誰(shuí)貴經(jīng)綸才”[4]120是李白知音難遇、不得賞識(shí)的愁怨與無(wú)奈;“饑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jiǎn)”[4]122是此時(shí)期李白困頓生活的真實(shí)寫(xiě)照。這樣的遭遇給李白帶來(lái)很大的打擊,730年秋,失意的李白開(kāi)始岐、邠之行,之后游于坊州,于731年春歸長(zhǎng)安,之后便不再致力于干謁,作品多是抒憤之作。往來(lái)之人大多具有俠客風(fēng)范,有《俠客行》《少年行》等作品流傳。
王維于公元718年赴京兆府試,獲解頭。721年春,進(jìn)士及第,為太樂(lè)丞,后因“伶人舞黃獅子”牽連被貶,輾轉(zhuǎn)濟(jì)州、淇上等地為官,政治生活頗為坎坷。迫于生計(jì),不得不在地方上作一些小官。728年得以返回長(zhǎng)安,但是回京途中妻子逝世,在政治坎坷與妻子逝世的雙重打擊之下,王維逐漸萌生了歸隱之意。李白730年到達(dá)長(zhǎng)安時(shí),王維已經(jīng)閑居長(zhǎng)安,過(guò)著“避世”的生活。他早年雖與寧王等人交好,但是在玄宗限制官員與貴族交往的禁令的影響下,再加上王維在外數(shù)年,早已物是人非,此時(shí)王維與這些諸如張說(shuō)、玉真公主之類(lèi)的上層貴族并無(wú)交集,李白自不會(huì)去訪問(wèn)一個(gè)無(wú)官無(wú)名的避世之人。
公元742年春,“正月丁未朔”,唐玄宗親撰《改元大赦文》[5]427-428,詔令大下,“改開(kāi)元三十年為天寶元年”,大赦天下的同時(shí),給“內(nèi)外文武官九品己上,各賜勛兩轉(zhuǎn)”。此時(shí)任監(jiān)察御史的王維,被擢升為侍御史。李白在玉真公主、吳筠等人的舉薦下,使得唐玄宗專(zhuān)門(mén)下詔書(shū),征召其進(jìn)京。對(duì)于此次進(jìn)京,李白一句“仰天大笑出門(mén)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足以表明其樂(lè)觀與自信。李白二入長(zhǎng)安,本就是奉召而來(lái),之后又受到玄宗非凡的禮遇,對(duì)此,李陽(yáng)冰《草堂集序》記載:“天寶中(初),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攆步迎,如見(jiàn)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diào)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聯(lián)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于翰林中,問(wèn)以國(guó)政,潛草制誥,人無(wú)知者。”[6]1789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一文:“天寶初,召見(jiàn)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葷步迎,如見(jiàn)綺、皓。論當(dāng)世務(wù),草答蕃書(shū),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wú)比侍。遂直翰林,專(zhuān)掌密命。”[7]1780-1781根據(jù)文本互證的方法,證明事件存在的真實(shí)性。李白詩(shī)集中也有不少詩(shī)句表達(dá)他此時(shí)受到的恩遇,“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緩來(lái)相趨”,“救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luò)頭白玉鞍”等詩(shī)句,足以證明李白此時(shí)的地位、聲勢(shì)這些使其極度的自信與自負(fù)得到了滿(mǎn)足。
與李白相比,此時(shí)的王維,人微言輕,甚至不具備參加一些宮廷活動(dòng)的資格。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寶三年為賀知章舉行的餞行宴會(huì)。《全唐詩(shī)·卷三》著錄唐玄宗《送賀知章歸四明并序》載:“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聯(lián)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稗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huì)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mén),寵行邁也。”[8]568此篇序表明參與此次活動(dòng)的是“六卿庶尹大夫”,同時(shí),此次宴會(huì)除李白外,其余人皆為“六卿庶尹大夫”,顯然王維作為低級(jí)官吏且與賀知章過(guò)從甚疏,是沒(méi)有資格參與此次宴會(huì)的。因此,身份地位的差異是二人不能相見(jiàn)的一大原因。
二、交游群體不同
通過(guò)對(duì)王維生平經(jīng)歷的分析,發(fā)現(xiàn)他從714年離家游長(zhǎng)安之后,除了最初貶官和出使塞外的幾年,長(zhǎng)期居于長(zhǎng)安。如此,王維可稱(chēng)得上是一個(gè)地道的長(zhǎng)安居民。他早年雖與岐王等上層權(quán)貴交游唱和,但是開(kāi)元八年十月玄宗發(fā)布了一道禁約諸王和諸大臣交游的禁令,之后王維貶官,離開(kāi)了生活數(shù)年的長(zhǎng)安。從王維詩(shī)文來(lái)看,經(jīng)過(guò)貶官之后,其相互交游唱和之人變成了以祖詠、嚴(yán)秀才、孟浩然為主的失意文人,并一些山間隱士,如崇梵僧、焦道士等。李白初入長(zhǎng)安時(shí),王維正隱于嵩山,日常和山中摯友來(lái)往唱和,如崔興宗、韋給事等人。各種事實(shí)表明,此時(shí)的王維功名之心日減,著意于山水田園,不問(wèn)世事。與之相反,初來(lái)長(zhǎng)安的李白,為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著重于仕途干謁,致力于和上層貴族交往唱和。王維這樣一個(gè)隱居嵩山、不問(wèn)世事的閑居之人自不會(huì)得到李白的拜訪。同樣,王維隱居于嵩山,與山間隱士唱和應(yīng)答,也不會(huì)與一個(gè)剛?cè)刖┏遣坏弥镜脑?shī)人來(lái)往。
742年秋,李白奉召入京,得到賀知章的高度贊譽(yù),《新唐書(shū)·文藝傳》記載:(李白)“往見(jiàn)賀知章,知章見(jiàn)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9]5762-5763隨著李白在京城名聲大噪,他來(lái)往之人皆為社會(huì)名流,據(jù) 《新唐書(shū)》載李白在待奉翰林期間,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yáng)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9]5763。而杜甫的《飲中八仙歌 》之“歌”,又可與此互為印證。除此之外,據(jù)《李太白全集》《新唐書(shū)·李白傳》《唐才子傳》等文獻(xiàn)記載,李白在京城來(lái)往頻繁者還有音樂(lè)家李龜年、司勛員外郎盧象、獨(dú)孤駙馬、徐王李延年以及盧郎中、集賢院諸學(xué)士等人,皆為一時(shí)名流。王維則與之相異,據(jù)其年譜記載,公元743年,維與王昌齡、王縉、裴迪集長(zhǎng)安青龍寺懸壁上人院共賦詩(shī),維詩(shī)題曰《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2]91。觀其此時(shí)期詩(shī)作,大多是與友人相互贈(zèng)答之作,所來(lái)往的是諸如綦毋潛、張諲等失意文人。這樣看來(lái),二人的交游團(tuán)體可以說(shuō)是封建社會(huì)的兩個(gè)階層,那么,二人見(jiàn)面的機(jī)會(huì)則寥寥無(wú)幾。所以說(shuō),二人來(lái)往唱和之人的不同也是二人未交游的原因。
但是從二人的詩(shī)文集、年譜等現(xiàn)有資料分析,二人交友亦有很多重疊處。
孟浩然是為一例。公元726年,白二十六歲,結(jié)識(shí)孟浩然,當(dāng)年并無(wú)詩(shī)作流傳,但《李太白年譜》記載:由汝海南來(lái)時(shí),或曾往襄陽(yáng),結(jié)識(shí)孟浩然。兩年后(728年),有《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shī),得稱(chēng)孟為“故人”[1]26。就孟浩然和李白之間的感情來(lái)說(shuō),二人的感情并不是很深厚,后世流傳下來(lái)的李白寫(xiě)給孟浩然的詩(shī)作有五首,而孟浩然詩(shī)文集中卻無(wú)一首作品是回應(yīng)李白的。從具體詩(shī)作分析,李白對(duì)孟浩然更多的是敬仰,有詩(shī)“吾愛(ài)孟夫子”“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等為證。通過(guò)對(duì)《新唐書(shū)》《唐才子傳》等史料進(jìn)行分析,可以看出王維與孟浩然感情甚篤。二人相識(shí)于730年,《新唐書(shū)·文藝傳》載:嘗于太學(xué)賦詩(shī),一座嗟伏,無(wú)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chēng)道之[9]5779。孟浩然落第還鄉(xiāng),維作《送孟六歸襄陽(yáng)》詩(shī),勸其不必再干謁投獻(xiàn),回鄉(xiāng)躬耕、讀書(shū)、隱居:“杜門(mén)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zhǎng)策,勸君歸故廬。”[10]84《新唐書(shū)》對(duì)孟浩然的記載是二人過(guò)從甚密的一個(gè)證據(jù),而王維為孟浩然送行所作之詩(shī),則是站在摯友的角度對(duì)朋友的規(guī)勸,二人感情之深可見(jiàn)一斑。所以,孟浩然的私人感情并不足以成為二人結(jié)識(shí)的依據(jù)。從孟浩然之后的行跡來(lái)看,在王維、李白均在長(zhǎng)安時(shí)并未到長(zhǎng)安。因此,孟浩然不足以成為二人相識(shí)的媒介。
玉真公主都曾舉薦過(guò)二人,李白第一次入長(zhǎng)安時(shí)住在玉真公主別館,第二次入長(zhǎng)安亦是受到了玉真公主的舉薦,因此,玉真公主稱(chēng)得上是李白世宦生涯中的貴人。據(jù)《唐才子傳校箋》中記載,王維于公元721年應(yīng)試獲“解頭”,也離不開(kāi)玉真公主的推薦。玉真公主喜王維“善音律”而放棄本來(lái)推薦的張九皋,對(duì)公主來(lái)說(shuō),求入其門(mén)下的士人何其多,推舉何人只是憑借喜好罷了。至李白到長(zhǎng)安居玉真公主別館時(shí),公主可能已經(jīng)不記得王維是何人了。
所以,二人的交游重疊不足以成為二人有交集的媒介。
三、個(gè)性信仰的差異
《新唐書(shū)·文藝傳》寫(xiě)道:“維弟兄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彩。”[9]5765《唐才子傳》同樣寫(xiě)道:“篤志奉佛,蔬食素衣。”[11]300王維奉佛可見(jiàn)一斑。與王維不同,李白崇道,他的為人處世中帶有道家的憤世嫉俗與灑脫肆意,《盛唐三大家異同與出現(xiàn)意義》中說(shuō):“李白曾加入道教,但卻不是純粹的道教徒。他的入道與唐玄宗張揚(yáng)道教不無(wú)關(guān)系。可以說(shuō)道教不過(guò)是他設(shè)法盡快干預(yù)政治的工具或者敲門(mén)磚。這是李白的聰明也是其世俗的一面。”[12]如此說(shuō)來(lái),李白早年并非一個(gè)虔誠(chéng)的道教信仰者,直到晚年才成為一位忠實(shí)的道教擁護(hù)者,《唐才子傳》說(shuō)李白“晚節(jié)好黃老”[11]392是其證據(jù)。
由于信仰的不同,二人在失意時(shí)選擇的退路亦不同。白初到長(zhǎng)安時(shí),王維亦結(jié)束了在外為官的生活,不幸的是,其妻子在途中逝世,在政治坎坷與妻子逝世的雙重打擊之下,佛教清凈無(wú)欲的思想逐漸成為王維的主導(dǎo)思想,因此他不再專(zhuān)注于政治中的汲汲鉆營(yíng),也少了年少時(shí)期的進(jìn)取精神,轉(zhuǎn)而開(kāi)始寄情山水田園。這一時(shí)期王維只留下一首《華岳》,其他的多是寫(xiě)景之作,如《清溪》《納涼》《黃花川》等作品。可以看出,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王維遭受打擊之后便選擇避世隱居,不問(wèn)世事。與其不同,李白在長(zhǎng)安干謁無(wú)門(mén),生活困頓之后便開(kāi)始了他的岐、邠之行,之后雖因?yàn)樯罾ьD而不得不離開(kāi)長(zhǎng)安,但是其作品表現(xiàn)出的雄心壯志、積極進(jìn)取的精神是不容忽視的。
與陶淵明的“結(jié)廬在人境”不同,王維追求的是真正的寧?kù)o,表現(xiàn)在作品中為詩(shī)意的佛性,這種特點(diǎn)隨著王維的年紀(jì)漸長(zhǎng)而愈加鮮明。維740年三月“知南選”后,至741年三月回長(zhǎng)安,回長(zhǎng)安之后便開(kāi)始隱居終南山,有詩(shī)《終南別業(yè)》為證。據(jù)《唐詩(shī)紀(jì)事》卷十六記載:“裴迪初與王維、興宗俱隱終南山。”[13]240裴迪與張湮開(kāi)元二十八年在張九齡幕中,又同時(shí)回長(zhǎng)安,也同時(shí)隱居終南山,此為王維隱居終南山的又一例證。此時(shí)的王維,經(jīng)過(guò)宦海沉浮之后功名之心日益減退,沉迷于亦官亦隱的生活。早期王維身上雖然有儒生的“濟(jì)世安邦”的理想,但是隨著佛家思想逐漸占據(jù)主流,王維逐漸成為一個(gè)純粹的佛教徒。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王維逐漸把眼光轉(zhuǎn)向大自然,他在《青雀歌》里就表達(dá)了這種與世虛與委蛇的觀念:“青雀翅羽短,未能遠(yuǎn)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zhēng)上下,唧唧空倉(cāng)復(fù)若何!”[10]291他的這種“無(wú)可無(wú)不可”的人生態(tài)度與李白是非分明的性格恰恰相反。李白受莊子與屈原的影響,憤世嫉俗并敢于揭露社會(huì)的黑暗腐敗,因此李白作品中亦充滿(mǎn)對(duì)奸臣的諷刺。李白的這種是非分明的態(tài)度與王維的“無(wú)可無(wú)不可”的人生哲學(xué)背道而馳,假設(shè)二人在長(zhǎng)安相遇,定會(huì)是“話(huà)不投機(jī)半句多”的。
四、文人相輕的傳統(tǒng)
通過(guò)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gè)確切的結(jié)論,即王維、李白二人在730-731年是不具備互相結(jié)識(shí)的條件的,這種條件是非人為可以創(chuàng)造的:李白初入長(zhǎng)安時(shí),王維已經(jīng)居住在嵩山,且不問(wèn)世事,日常與山野友人互相唱和。此時(shí)李白初來(lái)長(zhǎng)安,懷著滿(mǎn)腔的政治熱情,希望實(shí)現(xiàn)自己“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的政治追求。而此時(shí)的王維閑居長(zhǎng)安,在政治上無(wú)所作為,詩(shī)壇名氣亦不大,甚至不敵李白在蜀地的名氣。綜合而言,李白是不會(huì)去拜訪一個(gè)于自己仕途毫無(wú)幫助的王維的。所以,王維、李白二人在李白初入長(zhǎng)安時(shí)是沒(méi)有結(jié)識(shí)的機(jī)會(huì)的。
但是李白二入長(zhǎng)安時(shí),二人皆在朝為官,卻沒(méi)有相互唱和的文章,除去以上所列舉的原因,還應(yīng)與文人相輕的固有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分析王維的交游團(tuán)體可以發(fā)現(xiàn),與之來(lái)往唱和的雖然有祖詠、張湮等失意文人,但是也包含孟浩然、王昌齡等李白的好友,這些來(lái)往唱和的詩(shī)人之詩(shī)風(fēng)并非與王維一致,所以可以排除二人因詩(shī)風(fēng)的不同而導(dǎo)致的不能相識(shí)。那么,是否可以將原因糾結(jié)為二人入仕方面呢?通過(guò)史料記載,王維在李白二入長(zhǎng)安是為“右補(bǔ)闕”,李白則被玄宗親自封為“翰林待詔”,關(guān)于這兩個(gè)官職,《唐會(huì)要》有明確記載。
關(guān)于翰林待詔,《唐會(huì)要》載:“翰林院者,蓋天下以藝能技術(shù)見(jiàn)召者之所處也。”[14]977翰林院官員的職能是“會(huì)于禁中,內(nèi)參謀猷,延引講習(xí),出侍嶼輦,入陪宴私”[14]977。李白作為“翰林待詔”,書(shū)中記載:“自后給事中張淑。中書(shū)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后有韓雄、孟匡朝、陳兼、蔣鎮(zhèn)、李白等。白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wú)所職。”[14]978從文獻(xiàn)記載分析,李白為翰林待詔時(shí),并無(wú)實(shí)際職務(wù),只是陪同玄宗游樂(lè),并作詩(shī)取悅玄宗。畢寶魁在《王維與李白關(guān)系臆說(shuō)》一文中把李白此時(shí)期待詔翰林定義為“高級(jí)臨時(shí)工”,文中寫(xiě)道:“……臨時(shí)工不愿干就回家,很正常,皇帝多賞賜幾個(gè)錢(qián)只是給個(gè)面子而已。”[15]這段論述雖對(duì)李白的官職有些貶低,但是一定情況下也揭示出李白此時(shí)期在官場(chǎng)上的尷尬地位。
此時(shí)王維任右拾遺,兼監(jiān)察御史,據(jù)《唐會(huì)要》記載,右拾遺職務(wù)為“掌供奉諷諫”[14]965,雖然是從八品的職位,居于末流,但是也能參與商討一些軍國(guó)大事,施展一番抱負(fù)。與李白相比,王維為右拾遺時(shí),雖不如李白風(fēng)光,但是所居官職的重要性也是可以和其一較高下的,甚至可以說(shuō),王維官職的意義要高于李白許多。對(duì)于李白的“翰林”之職位,畢寶魁先生在論文中說(shuō)“實(shí)際上只是盛世天子的擺設(shè)而已”。這句論述可作為現(xiàn)代人對(duì)李白官職的解讀,所以說(shuō),“作為盛世擺設(shè)”的李白,必然不會(huì)得正統(tǒng)文人王維的重視。因此,文人相輕也是二人不能相識(shí)的重要原因。
唐朝詩(shī)人交游、干謁之風(fēng)為盛唐一大特色,忽略唐朝交通不便等外在原因,李、王二位生活在同時(shí)代的作家毫無(wú)交游痕跡的原因在于二人政治地位的差異、交友群體的不同、性格信仰的兩極化,同時(shí)還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相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