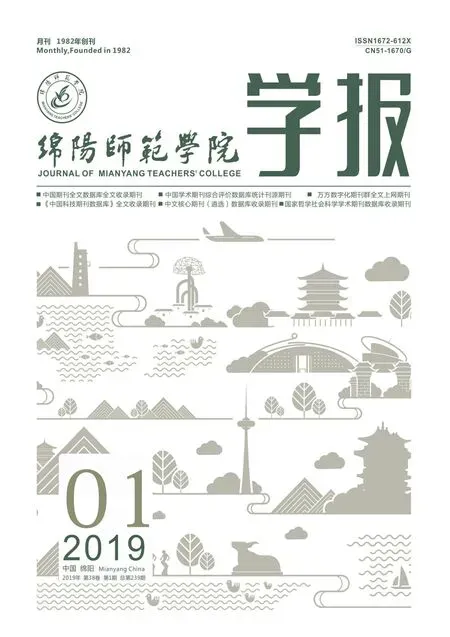光影的形上之美
——以“白墻落影”的光影現象為例
宋思捷
(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成都 610068)
“生活中從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①生活之中處處都可發現美的蹤跡,其關鍵在于用何種視野去發現并對其進行闡釋。美是作為無敝真理的一種現身方式,我們通過對美的欣賞,能夠讓我們從非本己本真向本己本真的存在進行超越。光影作為生活中常見的視覺現象,卻也很容易被人所忽略。似乎“只有藝術家和詩性偶發的普通人,才能在對它進行審美觀察和審美欣賞中窺見它的美的光輝”[1]9。
須知,唯有光影存在之時,安藤忠雄②設計的“光之教堂”里的十字架才被賦予了神圣的意味;東方園林藝術也只有在光影空間里才可呈現出“雖由人作,宛如天成”的獨特意境。當夕陽之下的光影籠罩于建筑之中,校園小道被月色覆蓋,伴隨著自然光、人造光等光源的照射,建筑、行人、花草植被、疏枝密葉等自然實物都因為光的影響而在墻面等光源的接受面上留下投影。在對這些光影現象進行審美時,會發現原本樸實的地面、堅硬的墻體忽然間有了某種藝術氣息,整個空間也因光影而有了超越現實的境界之美。有學者認為:“光影交錯,賦予了建筑以‘靈魂’,敲開了人內心深處與建筑藝術共鳴的大門。”[1]據此,我們也可理解為交錯的光影敲開了人與世間萬物共鳴的大門。當光影躍然成為人類視覺要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形式時,眾多藝術設計者也越來越重視光影強大的空間塑造力。然而,對于這些常見于生活之中的光影現象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建筑、空間裝飾等設計領域來進行分析闡釋,以此來指出光影之美。但為何通過對光影的設計,能給人以美的享受?為何光影就能營造出獨特的空間意境?其美學內涵究竟為何?還有待進一步指出。因而本文針對以上問題,以“白墻落影”,即光源通過對自然實物的照射,在墻等接受面上產生投影這樣一種光影現象為例,分析光影的形上之美。
一、光與影的釋義概述
通常意義上,光的科學內涵是一種肉眼可見的部分電磁波普,且具有“波粒二象性”。光線可以在透明介質中傳輸,如真空、空氣和水。而我們生活中所談的光影之光,主要是指自然光以及各種人造光,即能夠讓人產生直觀視覺效果的可見光。有光的地方必定有影,光與影總是相伴而生,影也是一種光學現象,即光在同種均勻的介質中是沿直線傳播的,而當光在傳播過程中,遇見無法穿透的即不透明物體時,它會在該物體的接受面上留下陰影,這種影將事物的形,以抽象簡練的方式變化成某種另外的圖形。
以上是以科學的方式對光影進行的簡單闡釋,而科學知識總是有“去蔽”與“去魅”的作用,一方面讓我們了解事物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也把一切事物的“詩意性”一掃而空。而現象學認為“現象即是事物本身”,那么在光影作用下的視覺現象,應當是人所看到的事物本身。因為光讓存在物的形象得以存在,而影則賦予觀者對此存在物的感性之思。此外,光影給人的世界帶來的不僅僅是視覺上的沖擊,更有心靈上的精神享受。世界若沒有光,那人的內心會天然地產生一種恐懼。光始終給人以“希望”“方向”的存在,具有指引人前行的力量感,沒有光,世界會一片黑暗,所有的存在物無法以它本來的面貌如其所示地存在于人的視覺當中。而當純粹的一束光直射入眼中時,人也無法看清世界萬物,因而光的存在一定需要伴隨影的浮動。
在西方的文化世界中,每當提及光影,人們可能會直觀地與西方油畫的光影運用技法相聯系。西方繪畫通過光影的作用,把物體分為高光、亮面、灰面、明暗交界線、反光、投影等部分,以此充分表現出物體的立體感,再加之透視等技法運用,光影下的西方繪畫總是給人一種寫實的視覺沖擊。可以說,西方對光的研究主要來源于繪畫及建筑藝術。此外,柏拉圖有對太陽的比喻,他認為:“太陽是肉眼視覺的源泉……僅有視力和可視對象不足以使肉眼看見對象,必須有一個媒介把兩者聯系起來,這個媒介就是太陽發出的光。若沒有光,眼睛只有‘視而不見’的能力,光使視力變成看見可視對象的活動。”[2]49-50這可以看作是西方最早對光進行視覺上的闡釋。而隨后“從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到光的波動學說產生之前,西方對于光的認知一直停留在直觀總結階段。這段時期正是西方的文藝復興前后,西方建筑與繪畫都是顯示出當時人對光與視覺理解的影響,滿足并充分利用透視原理,并且對于光影的藝術表現都有很強的宗教意味。而后的波動光學讓人相信光是一種物質(電磁波)而這也給印象畫派提供了理論依據。此外,西方世界的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派的創作也同樣受光影影響深刻”[3]14。
在古代中國,通過光影的變化來用日晷進行計時,光影的提法在中國傳統繪畫中并不是同西方純粹的科學方式,而是通過留白之處與有墨之處白與黑的對比、虛與實的相互交融來進行表現。關于中國人對光影的最早認識,很早就開始了。《轂梁傳·僖公廿八年》:“水北為陽,山南為陽。”許慎《說文解字》:“陰,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中則指出:“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水北曰陽,水南曰陰。”墨子的《光學八條》是中國古人對光學的理論著作。此外,光與影的概念在古代中國還體現在“陰”與“陽”的哲學范疇上,道家講“世間萬物皆有陰陽”,“萬物負陰而抱陽”。中國人也以這種形而上的哲學視角對光影進行觀察。
二、光影的功能性及視覺藝術表現
(一)生活世界中光影的功能性
人作為自然物,自然環境的變化對人類的生活狀態有很大的影響,而光影是人類生活世界中常見的自然現象、視覺現象,因而對光影的觀察不能與人類世界,特別是人的情感世界割裂開來。光影對人類的生活具有何種功能性,這里主要從三點進行概述。
1.光影對人心理的變化性。光影的自身性質讓萬物在人的視覺上得以顯現,不同角度、顏色的光會賦予萬物以不同形式的影,從而對人的心理產生不同的刺激而引發情感上的異同:“正是光與影的變幻莫測,讓人們體察到諸如莊嚴、神秘、輕快、奇幻等各種各樣不同的建筑心理、空間情感。”[4]因而,光在視覺上給人一種敞亮的作用,且光對人的感官具有強烈的感發作用,如把光看作希望的象征、愉悅的寄托等,當身處黑暗的洞穴,出口的光或成為最大的精神動力。晴朗的天氣中有充足的太陽光照,使得墻等接受面上的投影會很豐富,因而給人以積極舒適的心理暗示。而月光投影下的空間環境總給人以凄美的、幽靜的且更能抒發主體情感的心理暗示。人的內心情感總是受到外物的刺激而在內心受到感發,視覺圖像可直觀的對人的心理情感產生影響。因而不同時間段的光影效果,可給人的心理帶來不同的感受,而光影給人心理上的落差,“能夠利用光與影給人們帶來的心理特征,創造出各種空間。因為在空間中能夠打動人的不是它的功能,而是它所傳達的精神,這種精神情感能夠激發出人的內心世界,或美好、或感動、或悲傷、或肅穆等無盡的聯想和回憶”[5]。
2.光影的時間性。所有的光影的視覺圖像藝術都依賴于光的存在,當是純粹的黑暗世界時,并不會有影的視覺圖像發生,因此光影的藝術是具有時間性的,并且隨著不同的時間變化,光影的視覺圖像也會產生變化。“陰影隨光而生,隨形而變,且與日、月、風、云、雨、霧、嵐、光氣候季節變化有關,隱現沉浮、變化無常;不像建筑實體,行之可游、息之可居、望之可感、觸之可及、清楚實在。”[6]最直觀而言,光影的這種時間性就在于,白天的光照強烈,影的虛象更清楚,且影的顏色因太陽光的顏色強烈而更深也更明顯,人們很直觀地可以感受到晴天的天氣情況,而到了夜晚或者陰天,影的虛象隨著月光或者其他光源的變化而慢慢減弱,虛象也變得模糊,且顏色也更淡。
此外,在一天不同的時段光影的變化也大有不同,且表現出不同的“形”。清晨的時候,由于空氣中水分較多,陽光通過散射而將各種事物都渲染成朝霞的顏色;到了上午光源照射充足,影的虛象柔和;日漸正午時,光照垂直地面照射,且光線更加明亮,這時候影的虛象因為光的強烈而顯得深;而到傍晚時,夕陽將影子拉長,且夕陽的光讓影顯得更有飽和感,層次豐富;到了夜晚,主要以月光和人造光為主要光源,影的虛象呈現出一種區別于白天喧鬧的平靜感。
3.光影的裝飾連接性。不管人們對光影懷著何種態度去打量,去觀察,去欣賞研究,也不管光影對人有何種功能意義,說到底一定是要人這個主體去進行感受,中國的園林藝術是對天人合一古典哲學觀念最直觀的表現。在對園林等建筑藝術進行造景與設計時,光影現象能有意地拉近人與外在物的距離,從而形成一種詩性的空間。另外,當下時代生活的快節奏,使得身處都市空間的人與慢節奏的自然空間處于一定的對立狀態。而當人在月色光影的視覺空間之中時,一定程度上會讓人沉靜于安寧平和的空間環境之中,以光影的律動將人的內心與自然事物相互連接。
此外,當沒有光影存在的時候,建筑與自然物之間是相互分離的;而反之,光這個媒介將自然物與人造物聯系了起來,光影的虛柔和了人造物的實,或是自然物的實,且相互融合。光影的連接性也可說是光影具有某種裝飾性。“陰影對墻面或者空間的裝飾作用主要體現這種由陰影和載體形成的‘圖-底’關系上”[7],即在光的作用下,以影為圖,以影的接受面為底,就園林空間而言,室內室外的建筑與園林景觀因為光影而融為一體。光影下園林植被在建筑的接受面上形成的投影,無疑也是一種純粹自然的裝飾畫。另外,“私家園林建筑輕盈通透,回廊、窗欞以及玻璃在陽光的照射下,與室外的疏枝密影相映襯,將室外的景物及氛圍納入室內。現代居住區架空層引入園林植物景觀的設計,除了增添室內景觀的視覺效果,植物叢的投影連林緣線也豐富了建筑與園林銜接的邊界,弱化了建筑的剛性線條,達到室內外景觀園林化,內外空間自然融合,過渡自然”[8]。
(二)光影的視覺藝術表現——白墻落影
沒有重點就沒有藝術,而落入藝術的光輝總是在于視覺上的突出性,光影所帶來的明暗對比除了讓人產生心理上的情感變化,更重要的還在于對萬物形體及空間的再塑造功效。“光線通過建筑的材料、質感、虛實度、透明度、熒光度、反射度等特質使物體得以成為物體,空間成為空間……光影通過介質賦予空間以生命。在光與影的交界和轉折處, 強烈的光線與深沉的陰影互為比照,在這個轉折之處,形式、體量和三維的空間被明確地限定。”[9]也就是說,光影對人生活世界的以上功能性是需要通過具體的形式來進行表現與產生影響的,光影之美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是需要一個中間介質對光進行阻擋、切斷、接受,以此來形成影的形式,比如,生活中常見的“造影之墻”。因而,在眾多的光影現象中,本文主要以“白墻落影”這種光影的視覺現象為主來進行闡釋。
白墻落影是生活中常見的光影視覺現象,其表現為自然存在物因光影的作用,在以墻或者其他客觀物為接受面上形成的一種新的空間產物,且這種空間與產物具有一種形上的意味,同時也是將自然萬物與人的精神內涵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意象世界。另外,虛實交融、自然靈動下的白墻落影視覺現象,不管是從形式、意境、虛實、色彩,還是從線條的角度來賞析,都與中國傳統水墨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它是一幅以墻為“紙”、以光為“筆”創作的藝術畫卷。
三、白墻落影的美學內涵
“江南園林粉墻的無色之美,也和水墨畫一樣,表現出不施彩色而肇自然之勝,呈現出以粉墻為紙、以石為繪的‘實景消而空景觀’的水墨效果。”[10]白墻落影作為光影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究竟其為何能給人以獨特的視覺享受?其藝術審美內涵究竟為何?
(一)對立統一之美
白墻落影的視覺現象是源于自然存在物在光的作用下,且有墻等客觀物作為接受面而形成的一種影的視覺藝術形式。換言之,白墻落影源于光與影的相互作用。而在文學、影視等藝術作品中常樹立的光明與黑暗的形象,實際代表不同利益雙方的相互碰撞與對立沖突。但在對白墻落影的光影視覺現象進行賞析時,不能將光與影對立看待,因為光與影是在以中間媒介存在物即世間萬物的基礎上相伴而生的存在。大片的光與純粹的黑暗無法讓人欣賞其中的美感,光讓影得以發生,影讓光得到顯現,沒有光就沒有影,沒有影也就無從談光。光與影的一明一暗的狀態,恰是一對和諧共生產物。畢達哥拉斯認為美是和諧,和諧是宇宙的內在本質與規律,而赫拉克利特則進一步說明了和諧源于對立與斗爭,強調并不是從相同的東西中產生了和諧,而是從不同對立的因素中產生了和諧。因此,唯獨在光與影的共同作用下,我們才可能去領會光與影別樣的美感。法國野獸派畫家代表人物亨利·馬蒂斯③說:“總有一天,一切藝術都要從光而來。”白墻落影不僅僅是光的造物,更是影的顯現。總之,只有在對立與統一的哲學思辨中,才可能感受到和諧之美,而在對光影現象進行賞析時,也需帶有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光與影的相伴而生,不僅出現了像白墻落影這樣的光影現象,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一種和諧之美,并給與人類主體精神上的感性之思。
另外,白墻落影中光與影的對立統一關系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與陽理論如出一轍。道家講“世間萬物皆有陰陽”“萬物負陰而抱陽”,《周易·系辭傳》中提到“一陰一陽謂之道”,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認為宇宙萬物變化的原因,是陰陽的對立統一。老子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產生混沌的氣,而氣則分為陰陽二氣,陰與陽的相互交融則產生了萬事萬物。這樣而來,一陰一陽的相互交融、對立統一是能夠產生生命本體的意蘊的,是能夠創造出新的讓人去體會的世界萬象。這也如同老子關于“道”“氣”“象”的論述。“既然萬物的本體和生命是‘道’,是‘氣’,那么‘象’也就不能脫離‘道’和‘氣’,如果脫離‘道’和‘氣’,‘象’也就失去了本體和生命。”[11]27那么光與影所帶來的一虛一實、一陰一陽的視覺對比,無疑是具有和諧互補性的,且這種和諧互補能夠給觀者帶來生命的感悟、情感的反思。光影交錯同時也是陰陽交融,這種融合可產生流動的、富有生命節奏感的世界。宗白華先生認為:“‘陰陽二氣化生萬物,萬物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一切物體可以說是一種‘氣積’。”[12]112因此,可以說,生生不息的陰陽二氣織成了一種有節奏的生命。
光與影相伴而生,陰與陽化成萬物,白墻落影,通過光的照射,樹葉、花草等自然存在物投影在墻面上,一陰一陽,一虛一實,表現出了生命的動感世界,也帶來了一個充滿意蘊的生命世界。光影下的美的世界,只有在光與影的既對立又統一的前提條件下,才能夠產生,也只有在二者共同的作用下,我們才能看到白墻落影的形式,感受視覺上的動感。要分析光影之美,就不能將二者孤立地來分析。
(二)虛實的境界之美
白墻落影有著中國水墨畫的境界之美,花草植被、疏枝密葉等自然實物因為光影的作用成為以墻為接受面上的繪畫題材,虛實濃淡之間,精氣神意全有道理。當對墻上的光影現象進行觀察時,可直觀地知曉影是花草樹葉等自然實物的投影,但以審美心胸觀之,白墻之上的落影,花是實體的花,樹是實體的樹,但花影卻非實花,樹影也非實樹,也就是說白墻落影等光影的視覺現象,首先源于光對自然實物的作用,但在接受面上留下影的藝術表現形式時,就并非完全只是對純粹外在物的反映。正如繪畫藝術一樣,畫中之景雖出自自然萬物但又并非純粹的模仿,而是畫家自身與外物情感交融的產物,畢竟白墻落影的光影現象也是光的藝術杰作。另外,由于自然物是以三維立體的形式存在,因此會有不同的層面,在以一棵樹為整體時,置于前層的樹葉會比后層的樹葉在受光面的飽滿程度上出現不同,因而當光從某一個方向照射而來時,投射在墻等接受面上的影象會出現虛實濃淡、層次分明的變化,因而由于層次分布,光與影的交錯,會帶來實中有虛、虛中有實、濃淡粗淺的層次美感,此外,在風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下,光影隨自然實物而律動,因而這種層次的美讓無生命的畫面變得富有生命意境。那為何虛實的光影能帶來審美的視覺享受呢?
老子說“道”是無與有的統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又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是有與無的統一,是恍惚竊冥,但卻并不是絕對的虛無。有與無、陰與陽產生萬物,萬物之本體就是有無虛實的道,因此萬物之象是要體現道,才能成為審美對象。反觀白墻落影,虛實之間,并非完全只是純粹地反映自然實物本身的具象,而是以光影的虛,來反觀自然實物本身的實,通過在虛實之間來把握事物的本體生命。而中國古典藝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虛實結合,虛實之間才能反映有生命的世界。隨著光的照射,人將目光投射于墻等接受面上的光影形象時,不僅可見識大自然所創造的無比精妙的畫作,也可體味一個具有生命活力的意象世界。前面提到白墻落影的藝術境界與中國水墨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宗白華先生說:“中國人則終不愿描寫從‘一個光泉’所看見的光線及陰影,如目睹的立體真景。而將全幅意境譜入一明暗虛實的節奏中,‘神光離合,乍陰乍陽’。”[12]140另外,他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中認為:“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而為虛景,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意境’。”[12]141既然老子講萬物都生于“有”,而“有”生于“無”,在白墻落影的光影圖像中,以實象而觀虛象,以虛象而襯實象,以虛寫實,以實寫虛。在這種虛實之間,人們通過對光影圖像的視覺把握,以有限到無限,以樹觀樹影,由花賞花影,從而“取之象外”,可領悟到一種“藝術境界”。另外,如果說中國畫的“氣韻生動”是虛實相生而產生的如同“道”的境界,宗白華先生說的“藝術意境”就是“人類最高的心靈賞玩宇宙人生對象時所形成的一種虛實相生的‘生命的節奏’或‘節奏的生命’”[13]。所謂“云破月來花弄影”,就是月光賦予花影以生命的律動,影忽然間就活了起來,這樣的空間意境,就是“虛空中傳出動蕩,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的境界。
瑞士建筑設計師卒姆托④說:“我不理解光,光給予我那種存在著某種超出我之外,某種超出所有理解之外的感覺。”當以審美心胸對白墻落影的光影現象進行審美時,光影圖像成為了審美主體視覺里的全部世界,且主體并非單純的對實象進行觀賞,而是進入了由光影創造出的虛實境界。審美主體在這種氛圍之中,超越自然實體本身,也超越現實境遇,甚至超越主體自身,沉浸于因光影而將實景與虛像連接起來的藝術境界,并由此展開聯想,陷入沉思。而這種藝術境界筆者也認為是一種形而上的,因對現實的超越而形成的情感空間。日本建筑大師安藤忠雄認為,“如果人越來越缺少對黑暗深度的豐富理解及其感覺,那么可能會遺忘空間的回映及光影創造的某種微妙感”,“光永遠是一種把空間戲劇化的重要元素”。可以說,人在光影世界中,是能夠在光和影的相伴之下進行生命的感悟以及體驗的,如教堂里的光影給人莊嚴的反思與懺悔,月色之下的“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的憂傷之思。光影下的空間也是美的境界,因為美是審美者從初始客體上通過直觀或折射出來的審美思維,而生成的一種類理性的無限生命時空。審美主體在欣賞白墻落影光影現象的這個瞬間,創造出了自己的無限生命時空,這種時空也是藝術的境界,首先它是由白墻落影這個光影視覺生成而來,再者更是由于主體內心情感的融入。劉禹錫說“境生于象外”,謝赫說“取之象外”才能達到宇宙之生命本體。虛實相融的樹影花影,觀者通過目擊其物,看花非花,看影非影,觀者的心境與影的虛化相互融合,產生了某種藝術靈感與藝術想象的境界。這種境界就是白墻落影的光影圖像造就的形上之美。
另外,有學者認為:“以寸眸所見寫寸心之大,這是中國繪畫藝術的目的所在。中國繪畫藝術執著于在制造寸眸之小與寸心之大的矛盾中實現自己的理想。”[14]白墻落影作為與繪畫藝術一樣的視覺圖像藝術,同樣是以具體有限的光影圖像,營造出無限的融匯宇宙萬物之道的藝術境界。觀者從靈動虛實的光影之中,看到了萬物活躍的生命氣息,這是一種對當下時代背景的超越,也是對城市之中自然境界的向往,更是通過光影之美而對宇宙本體和生命的發現,人在寂靜的、壯麗的空間之中進行心靈上的享受。總之,通過對光影的欣賞,以小觀大,似乎是觀賞到了現實境遇以外更高層面的境界之美,因而有形的自然實體與虛無的影相互融合,這也就是笪重光所說的“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三)空靈之美
為什么說光影塑造的空間也有一種“空靈”之美?宗白華先生說:“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12]156就“空靈”這種審美范疇而言,“靜”是其最突出的特點,葉朗先生說:“‘空靈’是靜之美,或者說是一種‘靜趣’。”[15]393夜色之下的白墻落影等光影現象成為了與白天喧鬧世界的最佳對比。月光投影下的空間環境總給人以凄美的、幽靜的且更能抒發主體情感的心理暗示,靜謐的環境與靈動的光影圖像交織,成為了黑暗世界的“靜趣”。
我們再通過幾首詩來闡釋,王維的《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詩句描繪了傍晚之時,空山密林中的光影浮動的瞬間景象,其中,“空山不見人”是眼見為實的“空”;而又聽聞人語響動,卻又無法確定是否有人,更顯心理上的“空”。當夕陽的光照進空山密林時,在苔蘚上留下虛幻的影,這種似有似無,且時有時無的虛實、有無交錯,構成了空靈的境界。此外,再看“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這句詩,冰雪的沉寂,但是水中有梅花的投影,魚兒在花的影子周圍徘徊游蕩,這是一個虛實相交,既真實又虛幻、既模糊又清晰的世界,這也是空靈的境界。
以詩句為例,再反觀夜晚的光影圖像,白墻落影就是虛實相生的圖像。當夜晚來臨,世界隨之安寧,在這樣安寧的世界里,花影、樹影卻因月光而生,微風輕拂,虛影隨實體搖動。這種充滿生命節奏的動感,與整個夜晚安寧的環境相互呼應,靜中有動,而這種動卻又不是白天喧囂的躁動,而是生命本原的靈動,且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體會到的動。這種動是對有限時空的超越的動,是因整個寂靜的空間而動,而并非是浮躁的動,因而又可以說是動中有靜。光影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節奏,造就了空靈般的“靜趣”。隨著太陽的時間性變化,這種夜晚安寧之下的光影之景又重新回歸到白天喧鬧的世界之中,且直到下一次月升之時,循環往復。而當人處于安靜的黑暗環境之中時,光與影這兩種對立又沖突的對比加深了人的審美強度,不僅僅給人以安寧的視覺沖擊,也有心理深處的某種感悟。動靜結合的光影,讓人心理強度逐漸變化平復,與白天的焦躁感不同,因為在這樣一種“靜趣”之中,人是超越現實境遇存在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與自然的對話,因而內心是充滿平靜的,是可產生一種靜默的愉悅之美的。
(四)寫意傳神之美
白墻落影的光影現象,雖然是光對自然實物的作用而在墻等接受面上留下的虛影,但虛幻的映像只是一個大致的輪廓剪影,或者說只是一個模糊的外在形式,僅僅是對自然實在物的一個抽象的概括,并不如照片一樣清晰可見每一個細節。但這種抽象的概括形式,正是白墻落影等光影藝術的美感所在。前文提到白墻落影與中國水墨畫的意趣相似,中國繪畫所追求的寫意的審美特征,光影藝術同樣如此。就寫意而言“意”,除了意志、情意等,還有更重要的是表現一種“意境”。白墻落影的光影現象,就是以簡單的、概括的、虛幻的影像,向人們表現出虛實相生、以小觀大、富有生命律動的藝術境界,而非完全與實物相互契合的真實形象。但即便如此,光影的虛像并不妨礙人們對其的觀賞,人們對光影的欣賞也并非是為了獲得對實物的認知,終極目的還是為了體驗光影所營造出的藝術的精神空間。
顧愷之在畫裴楷時在其臉上加上了三根毛,以此將裴叔本來的風貌表現得淋淋盡致,顧愷之傳神論的提出,指出繪畫創作要體現所描繪對象的“神韻”。那某種空間的神韻如何表現?通常白墻落影的光影藝術,與中國園林、建筑相互影響,而“中國的園林向來強調‘天人合一’,強調與自然的對話,建筑的亭、落地鏤空門窗總是毫不掩飾對自然光影的擁有,‘辟牖棲清曠,卷簾候風景’,但這一切,如果沒有光影交錯,再靈光的山石也失去了生機”[16]。不管是在園林空間還是在另外的某種空間,光影都作為一個媒介,將實景與虛景聯系起來,創造一個形而上的藝術空間。“傳神寫照”,是要通過“象”來表現出整體的“神”,而“象”則要通過“形”來表達。就園林空間而言,為何人在進入一個園林空間時,會有一種超越之感,而這種感受與都市生活并不相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人在園林空間中,受植被、山水、亭臺樓閣等這些“形象”及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內涵的相互熏陶,內心的某種自然靈性及對詩性家園回歸的精神愿望被喚醒,而這些愿望是在現實境遇中又并不易存在的。人雖然具有社會性,但本質上卻是自然的人。同理,白墻落影,用光造影,以影造形,原本毫無生命動感的墻體與自然實物,在通過光影的視覺表現后開始有了傳神的生命律動。單純的墻面上升到整個園林空間,或者說在其他的空間里,光影通過虛象,將周圍所有的層次、景物、材料、色彩等相互獨立的事物之“神”完全地連接并表現出來。可以說這就是光影的傳神之美,傳神處就是通過光影所起到的鏈接作用,使整個空間的神韻得以顯現的藝術境界。這種藝術境界,無不通過光影的視覺表達來實現。光影的這種美,在于它通過虛象表現實象,一方面虛象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形象,另一方面更突出實象。在一個園林建筑的藝術空間之中,如果沒有樹影在白墻等建筑物上的虛象,白墻就只是白墻,樹也只是樹,空間的意象相互獨立,使得整個空間并無“精神”可言。而當有光影存在時,獨立的意象因律動的光影而使整個園林空間呈現出一種生命的動感。這種天人合一的生命動感或就是園林空間的獨特“神韻”,而這種神韻的顯現離不開光影的傳神作用。
四、光影之美的本質性探索
對光影之美的分析實質上是對光影美學的闡釋,對光影的審美依然是審美主體以審美意象為對象的一種人生體驗的審美活動。另外,對光影的審美最早可追溯于攝影的技法,但究其目的仍然是借助光影的作用,將拍攝主體放置于理想的空間之中,以此達到其本真生命意蘊的顯現。有學者認為:“光影美學是將五彩斑斕的現實世界抽象成簡樸、素雅的黑、白和灰三種色調,與紛繁的彩色世界相比,它更加簡潔、凝練,也更容易具有純粹的意味。光影美學是一種高度提煉的影像語言,它剝離了事物色彩浮華的表面,而表達出事物的本質和內涵,塑造了影像與現實之間的抽象之美和距離之美。”[1]由此,光影美學的特點可概括為“抽象、簡練、純粹”[1]。
另外,人與大千世界的豐富多彩相比,所視所感的層次有限。所以,如果說“‘人乃萬物之靈’,還不如說是‘人因體察萬物而靈’”[3]9。光影的視覺形式多種多樣,而本文是以“白墻落影”的自然光影現象對光影之美進行分析,那“白墻”之外的光影是美還是丑?亦或者任何投影在墻上的光影都是美的?對此,可以從立普斯的移情說的角度來進行解釋。立普斯認為審美移情是審美主體在進行審美活動時,主體不自覺地將情感賦予本不具有感情色彩的審美主體之上,以至于達到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的心理現象。也就是說,審美活動中,審美主體與審美意象應當是互相存在的。立普斯以陶立克石柱為例子進行闡釋,在他看來,并非是石柱的石頭讓人產生美感,而是因為石柱所呈現出的某種空間意象,而這種空間意象是由陶立克石柱這個建筑形象而產生的。另外,“遠遠不是所有建筑形象,都能引起審美移情的,只有那些契合了人一定的審美生理心理機制的建筑形象,才給予建筑美的移情帶來契機審美的空間是有生命的受到形式的空間”[17]58。在綜合了立普斯的審美移情觀點后,也可對光影的本質性之美做出一定探索,即并非所有光影都是有美感的,這取決于光影的審美意象是否被審美主體所感悟,光影作用之下的空間是否被“生命化”或者“人格化”,只有當審美主體從光影的空間中感悟到某種“自我”,某種“情感”時,光影才能表現出其獨特之美。
《易經·系辭》中講,“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以說,萬物之本即“道”的意蘊是由各自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現的。“白墻落影”的光影現象僅僅是光影之美的一種形式,但不管光影趨于何種形式的變換,光影之美的形上之“道”始終可聚焦于一點,即塑造詩性的空間意境,審美主體居于該意境中,獲得一種形上的情感反思。
五、結語
綜上,白墻落影作為光影的藝術表現之一,無非就是光照射在自然實物之上,經過光的反射、透射、折射等現象而與另外一個客觀接受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產物,墻等接受面上的影只是因為光無法穿透墻而讓投影停留在墻面上的現象。但為何光影能夠帶給人永恒的、寂靜的、空靈的、難以忘懷的視覺與內心體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光影形成的氣氛需要所視、所感、所書的綜合體驗,這種體驗持久而永恒具有謎一般的特質。光影與建筑以及人們對光影中空間的感受的交織是一種形而上學的交織。”[18]在光的作用下,接受面上映射的光影,對自然實物的形象塑造有強大的作用,而一虛一實將人的精神空間與自然空間聯系了起來。光作為媒介,讓自然實物在墻上能夠以另外更抽象的形式發生,當它們以這種方式存在時,在形式上就有了一種藝術之美,從而成為超越自然實物本身而存在起來。“光影的存在是一種氛圍、一種效果、一種情緒,不僅在視象,而且在心里和精神上有著豐富的歷史傳載。”[18]1光與影同時存在,光的直接性與影的發生性相互交融,在這樣一個交融的過程中,形式、空間、精神性通通表現了出來。
因此,在筆者看來,光影是自然產物,并不因人的意志而消失或存在,也并非所有的光影都有美感。而光影之美,可以說是大自然以光為畫筆,以墻等光的接受面為畫紙,以花草樹木等自然存在物為描繪對象而畫出的與中國傳統繪畫精神內涵有相似意趣的藝術作品。這樣的藝術作品是能夠引起審美主體的情感共鳴的。人覺得光影美,其實并非因為光或者影本來的美,葉秀山先生說,“光使天地‘明’,但它自身卻‘不可視’”,而是正因為光讓世界敞亮,并將自然萬物以影的方式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對光影的欣賞,其實質是在光影交匯之下,以自然實物為基底,對在接受面上形成的一個虛實相生、富有生命律動的、形而上的詩性空間的欣賞。人類自身正是通過這種理性的觀察與感性的想象的相互交織,而與外在世界相互和諧。人們在這種境界中來欣賞自然萬物本來的美,以此獲得精神上的超越,情感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