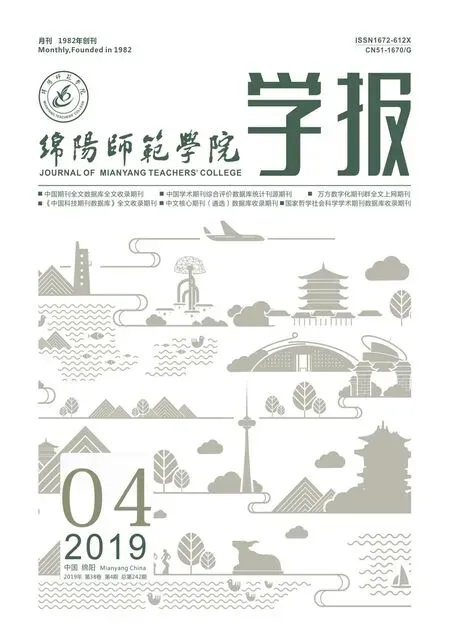啟蒙、革命與虛無——解析小說《狼煙北平》
王者羽, 王宗峰
(1.安徽大學藝術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2.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現代以來,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構想和設計一直是一個宏大工程,也是未竟之大業,其中啟蒙和革命則是無法躲避的命題,也一直是糾纏著中國人的話題和實踐活動,而在中國知識界,更是此起彼伏,波詭云譎,豐富多彩。都梁小說《狼煙北平》直面了這種話題,以文學特有的話語方式進行了審美化闡釋和表達。
在小說《狼煙北平》中,啟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惹眼的話題,作者對此可謂不吝筆墨。小說中的啟蒙主要體現為不同意識形態話語對文三兒這位人力車夫所施加的教化、啟迪、訓導等行為,而文三兒顯然代表著作為啟蒙對象的廣大底層民眾。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是,來自不同意識形態話語的啟蒙努力都不約而同地歸于失效,而啟蒙者卻又認同了文三兒的生存之道,是徹悟還是迷惘?就現代性而論,起碼是一種悲哀。
一、亟待啟蒙的文三兒
小說中作為民眾代表的文三兒被刻意描繪成急需啟蒙的人物,渾身都承載著國民劣根性,作者顯然走了魯迅書寫愚弱國民意在啟蒙的路子。文三兒也秉承了魯迅筆下愚弱國民的很多特征,與他們有明顯的家族相似性,當然最惹眼的還是文三兒遺傳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
文三兒自幼父母雙亡,為乞丐所收養,后以拉車為生,身世和成長經歷模糊不祥,名字也來路不明,大家都叫他文三兒,于是他就成了文三兒,小說此舉與魯迅對阿Q身世來路的刻意淡化極為相似,此意也無非是為了使人物形象文三兒普泛化,從而使之具有穿越時空的象征意義。
文三兒自私冷漠。在一起混飯吃的人力車夫老韓頭貧病交加悲慘死去,文三兒連份子錢都不愿湊。熟人馬大頭在和日軍肉搏中死去,文三兒唯恐其老婆孩子哭鬧而使自己不好意思不掏點份子錢,慌忙逃避了。文三兒為了兩塊銀元出賣了東家陳掌柜而間接導致其家破人亡流落街頭淪為乞丐,而陳掌柜當街暴死在自己面前時,文三兒卻唯恐避之不及而逃之夭夭。
文三兒遇強示弱又遇弱逞強,誠如魯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七》中所說的“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文三兒遇到強者便膽小怕事,動輒嚇個半死,常常伴隨著尿褲子、哆嗦等不良癥狀,如在日軍、彪爺、孫二爺、李爺等強者面前,文三兒或真或假地將自己視為孫子。酒后吹牛無意間損害了彪爺,在彪爺的暴力面前,嚇個半死。文三兒對同為人力車夫的那來順懷恨在心,為報復伺機罵了那來順,當那來順毫不示弱地質問其罵誰時,文三兒由于沒有勝算,便氣勢沖沖地說:“罵我自己呢,怎么啦?”[1]198而文三兒又不失時機地欺辱弱者。日軍戰敗,文三兒見到日本人就趾高氣昂地讓他們對自己鞠躬,后來竟得寸進尺帶根棍子見日本人就打,還心懷不軌地欺辱“日本娘們兒”。對于弱者張寡婦、甚至智障的殘疾姑娘娟子,文三兒也曾伺機欺辱。
文三兒自輕自賤又自欺欺人。文三兒自己心里都承認“自己的確是個賤骨頭”[1]188;他好吹牛、愛慕虛榮,“總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神話里”[1]370,以這種方式化解痛苦。曾吹牛謊稱自己是保密局的,仗勢顯擺,以此建構自信和優越感。與此相關的是文三兒的精神勝利法。愚弱的文三兒正是以這種畸形的方法調整著其不斷失衡的心理。文三兒一貧如洗,難免艷羨富貴,于無奈中又仿佛徹悟,認為有錢人容易招窮人算計,還不如做窮人,于是文三兒釋然了。文三兒晃悠一上午沒開張,正郁悶,但是見到同行伙計們也沒活兒便又幸災樂禍地笑了。
上述種種支撐文三兒生存在世的行為習性,在現代性話語體系中無不被視為阻礙現代進程的前現代惡性因素,是影響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國民劣根性,是制約現代性延展的負值性力量。這些固然重要,但對國族來說,更為關鍵也最令啟蒙者關注的還是文三兒的國族意識問題,異族入侵,文三兒始終認為與他無關,“誰愿意抗日誰去抗”[1]143;“抗日,抗他媽的鬼去吧”[1]57。鑒于文三兒國族意識的缺位,各路啟蒙者分別對文三兒進行了啟蒙。
二、對文三兒的啟蒙
文三兒只知道拉車吃飯,僅是為了活著而活著,從不思考生存的意義,其生存于世的基本法則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至于國家、民族、人民等充滿宏大意義的符碼或事物,他認為都與他無關,“我一臭拉車的管不了國家大事,就知道吃飽不餓頂什么都強”[1]27。對于現代民族國家來說,文三兒這樣當然是愚昧落后的,不是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新民,所以急需啟蒙,目的無非在于“立人”和“新民”。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盡管波詭云譎,但所圍繞的元話題無非是建構和發展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洋務運動、戊戌改良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國民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后革命時代的改革開放等等莫不如此;就是說,這個元話題具有革命發生學和革命動力學的意義。而在這段歷史中,每當民族矛盾觸目驚心使得民族危機成為主導話語之際,民族問題的優先性便被凸現出來,于是,革命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便被統一于民族救亡之中。楊聯芬就曾指出這種現象,認為“革命”和“啟蒙”其實無法割裂開來[2]。進一步解析,我們可以發現,啟蒙與革命的這種“統一”或“共謀”并非有機融合,實質上是革命對啟蒙的整編;但是這種情形并不意味著否定啟蒙,不過是對啟蒙進行了進一步革命化的改造,也就是啟蒙的革命化。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革命其實也是一種啟蒙,是在個性解放基礎上的再啟蒙,是革命者以群體為本位的宏大敘事式啟蒙,引導個體融入到民族、國家、人民等群體之中,是吳瓊花式的;而啟蒙者所張揚的以個體為本位的自由主義私性化啟蒙,指歸主在個性解放,是娜娜式的。
現代意義上的革命顯然不再是文三兒所說的改朝換代,也不是文三兒所理解的出奴為主式的投機取巧,而是建構現代民族國家這項宏大工程;那么,這種革命所要求的參與者與文三兒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現代民族革命。文三兒也曾因沖動而激情澎湃,與民族革命發生了關系。在學生們發起的抗日募捐活動中,愛湊熱鬧的文三兒沖動之中將出賣東家換來的兩塊銀元捐了一塊,遂在學生(楊秋萍)的邀請和鼓勵下發表抗日演說,卻因滿嘴污言穢語而被打斷。文三兒激情難抑,表現欲正熾,便豪情萬丈地為抗日戰士運送軍火,感覺特有面子(露臉),盡管稍后被敵機的轟炸嚇個半死,倉皇逃命。可見,文三兒這次對民族革命的參與其實只是個體性情沖動下的玩票行為。文三兒在威脅之下歪打正著地救了抗日義士徐金戈,便以抗日英雄自居,并要求政府發餉,撈點好處,這種行為與民族革命更是相去太遠了。文三兒因為遭受了日本人的欺辱,并厭惡混合面,便仇恨日本人,又不敢與日本人斗爭,只好耍貧嘴泄私憤,要用其男性生殖器“干那日本娘們兒”而為抗日“做點力所能及的事兒”[1]58。文三兒還參加了北平軍民與日本人的肉搏斗爭,結果誤以為自己受了傷而被嚇得昏死過去。上述種種行為都說明文三兒與現代民族革命的宏大要求相差太遠,急需啟蒙,急需開導和教化,而這種民族危機情勢下的啟蒙話語便是民族革命思想和意識,這就意味著啟蒙的民族化和革命化。
燕京大學學生羅夢云試圖對文三兒進行個性解放和民族革命的啟蒙,試圖使其意識到做人的尊嚴,并激發其以男性的榮譽為國族參戰。盡管作為學生的羅夢云這時自己還沒有走出男權主義文化影響,但對文三兒的啟蒙倒是摻合了個性解放和民族革命的思想意識,無意間實現了從啟蒙到革命的延展,使得啟蒙革命化。
燕京大學教授羅云軒也是從民族主義角度用最簡單的語言對文三兒進行啟蒙的。他告訴文三兒日本人是要讓中國亡國滅種,當亡國奴的日子不好受,在文三兒這兒無異于對牛彈琴,徒增悲憤。盡管曾經主張教育新民救國的羅云軒無意革命,但話語之中所流露的強烈民族主義意識卻和革命者當時的主張并無二致,實現了所謂啟蒙與革命的“共謀”。
地下共產黨員方景林違反組織紀律甘冒生命危險解救愚弱國民文三兒和那來順,這本身就彰顯了啟蒙思想中的平等意識,而他以民族大義為念啟蒙文三兒并試圖動員文三兒去前線參加民族抗戰則同樣是在啟蒙。見文三兒油鹽不進,方景林幾乎崩潰,怒其不爭而大罵一通。在此,方景林把啟蒙和革命已經統一于民族革命之中了,啟蒙的革命化清晰可見。
盡管小說中徐金戈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關于忠君愛國的教育,并被馴化成“以服從長官命令為天職”的軍人,但基于殘酷現實的觸目驚心,徐金戈這個人物形象的發展超越了文化的操控,他對文三兒的訓導與文化對他的設定就不完全吻合。徐金戈的啟蒙使用了現代意義的“國家”“民族”等巨型符碼,與現代民族革命本質相同,這樣就使得徐金戈對文三兒的訓導具有了革命化的啟蒙意味。
從上述可知,盡管啟蒙者來自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但在現代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他們的啟蒙意識都凝結于民族革命這塊磁石上,從而使得啟蒙染上了民族革命的色彩,成為革命化的啟蒙。
三、啟蒙的消解與虛無
在小說《狼煙北平》中,以民族革命為旗幟而統一的各路啟蒙者紛紛受挫,對文三兒所表征的愚弱民眾的啟蒙努力最終都歸于失敗,陷于荒誕,最后歸于虛無。
一群青年學生關于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式的啟蒙宣傳鼓動并不是文三兒捐款、演講以及運送彈藥的動力,這一動力其實就是虛榮心的沖動,而文三兒的演講無非是污言穢語,其主旨也不過就是“操他小日本的十八代祖宗”[1]43。這次活動對文三兒的影響不過就是被嚇得昏死以及關于楊秋萍“軟和”的小手的色情記憶,這就難免褻瀆性的尷尬了。
對于羅夢云的啟蒙開導,文三兒的反應是國族大事與他這個小人物沒關系,他需要的是卑微地活著。當羅夢云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而英勇獻身時,文三兒反倒認為羅小姐不明事理,“好死不如賴活著”。對于羅教授的大義啟迪,文三兒反倒認為非常酸腐。對于救命恩人方景林的革命化啟蒙和參軍動員,文三兒的回應很干脆,就是要保命。對于徐金戈訓導般的啟蒙,文三兒依然堅守他的底線,“好死不如賴活著”。
各種啟蒙努力都在文三兒這個“愚弱”底層民眾的代表身上遇挫,顯示了話語的蒼白,原因固然很多。從被視為啟蒙客體的“愚弱”底層民眾身上尋找原因的做法已經司空見慣了,人們在阿Q、閏土、華老栓、祥林嫂、祥子等人物身上都努力地探尋過,而從現代性話語層面進行探析也不失為一種路數。
藍愛國認為,中國現代性入場的動力學基礎是拯救和治療“民族國家焦慮”,“這就決定了現代性話語具有強烈的民族整體意識,具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觀念”[3]8,這就意味著個人主義的尷尬和委屈,個人的生存只有在政治群體甚至整體的神圣照耀下才有意義和價值。在這種態勢下,個人的私性存在受到擠壓和排斥,基于生命意義的個人生活失去了合法性。以此而論,文三兒的生活自然是負值性的,因為他沒有國家和民族的概念,只求自保,評判事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其個體的現實生命存在。文三兒堅持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至于抗戰,誰愛抗誰抗,不管他文三兒的事,“抗他媽的鬼去吧”[1]57。
文三兒的個人生活中最為關鍵和切要的就是物質生存,現代性話語對此的解決更是令人難以適從,“無論是啟蒙現代性還是革命現代性,核心的本質都是現代性的精神性、思想性、心靈性、理性、意識形態性”[3]5,而對個體生存的物質依據卻處理不當,致使現代性話語具有明顯的“反物質性”。“啟蒙話語對物質的地位基本采取忽略和遺忘的態度,而在革命話語中,物質欲望與私有財產、保守落后、小農意識、反革命緊密相關。”[3]18小說中各路啟蒙者在抗戰時期都沒有從文三兒的切身物質境況出發進行換位思考,而是居高臨下地將遠離文三兒的宏大信仰和理念塞給他。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文三兒最需要解決的就是物質生存問題,所以他接受事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就很難離開物質性,他實在無法像名角楊易臣那樣為了民族氣節而罷演,靠著積蓄堅持八年,也不能像羅教授那樣喝著豆汁兒憂國憂民。所以,他毫無國族觀念,如果日本人能提高其收入,他倒寧愿當亡國奴。中日戰爭在文三兒看來無非就是“混合面問題”,“仗打敗了就得吃混合面”[1]172。聽說共產黨“按人頭分大米白面”,文三兒當然“待見共產黨”[1]291。可以看出,物質缺位正是精英式的啟蒙努力在文三兒這個“愚弱”底層人物身上遇挫的關鍵原因。
小說結尾處讓方景林和徐金戈歷經滄桑之后最終認同甚至羨慕文三兒的生活,這就使得小說在價值取向和追求上陷入了虛無。憂國憂民,上下求索的方景林和徐金戈原以為國家、民族、人民這些巨型符碼能否賦予他們人生足夠的意義和價值,曾浪漫地憧憬攸關國族命運的宏大事業能夠支撐他們奮勇到底,卻在多年以后發現他們自己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擔負不起歷史的重任,命運卻因“被拋”而荒誕,到頭來還是空空如也的小人物,卻因宏大焦慮難以釋懷而疲憊不堪。而一直認定自己是小人物的文三兒反倒是了無牽絆,洞穿世事,反而成了方景林和徐文戈艷羨的對象。據此可見,歷經人世滄桑之后的方景林和徐金戈不論對啟蒙還是革命都已淡漠如水,退守順其自然的平平淡淡,儼然看破紅塵的超脫和沉寂。
以現代的知識體系來看,說文三兒“沒心沒肺”“昏昏噩噩”,無非是說文三兒將個體生命的當下體驗的感性作用推向極端。文三兒憑著其個體生命的當下體驗來衡量日本人統治的不合理無非是讓他吃混合面,還有就是被日本人打了(原因卻是他調戲日本女人);依據基于身體生命的感性追求,文三兒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并將此作為生存底線。這樣一來,就“將對世界進行價值設定的可能性推向了極端”,“人的感性當下的生命體驗才是確立世界的終極價值的真正出發點”,而“感性自我之外的原則、戒律、規范和教條都成為值得責疑的東西”[4]16。其結果便是對個體生命肯定的同時導致價值虛無。
“生者如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猶記當年軍壘跡,不知何處梵鐘聲,莫將興廢話分明。”夕陽西下,方景林和徐金戈兩位滄桑老人引詩詞唱和,傷感處充斥著虛無,就現代性而論,這無疑是一種悲哀;而小說對此卻頗為欣賞,從而導致價值缺席,這就不能不令人遺憾了。藝術不能只限于揭示,還應該更進一步,那就是給予,給人光明和希望。尤其是對存在與虛無的揭示,將意義和價值都冷靜地消解殆盡,確實能夠使人深刻驚醒,可醒來之后呢?難道只能面對空洞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涼? 我們以為,這種冰冷的深刻頗為殘忍。藝術應該是有溫度的、良善的,恰恰因為最終能夠給人不憚前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