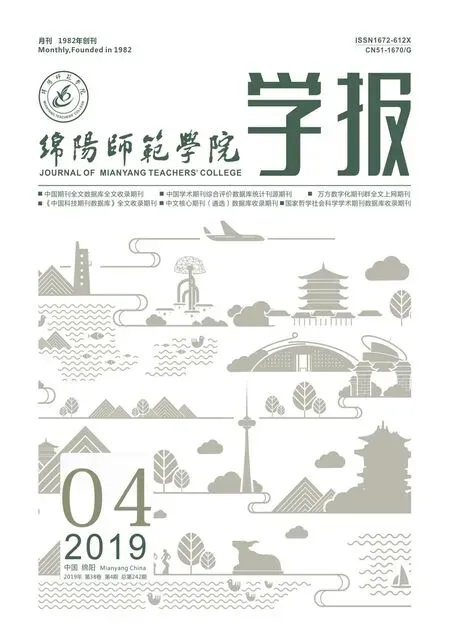尤金·奧尼爾《毛猿》的動物敘事
張惟喻
(陜西理工大學,陜西漢中 723000)
《毛猿》演繹了后工業文明把人異化成非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奧尼爾采用了動物敘事。作者不僅用“毛猿”命名全劇,把主人公和郵輪燒火工們塑造成一群充滿獸性特征的形象,安排他們身處“籠子”里,而且讓揚克圍繞對“毛猿”身份的認同問題展開不懈的探索,最終在動物園猴房與真正的毛猿形成共鳴,并在其大力摟抱下橫死。引入動物敘事,是因為奧尼爾透過社會現象回溯本源,從動物行為和進化理論發現了人類存在的真相:動物在原生環境中生長、繁衍和被置于人工條件下進行豢養,必然呈現不同的行為方式,以此觀照人類文明史,容易取得“陌生化”效果[1];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則再次對人的主體性、人類文明呈現倒退的“荒原”狀態構成反諷,顯露出一種喜劇形式下的悲劇意味。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揚克之死是外部環境強加給他“毛猿”的身份造成的,動物敘事承載著《毛猿》濃重的悲劇意識。
一、叢林法則對理性主義文明的顛覆
《毛猿》用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西方傳統價值觀進行了解構,其思想根源是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奧尼爾曾稱《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對他產生的影響“超過以前他讀過的任何一本書”[2]。他十三歲目睹母親染上毒癮變得精神異常,甚至跳河自殺,而虔心敬奉的上帝在悲劇前無動于衷,導致他深感受到宗教愚弄,進而與之決裂。一家人因復雜的身份、職業背景被當地人歧視,奧尼爾從洪都拉斯探險歸來后自殺未遂,長期混跡酒館“醉心于湮滅”[3],后來一度感染肺結核,出院時父親不信任他的痊愈(其外祖父、祖父皆死于此病,且愛爾蘭人認為重病是上帝對罪人的懲罰)[4],1920至1923年間父母、長兄相繼病逝。以上經歷給奧尼爾留下了終身的心理創傷,使他患上嚴重的抑郁癥,尼采關于“上帝死了”和“酒神精神”的觀念,無形中與當時依賴酗酒擺脫精神痛苦的奧尼爾達成了默契。奧尼爾在尼采非理性主義哲學下重新審視20世紀人類的理性危機、信仰危機,認識到“今天的劇作家應該挖掘當代病的根源,即老上帝的死亡,以及科學和物質主義無力提供一個新的上帝,以滿足人們身上殘留的原始宗教本能——尋找生命的意義,用來安慰死亡恐懼的本能”[5]。
既然傳統的宗教教義、理性精神及現代科學都無力引領20世紀人類文明,人放任自我本能和原欲復蘇,那么《毛猿》通過動物敘事所展示的“叢林法則”填補上述空缺就成為必然。主人公揚克的首次出場是在一艘遠洋郵輪的鍋爐房,“關在籠子里一個野獸瘋狂而憤怒的掙扎與反抗”的混亂中,“所有的文明的白色民族都全了”,曾經憑借發達的文明控制全球話語權的西方人已經墮落成一群“野獸”。“揚克坐在前臺上。他好像比其余的人更健壯、更兇猛、更好斗、更有力、更自信。他們尊重他的強大的體力——因為畏懼,不得不表示的那種尊重。”揚克一出場就儼然是獸群的頭領,其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美德、智慧或才能,而是因為強力;工人們對其地位的承認不是出于尊重,而是因為畏懼。
采用動物敘事,使全劇一開場就設定好底層燒火工人們“非人”的境況:群居動物的類人猿一般以家族單位集群活動,這個家族的首領由一頭在競爭中勝出的,最強壯、最富經驗的雄性個體擔當。揚克與燒火工人間,并非是通過民主方式產生的領袖和支持他的民眾的關系,而是依靠暴力奪取領導地位的頭領與暫時臣服于他權威的群體的關系,原本人性中的利他主義、對集體身份的認同異化成動物用于自保的生存策略,直接加劇了個體孤獨感和同他人關系的惡化。揚克也感到自己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他覺得其他人“對于世事全都有些麻木”,極力嘲諷派迪對風帆快船時代的留戀,要求工人們“別那么大聲亂嚷嚷”以免干擾他“思考”。劇中數次提到羅丹著名的雕塑“沉思者”,但“沉思者”的“邏輯思維”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具備的能力,西方認為“賦予人類最高榮耀的東西就是人是天然的理性存在者”[6]8,能否進行理性思考根本上區別開人與獸。《毛猿》的動物敘事使人獸間的界限模糊起來,作為主體的“人”被消解,思考無法在動物層次上取得進展,揚克自然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只能重陷酒精帶來的失智狀態,因此,他產生了“我是原動力”的錯覺,以為“我開動了什么東西,世界就轉動了”。這種失智狀態下的身份認同是固執而脆弱的,一旦被外部力量戳破就會造成悲劇性的后果。
米爾德里德·道格拉斯的出現正好充當了這一角色。鋼鐵托拉斯總經理的女兒,這是米爾德里德的社會和階層身份,她出身的階層和揚克的階層差異之大,似乎是兩個物種,唯一的相似處在同處“籠”中,說明上流社會本質上也已進入“非人”境地。為了體現二者差異和上流社會的狀態,奧尼爾有意讓米爾德里德與姑媽爭吵時以“豹子”自比:“我想我是那樣……當一只豹子埋怨它的斑點的時候,它一定顯得很怪。(帶一種諷嘲的腔調)咪嗚吧,小豹子。咪嗚吧,抓吧、撕吧、咬吧,塞飽你的肚子、快活吧——只不過要待在森林里,待在你的斑點能成為偽裝的地方。在一個籠子里,它們就使你顯眼了。”安排她懷揣了解“另一半人是怎樣生活”的愿望下到揚克工作的鍋爐房,親眼目睹“一群蹲著的、低頭彎腰帶著鎖鏈的大猩猩”。在自然界,豹子這種中大型貓科動物是類人猿除同類以外的主要天敵,類似的夜行性猛獸曾經給人類祖先帶來恐怖的印象,以致形成了一種隨基因遺傳下來的種族記憶,令人類至今仍對夜幕降臨后的世界心懷畏懼。后工業時代,上流社會靠剝削底層工人的剩余價值生活,米爾德里德與揚克在社會身份上的對立構成了某種類似天敵與獵物的關系,所以她心血來潮的試探,可以視作一次因為“掠食者”本身的孱弱和幼稚導致的不成功的“偷襲”,即便暫時未對雙方造成實質性傷害,也足以在燒火工人中間引發相當的騷動。揚克發現米爾德里德的第一反應,是本能地“急轉過身來,發出一種號叫、殺氣騰騰的咆哮,蹲下身子想向前撲,嘴唇向后咧,緊貼在牙齒上”,展現動物面臨無法避免的危險時自衛的動作,她的到來令驕傲的揚克極其不安,“他的眼睛變得驚慌失措”。米爾德里德昏厥前下意識發出的詛咒,加上維護上流社會的機師馴獸般的哨音(楊克認為這無異于馬戲團用來恐嚇動物的炸鞭子),直接傳達出上流人士對社會底層的認知和態度,正是這點刺激了揚克,引發他強烈的不安全感。
受辱產生的不安全感迫使揚克轉向尋求新的身份認同。他在紐約五馬路只身向上流人士尋釁,就像一頭尋找歸屬的年輕獨身雄猿,最后因為一位太太對“猴皮”表現出極大興趣而徹底爆發,證明對“天敵”(對立階級)的恐懼和仇恨使揚克潛意識里不自覺地把自己歸入毛猿一類,人的身份就此喪失。為了消除不安全感,他寄希望于世界產聯的“同類”,但分會秘書等一眾人對揚克抱以不信任態度,只希望他向燒火工人散發傳單做宣傳,“用合法的直接行動來改造不平等的社會條件”,這種溫和的改良方式與揚克急于用炸藥“把世界上的鋼鐵炸到月球上去”的暴力手段產生直接沖突,階層內部發生分化,揚克被斥為“沒有腦子的人猿”趕出了辦公室。對外來陌生同類的警惕是類人猿的天性,不同族群之間經常因為維護、爭奪領地和資源發生有計劃地殺死同類的沖突,世界產聯的“同類們”不只進一步把揚克推向“毛猿”這個身份,同時也暴露出雙方的局限。在現代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的積極效應消耗將盡,而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條件遠未成熟,人類文明創造出用以改善生存處境的救世理念反而將自身置于更復雜的困境中,對自我成就和尋求正當性的需要主動向叢林法則提供了主導人類命運的機會。
二、逆向演化導致現代人自瀆自殺
奧尼爾的所有悲劇都包含一個古希臘式的主題:主人公無論做何努力終難擺脫命運的糾纏[7]。以俄狄浦斯為代表的古代英雄們“主動采取行動,卻往往迎來被動的結果”[8],20世紀西方文明的探索歷程正好重現了這一悖論,與希臘悲劇略有不同,“人的斗爭,過去是與眾神,但現在卻是他本人,與自己的過去,與其企圖‘有所歸屬’進行搏斗”[9]。這種從泛靈論到宗教崇拜再到扮演神的變化,符合人類思維發展規律,而揚克尋求身份歸屬的過程將這一順序完全顛倒,奧尼爾通過動物敘事體現現代人類向原始思維的逆向演化。
逆向演化,即人的動物化,源自尼采“一切價值重估”中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的不同看法:“我們不再把人看作是源于‘精神’或‘神性’的,而是重新把人放回到動物之中。我們把人視為最強大的動物,因為人是最狡猾的:其精神性就是這種狡猾帶來的產物。另一方面,我們也反對這里可能重新抬頭的狂妄自負,這種狂妄自負認為,人似乎已經是動物發展中最重要的隱性目標。”達爾文的進化理論證明人起源于動物,“在精神能力方面,人類與更高級的哺乳動物之間并沒有實質差異”,尼采則更直接地抹除了人與動物的差異性,于是“人類”身份的同一性斷裂,“人重新動物化”成為19、20世紀人類學的一種傾向[6]5-9。
《毛猿》很好展示了該傾向在后工業時代社會層面的兩個例證。開場,揚克的自我認知充滿“工業崇拜”痕跡,“(機器)它們運動……它們就是速度……它們能突破一切……一點鐘走二十五海里!那不簡單!那是新玩意兒!它頂事”,他把自己看做機器的一部分,這種崇拜反映的是后工業時代人類對機器體系的盲目信仰。芒福德指出,機器體系在18、19世紀西方社會產生的效果“已經幾乎于宗教和信仰,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動力和人類物資的主要來源”。“雖然表面上宣稱設計機器只是維持生存的手段,但對于產業家、發明家及其合作階層來說,機器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目標。”[10]本雅明則直言20世紀是一個“機械復制時代”,“這種機器主義的每一點進展都排除掉某種行為和‘情感的方式’”[11]。機器文明對揚克的異化使他選擇與自然對立,唾棄派迪“星星和月亮,太陽和風”的“昏話”,但又不自覺地回歸原始拜物教。對逐漸擺脫混沌狀態的原始人類來說,“不存在兩種不同的直覺和作用的形式”[12],他們將自然界的物質和自我的意識混同,產生了萬物有靈論的觀點,以為通過向外物施加特定影響,可以起到對自身一樣的作用,從而滿足自己的目的。揚克一開始表現出極大的自信,也是出于這一點,他認為煤灰“是我的新鮮空氣!那就是我的食物”,“我能吃下去!我吃胖了”。通過操縱機器滿足溫飽,進而實現“開動這個世界”的目的,揚克從中獲取效能感。
上流社會的逆向演化則以機器體系信仰的另一變體——“商品崇拜”展現出來,即馬克思所稱“商品拜物教”。米爾德里德在甲板上的表現和紐約五馬路富人們的舉止高度一致,他們污染環境(黑煙),獵殺野生動物(猴皮),與自然保持對立;熱衷能夠滿足虛榮心的慈善事業;態度冷漠、造作仿佛機械產品。上流人士作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商品生產者,通過在市場中順利售出自己的產品實現價值,如果從商品到貨幣再到商品的任意環節出現問題,則必然導致虧損甚至破產,那么目的便沒有達成。因此上流社會操縱商業活動的表象下,他們的命運實際已經被商品掌控,趨于盲目的市場作用使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從猿到人類的進化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古人類學家在關于人類與黑猩猩的最近共同祖先問題上受到諸多不確定性所困擾”[13]。這種不確定性一般體現在某些亞種在原本共同具備的能力上發生適應性進化和退化,自然會影響到大腦機能的發育,對人類思維產生直接或間接作用。以此觀照現代西方社會兩個主要構成群體同時被自己創造的工業體系帶返原始拜物教思維的現象,確屬人類文明“逆向演化”的結果。
人類文明逆向演化可能造成的后果,在《毛猿》中已經進行過探討。戲劇第八場,揚克企圖擺脫毛猿身份的一切努力徹底失敗,他在內外因多重作用下終于承認自己是個“惟一地道”的“野毛猿”。揚克重拾人類身份的追尋完結,代表現代人的逆向演化到達終點,發展出高度文明的人類一旦重返祖先的動物狀態,不可避免要像揚克一樣遭受毀滅,或者說完成“自殺”。悲劇矛盾的頂點在于揚克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幸命運的根源,他選擇與自然握手言和,撬開動物園囚禁大猩猩的籠子,邀請自己的野生同類一起“打一次最后的漂亮仗”,即使明知可能被手槍殺死,當下處境也不會因此改變,“他們會把籠子造得更堅固一些”。揚克表現得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一個真正的“人”:強烈的自尊、清晰的思維、明確的目標、果斷的行動,但這些偏偏發生在他已經明確放棄人類身份,加入毛猿“俱樂部”的前提下,猿和人的身份沖突沒有解決,逆向演化便不可扭轉,結局便是揚克被自己親手釋放出來的同類殺死——毛猿被毛猿否定了。古希臘式的主題再次上演,揚克之死等同于自殺[14],縱觀整個20世紀人類文明史,確實籠罩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核威脅的陰影下,機器體系不僅提高了生產力,也提高了人類“自殺”的效率。奧尼爾反思上述情況,用動物敘事戲謔地表達了對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看法:“也許,最頂事的,畢竟還是毛猿吧。”
三、結語
20世紀正是人類文明大轉型時期。西方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跨國公司和機器生產使大量商品涌入全球市場,社會財富迅速轉移到資本家手中,隨之而來的是環境破壞、貧富分化、金融危機、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運動……人類剛剛看到理性王國成為現實的希望,就被物質和原欲異化成“非人”,靈與肉的矛盾進一步深化,現代主義文學風格便是其影響下的產物。奧尼爾坎坷的經歷和精神創傷,注定他不會像蘇聯作家,用動物遭遇來表現人道主義和生態主義思想,也不像卡夫卡那樣借動物形象尋求動蕩心靈與外界的平衡[15],而是刻意混淆人和動物的界限,把現代人當做動物來寫,以動物諷刺人類社會[16],體現一種充滿荒誕感的原始主義趣味。
面對種類繁多的物種,奧尼爾巧妙地選取“毛猿”這類與人親緣關系極近的動物,是有意識地采用動物敘事再現人類受工業文明異化重拾“叢林法則”,在“逆向演化”中被其逐步摧毀的悲劇。主人公揚克代表的遠不止底層階級,他本身由猿而來,從生物學上揭穿西方盛行的種族主義,經過否定之否定,又變回毛猿,把文明附加的一切東西都剝離掉,這個精心設計的“循環”實際上是一種單向的變形,進化是不可逆的,人類不可能再從生理上退化成猿,但是精神在追尋家園的過程中極可能誤入歧途。奧尼爾一方面向西方人強烈的種族優越感和普世價值觀發起挑戰;另一方面又發揮悲劇的“凈化”作用,對西方社會未來的走勢提出預警。
對于揚克之死,此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悲劇性的一面。奧尼爾采用動物敘事,可以繞開一些較敏感的文化因素,對當前的社會危機給出自己的治療方案。舞臺上的揚克死于“社會病”,現實中的西方人還要繼續作出選擇,“毛猿”原始力量的回歸也許能夠解放被物質文明壓抑的人性,使現代人重生對理性、自由、博愛的信心,進而為之付出努力一樣,就像人類祖先曾經無數次擺脫生存危機延續至今。從這點看,可以說奧尼爾在揚克之死中同時看到了危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