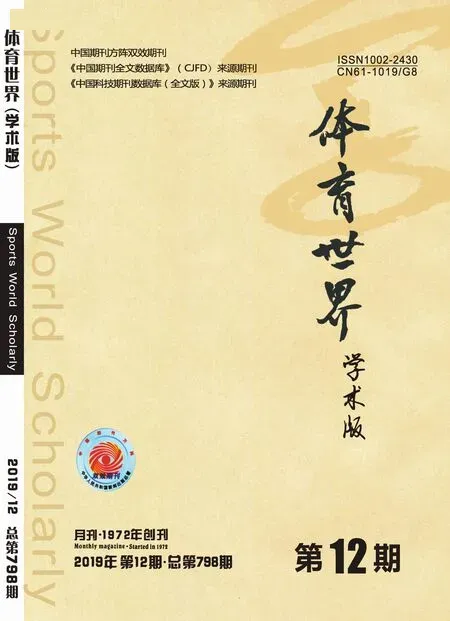湘西呂洞山苗族聚居區苗鼓舞歷史淵源與現代傳承研究
唐夢洋,房道鑫,姚 陽
(吉首大學 體 育科學學院,湖南吉首41600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東界常德,南毗懷化,西鄰川、黔,北連鄂西。面積平方公里。是土家族與苗族的聚居之地。境內轄七縣一市,即吉首市和鳳凰、花垣、龍山、永順、保靖、古丈、滬溪七縣。而就在這貧瘠湘西州土地上孕育著我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筆者通過查閱文獻,訪談及實地觀察對湘西自治州的保靖縣呂洞山苗族聚居區進行苗鼓舞歷史淵源與現代傳承研究。
1.湘西呂洞山苗族聚居苗鼓歷史淵源
鼓—作為華夏精神故鄉中一種獨一無二的祭器,最早源于原始祭拜和古代戰禍。其湘西苗族與苗鼓早已密不可分,有歷史可見苗族的歷史是由苗鼓來書寫,而苗鼓也由苗族傳承與發揚[1]。在湘西州呂洞山苗族聚居區人們不但有擊鼓起舞的風俗,而且有伐鼓歡慶和擂鼓迎戰的習慣,其我國著名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鼓舞就是以苗鼓作為伴奏樂器和道具并隨著鼓點的節奏起舞的。
1.1 鼓舞
湘西苗族舞中最為耀眼的的當屬鼓舞。苗族鼓舞,苗語稱“雀龍”,又叫“跳鼓”是湘西苗族人民最有特點的藝術表演形式,在呂洞山苗族聚居區鼓舞就像印在身體中一樣,從未離開過,每逢祭祀、集會或慶典時,苗族人民都會擂起大鼓,擊鼓起舞。所謂鼓舞,就是把擊鼓與跳舞相融合,擊鼓的同時表現出種種美妙的舞蹈步履[2]。其風格有女子的含蓄、活潑和嫵媚等,也有男子的剛健、奔放、憨厚等,動作形象生動。且具有濃厚的生活性,映現在其步履多來源于呂洞山人們的生活和自然,如耕田農務、農夫插秧、收獲打谷、梳理洗面、織棉、刺繡、織麻紡紗、機靈鬼上樹、貓兒洗臉等,還具有豐富性、地域性和綜合性[3]。苗族鼓舞的種類按表現形式和內容的差異,主要成分有花鼓、團結鼓舞、單人鼓舞、雙人鼓舞等,無論哪種成分都須一人或數人敲邊鼓,其節奏須同表演者的鼓點相統一。
1.2 服飾
苗鼓舞能突出重圍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因為鼓與舞的結合,還有其鼓舞時的服飾鼓舞也為苗鼓舞貢獻了一份力量。
在進行苗鼓舞時姑娘和小伙子們都會穿上具有苗族特色的服飾,其服飾用蠟染花、鳥、蟲、蝶、人物、景物、凡何圖形等;在用扎染根據之前設計好的花形,將織物按必定的要領矗起或扎結,然后放入染缸從而染色,經漂洗后拆去線結。凡是未扎線的部分均受染,扎結的部分則未被染色,因此呈現出不同的花紋。扎染在湘西鳳凰一帶較為流行;最后用刺繡在衣襟、領緣、衣袖、裙邊等都喜愛飾以花邊,圍裙、胸兜、頭巾、披肩等處則飾以圖案,其鞋子穿專門的舞蹈鞋,表面和鞋墊通常也會繡上各類花的圖案[4]。
2.湘西呂洞山苗族聚居區苗鼓舞現代傳承
隨著時代的變遷苗族鼓舞除了生成、傳承、保存、創新,還面臨著政治、時代、制度、市場、文化等復雜語境的挑戰。而湘西呂洞山苗族聚居區的人們面臨最嚴峻的挑戰就是文化遺產與語境的傳承與時代完美的融合。

筆者通過對湘西呂洞山苗族聚居區實地考察發現,每個人每次的鼓舞都是不一樣的,從中可以體現苗鼓舞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每位舞者的個人生命史的顯現,泛起每位舞者的生活、社會、文化語境等。因此苗鼓舞的現代傳承應該關注每代傳承者生命中的實踐、文化事項和知識結構,從每位傳承者的個人風格、經歷、境遇等方面分析現代傳承。
2.1 呂洞山苗族聚居區苗鼓舞的傳承者通過實踐和已有的技術來突破“非遺—苗鼓舞”的結構網。在呂洞山苗族聚居區的人們長時間的實踐過程中,苗鼓舞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價值,呂洞山苗族聚居區的人們一方面通過學習上一輩的苗鼓舞表演,從而接納和傳承著其所沉淀下的社會精華;另一方面,呂洞山苗族聚居區的人們通過一次次的表演,讓苗鼓舞獲取了新的生命,授予著苗鼓舞屬于他們這一代獨有的新的內容和魅力,突破了苗鼓舞從前舊時代穩定的結構張力。說明傳承人的本性、技能、天稟、世傳、興趣、境遇對文化遺產的影響是無時無刻又具有獨特的個人印記。
2.2 舊時代苗鼓舞的知識結構對于現代傳承著的個人能動性具有規范性。在我國的民間藝術有著標準化是美的前提,其表現了民間藝術必須擁有一種結構的穩定性才能稱之為藝術作品。只有在某種情況下發生出某種被要求穩定的規則和行為藝術才會被稱為美,因此作為苗鼓舞的傳承者們,其能動性要求必須于某種特定的社會氣場所吻合[5]。正如楊欣在教新生代打鼓時不停地重復,“(手)應該這樣”、“(腳)應該那樣”……,這一系列的“應該”就是傳承者對于結構的本能體會。
綜上所述,湘西呂洞山苗族聚居區的人們將即個人體驗置身于規定動作中表達,又將從古至今傳承下來的時代與各自身處的時代和地方場域的經驗相融合,這是他們通過日積月累的表演和實踐探究出來的,即將復雜的苗族鼓舞“非遺”傳承變成“簡單的復數”形式。在與當地傳承者的交流過程中,筆者才真正領悟到傳承必“先傳在其破”,也就是說,傳承者們表演者屬于“他們”的舞,并根據自我個性,創造性地發揮這一舞,使傳承者們在生活世界中成為舉世無雙的舞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