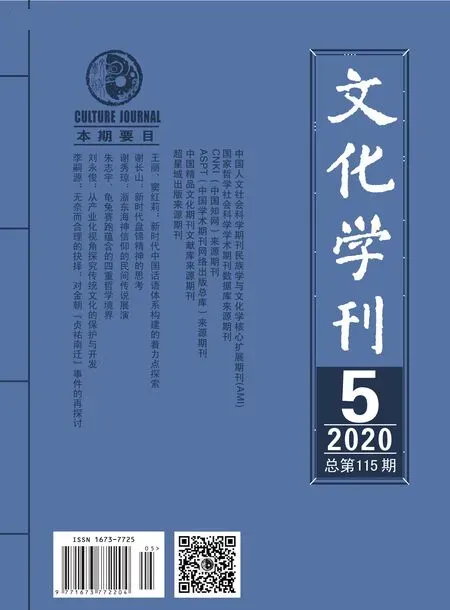論《金剛經》中“無住生心”思想及其當代人文涵蘊
單嘯洋 何 強
《金剛經》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佛教中一部影響極大的大乘佛教經典。《金剛經》為人們在經驗世界中的實踐和認識提供了新的方法論與價值觀,為個人面對現實生活時創造自身的幸福生活提供了一條實現途徑。“金剛”喻為銳利無比,能破一切事物,“般若”譯為智慧,是用以成佛的一種特殊知識,“波羅蜜”譯為到達彼岸。合而觀之,此經即為以金剛般的智慧破除一切事物的外相,而達到脫離苦海的涅槃彼岸。此經之中,何種智慧可以破除一切事物之外相?何種智慧可以領悟事物“性空幻有”的本質?答案在于本經的核心思想“無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不執著于一切事物,而生真心、本心、清凈心教會世人如何在復雜的現代生活中找到一片寧靜的精神家園。
一、“無住”之緣起
在經文之中,須菩提向佛陀詢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1]“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語發音,意譯為“無上正覺”,亦即追求佛果之心,“住”可譯為居住、存在、安住、執著、生命的延續等含義,“降伏其心”也就是借助佛法降伏惡心、塵俗之心。簡單說來,須菩提的提問就是詢問世人如何成佛,《金剛經》的全篇內容也圍繞須菩提與佛陀之間的對話展開。“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2],成佛的方法也蘊含于《金剛經》之中。在佛教般若學中,經驗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的,其本質并非“獨立實有”,故說事物之本質在于“空性”,即是“緣起性空”。事物的存在不是亙古不變的,我們所認識到的僅僅是事物物質性的表象。佛家不否定事物的客觀實在,但這樣的實在并非是先天存在的。在意義世界,事物所謂的本質并不固定,皆是在人類實踐活動過程中而產生,我們所感受、把握到的是事物呈現給我們的“相”。雖然事物的本質是“空性”,但因緣和合的關系一直存在,事物也是實在,故而名為“性空幻有”。由此,佛家修行之中對待世間一切事物的態度在于“無住”,便是世上沒有什么是值得執著之事,因為事物的本質本就是變幻無窮,因因緣而定。“無住”就是報以不執著于世間一切事物的心境而修持的佛家法門。
二、心中“無住”于相
無住亦可稱不住,具體到內部含義,可理解為不執著于一切事物之相。
第一,不執于“四相”。“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3]“菩薩于法應無所住。行于布施……不住于相。”[4]《金剛經》所提到的“四相”為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相”就是我們日常感受、把握到的東西的表象,“四相”是佛家對于凡夫俗子眼中的自我存在形式的界定。具體來說,“我相”有兩層含義:一為自我觀念,將自我意識所產生的形象認為是自我存在的實體;二為在意識中出現的形象與我感同身受,人們就把它當作實我。“人相”即是六道輪回之中的靈魂主體,將靈魂主體當作真實存在的外在相狀。“眾生相”是指眾生身體系五蘊集合而成,卻將其視為宇宙內真實存在的外在相狀。“壽者相”是指個體的生命觀念,一般指把外相的生命存在時限當作真實存在的相狀。無住于“四相”即必須不以我身為真實存在、不以他人為真實存在、不以眾生為真實存在、不以長住于俗世為真實存在,把我身、他人、眾生、長住于俗世都看成虛幻,將作為認識主體的“我”視為空,達到“無我”的狀態。
第二,不執于“身相”。“身相”即是如來于世間的佛像。“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5]對于佛教而言,佛像是一種符號,僅是如來的一個指代。修行者常將自己的本心寄托于寺廟中的佛像,對于雕塑的崇拜反而超越了如來本身的意義。《金剛經》中言:“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6]佛像僅是人心中的妄相,三十二相皆為假象,而非如來的實相。世尊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7]若修行者以佛的“身相”為如來,這正是“以色見佛、以音聲求佛”而不得佛,亦無法到達彼岸。佛相是存在于人腦意識中的圖景,同樣是在實踐過程中產生的虛幻圖景,亦為因緣合和而生,萬相皆空。故而若想獲得“無上正覺”,就得破除萬相,包括佛的身相,所謂“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8]。
第三,不執于“佛法”。“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9]佛法僅是用語言文字所描繪的方法,是渡化世人的工具,用文字所書寫出來的“佛法”也并非等于個人內心真正萌生的頓悟。《金剛經》中有“以筏喻法”的故事,言“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10],把“法”喻為渡河的筏子,一旦頓悟,通達了佛的彼岸世界,就應該登“岸”棄“筏”,不應執著于“佛法”,因為“佛法”只是修行者手中的工具。《金剛經》否定一切法的真實性,不但否定有為法,對實相、般若等無為法同樣否定。習得“佛法”本就為了破除對“相”的執著,萬法本空,法為名相,法即破法。若因得到法的真諦而執著于佛法,那么就會產生出新的執著,造成相互矛盾。
三、心中“無住”于塵
“無住于相”的工夫在于“無住于塵”。要達到心中“無相”的境界,必須處理好“六根”與“六塵”的關系。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感覺認識之六種境界,猶如塵埃能污染人之情識,故稱“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無住“六塵”就是要破除“六塵”在心中的相,使心保持無相的心境,保持心境的空明,自在而不被相縛。佛家以為,人的觀念世界的構成在于人有六根,物質世界的因緣和合卻使得世人六根不凈,內心之中常被六塵綁架,貪嗔癡欲時常左右人心,致使世人無法看清事物的真相。凡夫常為物所困,俗人常為欲所縛,始終不得安其生。若修行者為習得“無上正覺”,便需“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11],即破除六塵在心中樹立的幻相,不執于六根在世間的欲望。這樣才能把握“緣起性空”的奧義,證得真正的“般若觀照”,如六祖惠能之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12]。
“菩薩于法應無所住。行于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于相。”[13]菩薩對于現實世界與彼岸世界存在的一切都沒有執意的追求。在進行心志引導和物質給予的布施時,對于有形態、有情態的物質,有聲的東西、散發的清香、感覺的喜悅、觸發后的各種氣味,凡此種種都應當心地純清,一視同仁地進行。佛陀說到,有教養的心志誠篤的信徒應懷著平等對待一切的心念進行布施,不取決于事物的形象與個人的感受。布施是佛法中一等功德,菩薩行于布施的目的不在于求取功德遂而成佛,也不在于希望得到他人的禮遇與贊賞,更不是受到了外物的誘惑,即布施不是為了滿足色、聲、香、味、觸、法。菩薩布施沒有目的,在于發至本心。所謂“無相布施”即是心中無訴求之事,心境一片空明,行為舉止幾乎自然,這也回證了無住于佛法,菩薩布施并非因為是佛法的教導,而是在于菩薩將布施這一行為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自然而然地就表現了出來。簡單說便是,行善積德已是本然,而非應然,經文最后的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14]即是對金剛破除外相的最好概括。
四、心中“無住”于空
不執于相,更不執于空。空是否定一切事物的獨立實在性,不僅否定了認識主體的獨立實在,也否定了認識對象的獨立實在。“無住生心”是一種工夫論,旨在教導修行之人從對于外相的執著當中抽離出來,將一切事物視為空相。但如果不能辯證地理解空相,這樣的否定形式不免會讓人陷入對一切事物的否定當中,因為一切事物對于主體而言都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而墮入枯木死水般的“頑空”之中。這樣會導致修行者就此消沉,一或杜塞視聽、不問世事;二或玩世不恭,胡作非為,甚至輕視生命。“無法相,亦無非法相。”[15]“法”在佛教中的含義為世間一切事物本性、規律的統稱,也指代事物的表象,“非法”即對空的闡釋。有人看到了法相的虛幻,卻就此落入對“非法相”的執著,即產生對虛無的執著、產生對否定的執著。故《金剛經》又一任務就是要破除對“非法相”的執著,進行否定之否定。
第一,執空亦是執相。“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相。”[16]空相亦是相,若執著于空相,即執著于四相,所以不應執著于尋求一切事物的外在形態,同樣不應執著于沒有外在形態的一切現象的斷然否定。對于“空”的執著同樣會形成新的“有”,執空亦是破除了經驗事物的外相,卻樹立了自身心中的內相。
第二,空為不真空。“眾因緣說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17]不執于空在于認識到空相的邊界,空否定的是經驗事物的獨立實在性,而非否定經驗事物的實存實有。經驗事物的“實在”是因緣和合而生的,其本質在于空,故佛家將事物的實存實有稱為“假有”。“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18]僧肇的中觀之道將“空”解釋為非有非無,不落二邊。事物因因緣和合而在本性上空,因因緣和合而在現實中有。執空之人只看到了事物的“性空幻有”而忽視了事物的“因緣和合”,即忽視了事物的因果規定性,而導致墮入虛無。真正的空性在于空空,空掉虛無,領悟到“緣起性空”中的“因緣和合”。
故而只有做到無住于相、一切法、一切非法,才能生清凈心,修利他行,真正做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五、“無住生心”的當代人文涵蘊
世人常把眼前所見、所體會到的東西視為真實的東西,總是執著于自身已經擁有和掌控范圍之外的事物,對于自身的執著常常使自己陷入痛苦之中。所以無住即是在于倡導世人撥云見日、脫離苦海。“應無所住”就是不執著于世間存在事物。“應無所住”的重點在于無住,在于不執著,而不是將一實物視為不存在。該思想倡導不執著于事物對我們的影響,理應沉著冷靜地面對你的所見所聞,對于周遭的人或事、情或物常懷反思與審視,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不被他人的言行所蠱惑,從而大膽地去探尋真理之光。“無住于塵”就是不執著于我們內心的欲望。滿足人的需要是推動人的發展,而過度的、不合時宜的需要會違背社會或個人生理的發展規律,損害社會或自身。“應無所住”倡導不執著于欲望對我們的束縛,須要擺脫因欲望與現實不對稱而帶來的痛苦,成為更為獨立自主的個體,使個人精神力量更為強大,使心理狀態更為健康。“無住于空”就是要拒絕虛無主義。佛家倡導人們不執著于世間的事物,不執著于內心的欲望,因為這不免會讓人陷入虛無主義之中,認為世間的一切存在皆無意義。因而我們要拒絕虛無主義,將個人與社會的意義寓于內心之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與積極的人生觀,直視生活的慘淡與奮斗的艱辛。
“無住生心”的思想從心性學的角度出發,告訴人們:在物質生活層面,擺脫自身被物質所異化的現象,打破“拜物質教”的枷鎖,從被物欲所支配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在精神生活層面,形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執于生活之瑣碎,無畏于世間之亂象。面對生活所帶來的痛楚,將其視之為幻相,但又拒絕虛無,亦是積極去面對與處理。面對生命所呈現的脆弱,自然不是輕視生命的存在,而是鼓起更大的勇氣“向死而生”。不執著于一切的“應無所住”,自能生“金剛能斷”之心。因為不執著,所以內心更加強大。面對這紛紛擾擾的“婆娑世界”,“無住生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安身立命之法,在這“三千大千”世界之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塊凈土,這對于每個人都有現實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