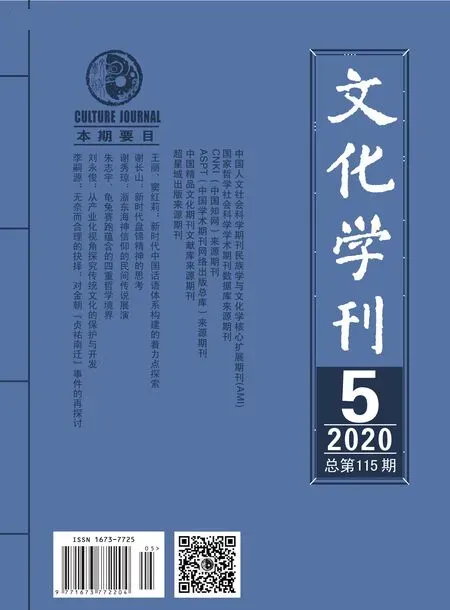一棵垂柳話女人
——淺談留法華裔女作家山颯的女性觀
鄭立敏
《柳的四生》作者山颯,本名閻妮,7歲開(kāi)始寫(xiě)作,9歲發(fā)表作品,陸續(xù)在國(guó)內(nèi)出版了詩(shī)集《閻妮的詩(shī)》《紅蜻蜓》和小說(shuō)散文集《再來(lái)一次春天》等。1990年從北大附中高中畢業(yè)后,山颯在詩(shī)人艾青等人的推薦下前往法國(guó)巴黎留學(xué)。1995年秋,她擔(dān)任法國(guó)畫(huà)家巴爾蒂斯的秘書(shū),在瑞士生活兩年。正是這個(gè)時(shí)期,山颯開(kāi)始了法文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1]。她以山颯(Shan Sa)為筆名,先后出版了法文長(zhǎng)篇小說(shuō)《和平天門》(1997)、《柳的四生》(1999)、《圍棋少女》(2001)、《女皇》(2003)、《爾虞我詐》(2005)、《亞洲王》(2006)與詩(shī)集《凜風(fēng)快劍》(1999)等多部作品,并獲得了龔古爾中學(xué)生獎(jiǎng)、法蘭西學(xué)院獎(jiǎng)、卡茲文學(xué)獎(jiǎng)等多個(gè)法國(guó)文學(xué)獎(jiǎng)項(xiàng)。她的法文小說(shuō)《圍棋少女》不僅獲得了法國(guó)四項(xiàng)文學(xué)大獎(jiǎng)的提名,并最終摘取了龔古爾中學(xué)生獎(jiǎng)的桂冠,還成為2001~2002年度法國(guó)最暢銷小說(shuō)之一。作為一位年輕的異國(guó)女性作者,初涉異鄉(xiāng)文壇便嶄露頭角,年輕的山颯憑借其作品,很快便在法國(guó)獲得了極高的聲譽(yù),甚至在法國(guó)文壇形成了一種文化效應(yīng)——“山颯現(xiàn)象”[2]。
《柳的四生》出版于1999年,此時(shí)的山颯已經(jīng)在法國(guó)生活了將近十個(gè)年頭。從一句法語(yǔ)都不會(huì)說(shuō)到用法文直接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山颯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時(shí)間,這除了她勤奮、肯吃苦的刻苦精神外,更離不開(kāi)女性本身對(duì)語(yǔ)言和藝術(shù)的敏感天性。從山颯的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她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始終落在女性身上。《圍棋少女》是一個(gè)中國(guó)女孩在抗戰(zhàn)年代的愛(ài)情悲劇,《女皇》是中國(guó)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武則天的一生,《柳的四生》更濃縮了四位不同時(shí)代的青年女性的人生故事……作為一位女性作家,山颯筆下的女性人物都有著中國(guó)傳統(tǒng)女性的通性:婉約、寧?kù)o、柔美,但兼具一種不同于作品時(shí)代中的女性群體的韌性、剛毅與堅(jiān)強(qiáng),傳統(tǒng)而又前衛(wèi)。在《柳的四生》這部作品中,山颯講述了四個(gè)關(guān)于女子、關(guān)于愛(ài)情、關(guān)于命運(yùn)、關(guān)于“女性覺(jué)醒”的故事,作者本人在四位主人公形象上的女性觀投射始終有其共性特點(diǎn)。
一、傳統(tǒng)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萌芽
小說(shuō)的第一個(gè)故事發(fā)生在中國(guó)古代明朝,是一段亦真亦幻、亦神亦鬼的傳奇故事。江南的富家公子重陽(yáng)少時(shí)救了兩棵瀕死的垂柳,后來(lái)家道中落,深居鄉(xiāng)村過(guò)著清貧的書(shū)生日子。一日,重陽(yáng)在路上偶遇一位家鄉(xiāng)來(lái)的少年青衣,相聊甚歡,結(jié)為好友。少年衣著不凡,看上去應(yīng)該是出身于大戶人家的富貴公子。青衣的妹妹綠衣自愿下嫁一貧如洗的窮書(shū)生,與之相伴。苦澀的生活從此有了滋味和暖意。而每每問(wèn)起這對(duì)兄妹的身世,二人總是緘口不言。后來(lái)重陽(yáng)遠(yuǎn)赴京城趕考,最終功成名就,得到了皇帝的接見(jiàn)和賞識(shí),功名利祿順理成章,自然也免不了接受一樁皇家婚姻。就這樣,重陽(yáng)慢慢學(xué)會(huì)了仕途的各種規(guī)則,結(jié)交權(quán)貴,逐步成為帝王的親信,一言一行在朝廷舉足輕重。這期間,重陽(yáng)幾次試圖將綠衣從小鄉(xiāng)村接到京城,綠衣卻屢次拒絕,最終激怒了重陽(yáng),但直到此時(shí),綠衣才托夢(mèng)給重陽(yáng):她兄妹二人不過(guò)是重陽(yáng)兒時(shí)救下的垂柳,前來(lái)報(bào)恩,命中注定,情分已盡,當(dāng)就此告別。夢(mèng)醒時(shí)分,只剩沒(méi)落無(wú)助的重陽(yáng)抱著兩棵已經(jīng)枯死的垂柳空悲傷。
在這個(gè)悲涼的故事中,作者通過(guò)綠衣的一言一行樹(shù)立了一位典型的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女性形象。她具備了所有傳統(tǒng)女性該有的特質(zhì)——美麗、溫婉、善解人意,面對(duì)與夫君的分離,報(bào)以全心全意的理解和支持,堅(jiān)強(qiáng)、獨(dú)善其身:“無(wú)論貧窮富貴,只要能長(zhǎng)相廝守,我心便已足矣”[3]而當(dāng)夫君已不再是當(dāng)年的窮書(shū)生,面對(duì)榮華富貴,她又是絕決的,遠(yuǎn)離世俗、絕塵而去。在與之相對(duì)立的男性形象對(duì)比下,這個(gè)女性角色更加鮮明,通過(guò)男主人公重陽(yáng)的善變凸顯出綠衣的堅(jiān)守。無(wú)論放在小說(shuō)中的古代背景還是當(dāng)下的現(xiàn)代社會(huì),這一女性形象都有其突出的個(gè)性特征。與傳統(tǒng)故事中女性命運(yùn)結(jié)局相異的是,山颯放棄了“死亡”,選擇用中國(guó)傳統(tǒng)神話中“幻化”與“輪回”主題,給予筆下女性角色新出路。這與傳統(tǒng)悲劇中女性的悲慘命運(yùn)有所不同,作家潛意識(shí)上在為女性的生存尋找出路。
二、傳統(tǒng)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覺(jué)醒
小說(shuō)的第二篇章仍然停留在中國(guó)古代,故事發(fā)生在明朝初建時(shí)期一個(gè)為躲避戰(zhàn)亂深居于世外桃源的大家族。作者以第一人稱“我”敘述,以一個(gè)女孩的“聲音”開(kāi)始講述。“我”和孿生哥哥的降生是這個(gè)家族的奇跡,因?yàn)楦绺缡羌易鍌髯诮哟ㄒ坏南M拔摇辈贿^(guò)是個(gè)陪襯,祖母說(shuō)“我”“太過(guò)瘦弱,定然無(wú)法養(yǎng)活”甚至命人提前“準(zhǔn)備一副棺木”,由此足見(jiàn)身為女子的“我”是多么不受重視,父親卻將全部的愛(ài)、關(guān)注和希望寄托在哥哥身上。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哥哥并沒(méi)有像家族長(zhǎng)輩期望的那樣成才成器,反倒是“我”這個(gè)在角落里無(wú)聲無(wú)息成長(zhǎng)的妹妹出落成舉止得體、獨(dú)當(dāng)一面的家族希望,但這并沒(méi)有影響到“我”和哥哥的感情。然而,哥哥由于陷害成為家族明爭(zhēng)暗斗的犧牲品,為保命遠(yuǎn)走他鄉(xiāng),父親盛怒之下一命歸西,昔日的大家族頹然間分崩離析。在這個(gè)危難時(shí)刻,“我”一個(gè)小女子承擔(dān)起家族的全部,挽救家族于危難。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與哥哥卻永遠(yuǎn)地分離。“我”不過(guò)是一具空殼,靈魂早已隨哥哥穿越草原,向遠(yuǎn)方的那個(gè)“我”(即哥哥)飛去。
第二個(gè)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仍然具備中國(guó)傳統(tǒng)女性的特征:溫柔、內(nèi)斂、寧?kù)o,但顯然這已經(jīng)不是作者強(qiáng)調(diào)的重點(diǎn)。作者在這一個(gè)故事中著重刻畫(huà)的是這位女性形象的異性特質(zhì),如“我”飽讀詩(shī)賦經(jīng)典、學(xué)習(xí)騎馬、獨(dú)自遠(yuǎn)足、在草原上馳騁飛奔等段落描寫(xiě)。作者將女性對(duì)自由、獨(dú)立的渴望傾注于“我”這個(gè)人物之上,與中國(guó)古代文化中“女子無(wú)才便是德”以及身體嬌弱等特征形成鮮明對(duì)比,“我”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傳統(tǒng)的古代女性形象,兼具男性的博學(xué)、勇敢等性格特征。在傳統(tǒng)的東方文化中,女性往往是等待解救的對(duì)象,面對(duì)困難與痛苦,女性的外在形象應(yīng)該是無(wú)助的、柔弱的,但當(dāng)作者筆下的“我”面對(duì)與“哥哥”的分離和杳無(wú)音信時(shí),內(nèi)心無(wú)比煎熬卻愈加堅(jiān)強(qiáng),運(yùn)籌帷幄以便整個(gè)家族不至于頃刻間方寸大亂、一敗涂地[4]。通過(guò)這一內(nèi)與外的對(duì)比,作者將“我”的異性特征鮮明化,對(duì)于這個(gè)古代女性角色,作者已經(jīng)賦予其先于時(shí)代的某些性格優(yōu)點(diǎn),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duì)女性身份和社會(huì)角色的期待,“我”代表了任何一個(gè)時(shí)代中那些走在傳統(tǒng)大眾女性之前的女性形象。結(jié)合第一個(gè)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青衣,以第二個(gè)故事中的春寧為代表的女性更加獨(dú)立,女性意識(shí)覺(jué)醒開(kāi)始覺(jué)醒,對(duì)傳統(tǒng)社會(huì)男尊女卑的角色定義產(chǎn)生懷疑,開(kāi)始尋求自由與平等。這個(gè)故事的結(jié)局仍然是開(kāi)放式的,作者選擇以“靈魂出竅”的方式實(shí)現(xiàn)女主人公超越時(shí)代的自我價(jià)值審視。
三、現(xiàn)代女性的身份探索
小說(shuō)的后兩個(gè)故事告別古代中國(guó),來(lái)到了現(xiàn)代社會(huì)。一個(gè)發(fā)生在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另一個(gè)則發(fā)生在經(jīng)濟(jì)飛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小說(shuō)仍然圍繞愛(ài)情這一主線愛(ài)情展開(kāi),兩個(gè)年輕男女在一個(gè)特殊的時(shí)代相遇、相知、相戀。因?yàn)闀r(shí)代的原因,也是為了尋找自己,男孩和女孩在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shí)青年大潮中相遇,他們成為朋友,成為兄妹,最終成為戀人,然而,命運(yùn)最終將他們分離。在這樣一個(gè)以悲劇為前提的故事大背景下,女主人公柔弱的外表下透露出的仍然是無(wú)比堅(jiān)強(qiáng)的性格。盡管命運(yùn)弄人,作為女性的她并沒(méi)有自怨自艾,而是始終保持著對(duì)友情的信念、對(duì)愛(ài)情的執(zhí)著、對(duì)未來(lái)的希望,這份堅(jiān)強(qiáng)在時(shí)代的壓力下顯得愈加凝重,也愈加令人動(dòng)容,女性面對(duì)命運(yùn)的抗?fàn)幪刭|(zhì)躍然紙上。最后一個(gè)故事是小說(shuō)中篇幅最短的,但也是形象最鮮明的一個(gè)當(dāng)代女性代表。女主人公事業(yè)成功,經(jīng)濟(jì)獨(dú)立,行事果斷,為了個(gè)人事業(yè)忙碌奔波,感情處于空白期。至此,作者完成了筆下的女性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從單一到復(fù)雜、從男性附屬到性別獨(dú)立的女性形象進(jìn)化過(guò)程。作者用中國(guó)民間故事中“前世今生”的傳說(shuō),將典型的現(xiàn)代女性與小說(shuō)的主線形象“柳”聯(lián)系起來(lái),構(gòu)成了“柳的四生”這一命運(yùn)輪回。回顧小說(shuō)中的女性形象不難看出,垂柳這一文本形象代表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女性的所有性格特征,作者將自己的女性期待投射在這個(gè)傳統(tǒng)的形象之上,并賦予了新的理解與闡釋——堅(jiān)強(qiáng)、隱忍、追求、執(zhí)著。無(wú)論時(shí)代如何變遷,女性身上那種寧?kù)o與溫柔始終是身為女性所具備的“天生麗質(zhì)”,時(shí)代和環(huán)境的歷練并不會(huì)使這種特質(zhì)消失,反而會(huì)錦上添花,轉(zhuǎn)化為女性的新魅力。
四、結(jié)語(yǔ)
縱觀作者其他作品,無(wú)論是《圍棋少女》中那個(gè)沉默寡言、思維縝密、為愛(ài)放棄一切的少女夜歌,還是這部小說(shuō)中垂柳所幻化出的四位女性角色,她們都投射出作者本人的女性特質(zhì)。童年的山颯便顯露出詩(shī)文才情,少年來(lái)到異鄉(xiāng),經(jīng)歷了很多不易,這個(gè)過(guò)程使她認(rèn)識(shí)到堅(jiān)強(qiáng)、隱忍這一品格對(duì)于女性生存之路的重要性,這也成為其筆下女性角色一個(gè)共通的魅力。分析作品中女性角色可以見(jiàn)得,作者在角色塑造的過(guò)程中有意構(gòu)建了從傳統(tǒng)女性到新時(shí)代女性的成長(zhǎng)與轉(zhuǎn)變過(guò)程,并以古老神話故事中的“幻化”“靈魂出竅”等意象為寄托,為女性的生存與自我實(shí)現(xiàn)尋找出路。在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響與作用下,作者筆下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兼具的女性特質(zh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本人獨(dú)特的女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