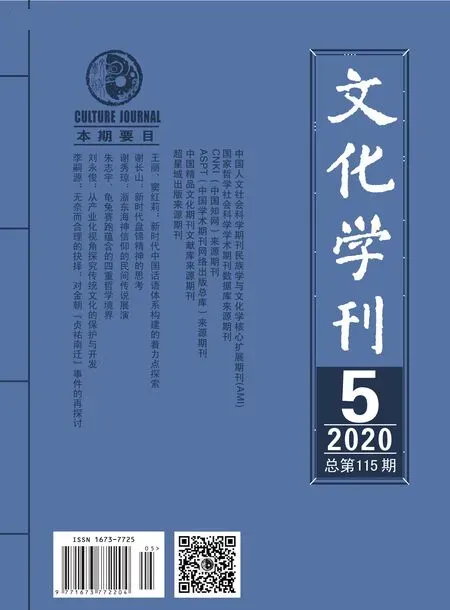新形勢下我國過度醫療侵權的法律規制
李瑞霞
一、過度醫療概述
(一)過度醫療的概念
過度醫療是當今社會的一個熱點問題,隨著過度醫療的發生率不斷攀升,人們的關注度只增不減。目前為止,過度醫療沒有公認的說法及概念,不少學者在自己的領域上有所表達。如張忠魯認為過度醫療就是臨床上,多因素引起的過度運用超出疾病診療根本需求的診療手段的過程[1]。杜治政認為,過度醫療是由于多種原因引起的超過疾病實際需要的診斷和治療的醫療行為和醫療過程[2]。
總之,過度醫療的本質是為追求金錢利益而實施的無關病情的醫療,指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超越了診療規范和醫療準則而實施的醫療行為,造成個人和社會經濟的損害。其構成有四點:第一,醫療機構,或在醫療過程中服務的醫務人員是行為的主體;第二,治療行為與診療過程中的具體規范背道而馳,超過了實際醫療的需要,且是故意為之;第三,給病患造成了人身、財產、精神等多方面損害事實;第四,存在因果關系。而診療最優化是實施醫療行為中的首要目標,應以適度醫療為基本標準,為患者提供安全、便捷、高效,花費少的醫療。
(二)過度醫療的法律屬性
目前對過度醫療行為的界定主要有違約說和侵權說。首先,違約說認為過度醫療符合合同違約的相關規定,主要是醫療機構及其醫療服務人員違反合同的約定,沒有達到合同約定的目的。此學說讓患者的舉證責任明顯減少,而醫院承擔的范圍相對較寬泛,增加了患者對醫院的訴訟,醫院敗訴的風險也加大了。這明顯是在保護患者,醫院很有可能為了逃避責任而進行各種過度檢查和過度治療行為,不利于醫療行業健康發展。而侵權說認為,醫療行為和合同行為是不同性質,不能同類轉換。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真實意思達成一致的協議,而醫療行為屬于公益事業,醫患雙方存在不平等,而且醫院及其醫療服務人員的義務來自法律法規,不能因約定而免除。比起違約責任,要求醫療機構承擔侵權責任更有利于患者維護自身權益,增加勝訴的概率,增加賠償項,如精神損害賠償等[3]。因此,過度醫療行為可從侵權的角度要求醫療機構承擔責任。
二、過度醫療侵權責任的承擔
(一)歸責原則
《侵權責任法》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其中過錯責任又分為直接過錯和過錯推定責任。在《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四條中,醫療損害行為被認定為一般侵權行為,過錯責任原則被普遍運用。第五十九條中列舉了無過錯責任的情況,但具體到過度醫療行為,過錯推定原則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可。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義務主要來源于法律法規等具體規范,第五十八條中規定了違反此規范的情形,此時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而醫療機構一方要證實自己無過錯才能免責。這種方式符合當今醫療活動的特點,醫療活動具有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沒有專業知識的患者和法院更是無從下手,難以面面俱到,因此在過度醫療侵權中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是相對合理的。
(二)舉證責任
訴訟中原被告雙方舉證責任的合理分配有利于平衡兩方的關系,達到相對公平。一般的侵權案件,原告需對四個構成要件全部進行證明,被告只需證明免責事由。而在醫療侵權案件中,醫患雙方地位上的不平等及掌握的信息難以統一,具有其獨特的復雜特征,因而應將證明責任更多分配給占據主導地位的醫療機構。在過錯關系的證明上,適用過錯推定原則,直接將過錯歸于醫療機構,另外由于醫療事故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醫療機構還需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這種舉證方式減輕了患者的舉證壓力,但會使醫療機構處于非常不利的訴訟地位,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會為日后的訴訟減輕舉證責任而毫無醫德地采取各種不必要醫療防御手段,反而使過度醫療行為更加頻發。因此,醫療機構完全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顯然有些矯枉過正,舉證責任逐步緩和更適合我國的醫療現狀。楊立新教授提出有條件的推定因果關系,即先由患者一方證明因果關系的存在,達到一定程度時推定因果關系,由醫療機構一方負責舉證,推翻因果關系推定[4]。
(三)損害賠償
一般的侵權責任承擔的主體應是引起損害的直接責任人員,但過度醫療侵權責任是替代責任,對外承擔的主體是合法的醫療機構。因為患者的整個就醫過程不止包括一個或兩個醫務人員,而是涉及多個部門和多名醫生,更重要的是醫生是醫院的工作人員,有勞動合同,在其職務范圍內從事的行為歸屬于醫療機構。
過度醫療不僅對患者造成直接的財產損失,還有可能帶來間接的人身和精神損害,應該適用全面賠償原則。首先是財產損害賠償。患者支付的醫療費用中涉及過度醫療部分,及可能存在誤工費住宿費、護理費等間接的財產損失。其次是人身損害賠償。造成患者殘疾的,醫療機構應賠償其日后的生活費用及相應的護理費和賠償金;嚴重的過度醫療行為引起患者死亡的,需賠償更多,包括死亡賠償金、精神賠償金及喪葬費用等。最后是精神損害賠償。無論是財產損害還是人身損害,都給患者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傷害,給患者或家人帶來很大的壓力和痛苦,造成嚴重后果的,當事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訴訟,我國《侵權責任法》二十二條(1)《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中也有所提及。
即使醫務人員在具體工作范圍內履行了自己應盡的診療義務,但由于診療行為具有高風險、高未知性,有些現象和情況仍是不可預料的,所以在醫療損害責任中規定了特別的免責事由。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患者和家屬自愿,即自擔風險;另一種是不可抗力,即不能避免且難以克服的一些客觀因素。總之,免責事由是指醫療機構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是由于患者的訴求甚至為了更多人的利益,因此不應該承擔侵權責任。
三、過度醫療侵權的法律規制
(一)完善相應立法,細化有關規定
在民法方面,《侵權責任法》中雖規制了過度檢查會受到法律制裁,但對具體的形式、類型并沒有說明,在實際運用中難以保護患者的利益。另外,過度檢查不能等同于過度醫療,過度醫療的其他表現形式在現實生活中更是無法可依,因此應在法條中明確列出,將過度治療和過度保健納入其中,突出強調,重點打擊[5]。在相關司法解釋中明確“診療規范”的含義,使患者有法可依。對過度的“度”作進一步說明,讓患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自行舉證,適當減輕對鑒定機構的依賴,減少其訴訟的成本。
在行政法方面,加強對醫療機構的行政管理,建立醫生的職業考核制度,完善相應的監督制度,設置行政處罰條例等,如《藥品管理法》第九十條的規定(2)《藥品管理法》第九十條的規定:“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在藥品購銷中暗中給予、收受回扣或其他利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并適當公開行政信息,增加醫生的壓力,這有利于規范其行為。
在刑法方面,醫生為了自身利益在醫療過程中欺瞞患者,讓患者做與病情無關的檢查,患者也因錯誤認識,聽從醫生的安排,做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如果檢查費用過高,達到詐騙的數額時,某種程度上會構成詐騙罪,須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需考慮到過度醫療行為可能觸犯的刑法罪名,以法律的形式規制,使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能更好地貫徹落實罪刑法定的原則。
(二)完善相關制度,緩解醫療機構壓力
完善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落實強化對醫療機構的分配和監督。首先,要改善醫療機構以藥養醫的機制,推廣按病種付費的醫保模式,減少醫療機構的誘導行為。醫保機構可以對醫院進行定期考察,完善醫療機構的信用等級制度。其次,醫療保險機構可以按級別為醫院支付保險,醫院級別和醫保報銷成反比,避免患者盲目地選擇高檔醫院,多花冤枉錢且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在完善原有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可以建立一個專業性強又相對中立的醫療保險監管部門,實行有效監管,平衡雙方的利益訴求。
在具體的審判過程中,法官可指定中立的有權威的第三方鑒定機構鑒定醫療行為是否過度。審查第三方鑒定機構是否遵循鑒定的原則和程序,是否履行了法定的義務,對有爭議的鑒定結果可請求專家輔助人出庭作證,但證明的效力需進一步確定。引入第三方鑒定機構,進一步確保鑒定結果的公正性,成立專家輔助人系統,給后期的審判和患者的訴求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
(三)尋求司法救濟渠道
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法作為正式的法律淵源。我國雖然沒有將司法案例作為法律淵源,但最高法每年會公布一些代表性強的案例,在具體審判中法院會適度地借鑒案例中的處理方式。在過度醫療侵權問題上,也可以發揮一些典型案例的指導作用。醫療活動中,因患者個體體質存在差異以及疾病的特點,司法解釋不能全面概括,也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典型性案例每年都會出臺,更新速度較快,與現實中的醫患糾紛聯系密切,適用靈活且相對具體,更能適應在過度醫療侵權案件中的新變化,具有一定的參考指導意義,同時有利于加快我國的法制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