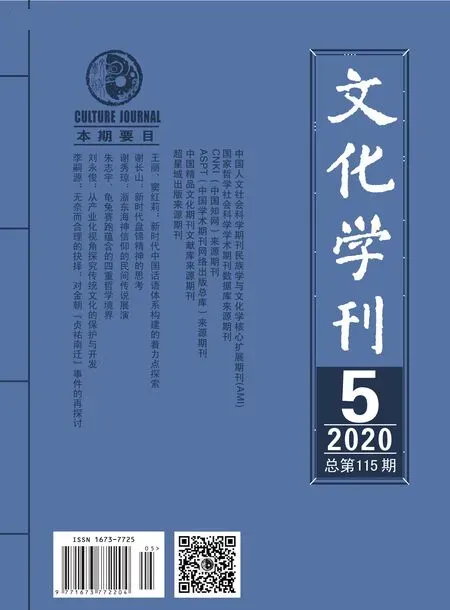男女平等視野下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立法
姜 月
一、男女平等的內涵
生理性別與生俱來,但社會性別是后天努力的結果。男尊女卑是人類早期根據生理特征定義的,因而可以推翻與重建。生理上的男性女性不再是單一獨立的分類,生物基因也不再是唯一判斷標準,社會性別的科學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其廣泛的可適用性。在中國特殊的背景下,男女平等常常被認為是性別平等,在現代倫理道德的解放與性別觀念的沖擊下,二者存在明顯的區別。男女平等可以說是性別平等的一種,是在一個社會上不同性別的人的平等尊重、平等保護、平等享有法律權利承擔義務、平等參與社會共享成果等。我國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平等觀是指男女平等理念。
二、男女平等融入立法的必要性
首先,男尊女卑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存在。男性身材高大,彰顯著力量、權利與權威;女性則弱小,代表著弱勢與服從。“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等諺語口口相傳,如果不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為什么沒有娶雞隨雞、男怕娶錯女的說法呢?時至今日,男女權力地位已經趨于平衡與緩和,但是仍然或多或少彌漫著傳統觀念的氣息。現代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關系仍有很大占比,社會分工依然受性別影響,男性依然是家庭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女性理所當然承擔更多家務,相夫教子,處理日常瑣事等。從全國來看,這種典型的男女觀念家庭分工發達地區較落后地區樂觀,城市較農村樂觀,年輕一代較年老一代樂觀。
其次,現行諸多法律條文體現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例如:《婚姻法》對夫妻雙方住所決定權規定的具體條文中,將“女性可以成為男性的家庭成員”置于“男性可以成為女性的家庭成員”之前,這便是男女尚未實現實質平等的最好證明。這一表述并沒有擺脫封建觀念下對男性權利的傾斜與對女性權利的壓榨,這仍然是扎根于中國傳統封建家庭禮制的土壤中結果的畸形果實,欠缺對女性權益的維護。
最后,體現在夫妻雙方對子女姓氏的決定權。我國現行《婚姻法》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修改了1980年婚姻法中“也可以隨母姓”的表述,可以稱得上是立法的嚴謹與進步,也是男女平等的體現。但是現實社會中,隨母姓的子女少之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在社會習俗影響下,隨父姓已成為理所當然,相當一部分人甚至產生誤解,認為子女只能隨父姓,對法律規定“可以隨母姓”全然不知。這種理所當然的隨父姓于法無據、于理無依,自愿或無奈放棄子女姓氏決定權的現象卻普遍存在。
三、我國法律對男女平等的規定
(一)《憲法》對男女平等的總領性要求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第48條明確規定了男女平等原則,以最高法律形式彰顯了男女平等是整個社會應當遵守并奉行的最高價值準則,男女平等被賦予濃厚的權威與莊嚴色彩。通過《憲法》促進男女平等原則的實施,為婚姻家庭法律體系中男女平等的實現提供了有力支撐。
(二)男女平等是《民法總則》中的具體體現
與《憲法》對男女平等的宏觀要求相比,《民法》著重于私法維度內男女平等的實現。首先,《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在貫徹落實《民法總則》平等原則的基礎上,結合婚姻家庭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充分體現與發展了男女平等觀。《民法》平等原則主要是指民事主體享有的法律地位平等,《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既符合《民法總則》形式外觀上的平等,又強調夫妻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平等,如對于夫妻共同財產的平等處分權、對共同債務的平等清償義務等[1]。男女平等觀著重夫妻間的實質平等,體現了我國法律和諧穩定的價值追求。其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貫徹了民法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婚姻自由原則是私法自治原則的一種,充分體現了法律對于男女雙方尤其是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權與自由意志的選擇。盡管婚姻家庭法律明文規定了男性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婚姻無效情形及其他法定程序等,但這是為了維護最底線的倫理道德與家庭穩定的正確限制,并不是對婚姻自由基本原則的違反,二者并不沖突。在結婚對象的選擇上,男女平等觀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傳統封建觀念使得女性的締結婚姻選擇權被忽視甚至被剝奪,而現代社會的婚姻家庭法律規范給予夫妻雙方充分的意志自由,是男女平等觀的最大發展。最后,《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一夫一妻制是男女平等觀念的體現,也是《民法總則》公序良俗基本原則的貫徹。傳統社會男性地位與生俱來的高于女性,男性三妻四妾是見怪不怪的事情,女性總是以男權為中心喪失了自我。一夫一妻制的實現使得女性掙脫封建束縛,實現自我的獨立與解放,與男性獲得相同的家庭地位甚至是社會地位,符合婚姻家庭倫理道德,符合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有助于家庭穩定與社會穩定[2]。
四、男女平等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的優勢與不足
(一)男女平等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的優勢
首先,我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將男女平等觀繼續貫徹落實,增加了“因婚姻家庭所產生的民事關系”的論述,使得《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與《民法總則》相銜接,在《民法總則》平等原則總體指導下,使得男女平等觀在婚姻家庭領域得以具體實施,是《民法典》分則與總則的科學對接,是科學化、體系化立法的體現。其次,明確了家庭成員的范圍。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此前一直被隱藏于家庭成員這一宏觀概念之下,家庭整體性突出,個體化不足,家庭成員的模糊化與不明確化使得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家庭成員的地位、要求與利益被忽視與遺忘。家庭成員范圍的明確與宣誓是對女性權益的重視,也是男女平等觀的主體要件的明確。最后,消除性別盲點,明確規定了家事代理權。夫妻對于共同財產的處分是平等的,更具現實性與可落實性,在根本上肯定了女性對財產的處分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體現了男女平等觀。
(二)男女平等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的不足
《民法典》編纂到了關鍵階段,《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是男女平等實現的重要領域與制度保障,《民法典》自身的體系化要求、男女平等觀的具體落實都給《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編纂提出了諸多挑戰。例如:在我國潘德克頓體系的立法指導下,《民法總則》的總領性作用凸顯,對于《民法典》各分編的具體法律規范都進行了“提取公因式”的指導,但是其中不免有所遺漏。《民法總則》對民事主體行使撤銷權規定了五年的除斥期間,依據法律適用原理,沒有特別規定時,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的訴訟程序也應適用于除斥期間的規定。在我國邊遠貧困地區,仍然存在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并強行與其結婚的情況,被拐賣婦女被成功解救時遠遠超過了五年的除斥期間,此時被拐賣婦女無法向法院主張撤銷婚姻,只能繼續維持在婚狀態或者提起離婚訴訟。
五、男女平等婚姻家庭制度的實現途徑
(一)宏觀構建:實現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
首先,將男女平等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為了弘揚生活中應用廣泛的、操作性強的、具有效規范作用的道德,需要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加以支撐。婚姻家庭法律體系是一個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復雜體系,男女平等觀是基本的道德準則,是包括《婚姻法》在內的法律明確要求的,因而每個家庭成員應當牢記與遵守。
其次,由民法規范增加社會法規范雙重保護。婚姻家庭問題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復雜的,婚姻家庭法律既涉及家庭內部成員間的權利義務又涉及社會保障、勞動與福利等多種法律關系。對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民事法律與社會發展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在男女平等原則的指導下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家庭成員予以雙重保護。
最后,保障女性身份利益不被財產利益所凌駕。《民法總則》創新性地將《民法》調整范圍中人身關系調整到財產關系之前,彰顯了我國立法理念中的人文主義色彩,為《民法典》各分編的編纂定下基調。婚姻家庭法律關系中同樣兼具人身利益與財產利益,為了避免處于次要地位的財產關系喧賓奪主,防止市場處理財產關系的一般法則被濫用于婚姻家庭,應加強對女性身份利益的維護,保護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基于人身關系而獲得的各種權益。
(二)微觀舉措:完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
男女平等觀念在婚姻家庭領域的發展有助于和諧家庭關系的建立,有助于建庭成員之間相互尊重、互敬互愛,促進和諧社會的穩定。目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關于男女平等觀的貫徹過于簡略,因此,要明確男女雙方實質上的全面平等原則,具體體現在婚姻家庭領域,要求夫妻雙方平等享有家庭利益,無性別上的差別對待。也應明確規定夫妻權利義務內容,以實現對男女平等的全面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