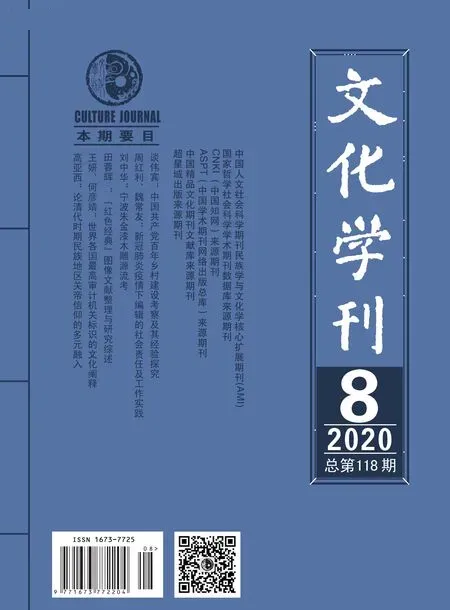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紅色經典”圖像文獻整理與研究綜述
田蓉輝
一、“紅色經典”圖像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意義
“紅色經典”指20世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批以中國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題材,在主題思想上與主流意識十分契合的一批革命歷史小說,如《青春之歌》《紅巖》《創業史》《林海雪原》等。“紅色經典”中存在大量的封面與插圖圖像資料,它們以圖文共生的藝術魅力為小說增色不少,與文字文本一起構成整個“紅色經典”文學,因此,對其展開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法國文論家熱奈特將封面畫、插圖等歸屬于“副文本”,認為其與正文本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已經連為整體,不僅具有歷史價值和文本價值,也具有史料學價值。一直以來,學界對“紅色經典”的研究都局限于小說正文本內容,忽略了封面與插圖等副文本因素,以至于“紅色經典”圖像文獻整理不夠完整,還需要做大量的圖像史料梳理和版本校勘研究。而這些圖像資料對探究“紅色經典”作品版本源流與補充文學史、美術史、設計史、出版史中的視覺史料有重要意義。
第二,目前對“紅色經典”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文字文本,鮮有人從圖像的視角探尋“紅色經典”的價值與意義。“紅色經典”作品封面與插圖參與了文本意義的生成,以圖像媒介的形式承載著特定的文學內容。從圖像與文本的互動關系著眼,可以突破過去以文字為核心的“紅色經典”研究的單一路線,拓寬人們認識文本內容的視域,強化文學研究的文化語境,帶來“紅色經典”文學闡釋意義的更新,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第三,隨著“讀圖時代”的到來,文學與圖像的關系更加緊密。對于文學自身來說,圖像文化的出現不僅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機遇,人們可以利用圖像文化更好地促進文學的發展。傳統文學如何突破語言單一性的障礙、文學作品如何實現文學與圖像的密切結合,“紅色經典”是成功的典范。因此,在“讀圖時代”研究“紅色經典”插圖與文本的關系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的“生產”屬于在上級領導高度重視下分工明確、組織得當的體制化創作,作家、編輯、畫家的聯動、畫家對作品的深入了解、出版社的深度參與是創作成功的主要因素,這一“生產”過程對今天的圖書裝幀設計有一定現實啟示意義。
二、“紅色經典”圖像文獻整理與研究現狀
對“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出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的報紙與期刊呼吁文學作品重視插圖,并對插圖做過一些淺顯的討論,如1953年《人民日報》上《關于改進文學書籍插圖和封面設計工作的座談會記錄》等。第二階段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書籍再度呼吁插圖回歸,如1998年《光明日報》的《文學書籍呼喚插圖》、張守義的《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插圖卷》等。第三階段出現在最近十年,語圖關系成為熱點話題,“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圖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學、美術學、設計學等領域。
一是文學角度的研究文獻。有學者從文學作品版本流變角度考證“紅色經典”插圖,如羅先海與金宏宇[1]對封面畫、插圖等副文本的生成和變遷進行了考察。龔奎林[2]、劉曉鑫、趙忠誠等分析了小說文本與插圖相互依存的關系和插圖的版本變化。龍其林探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圖文關系和類型。夏惠慧[3]、劉巍[4]、陳林探討了封面、插圖與文本主旨的關系,認為“紅色經典”封面、插圖嚴絲合縫地貼近小說文本。
二是美術學、設計學角度的研究文獻。王冬炎[5]、方方[6]對1949后的插圖特色做過分析。李蘇丹與龔小凡[7]、徐靜琪[8]、師靜[9]從書籍裝幀的角度對“紅色經典”插圖、字體進行分析,并討論了書籍視覺圖像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聯。祝重壽的《中國插圖藝術史話》、四川省美術家協會與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合作的《紅巖版畫——〈紅巖〉原著版畫插圖五十年》對各個時期的插圖情況進行了梳理。於賢德、劉婷分別以《紅巖》和《林海雪原》封面圖像為個案,力圖從封面、插圖的變遷再現“紅色經典”的發展史。
三是圖像學理論相關的研究文獻。金惠敏、李燁鑫、鄒廣勝、高建平、龍迪勇、肖偉勝等一批學者較早關注視覺文化和圖像研究,趙憲章[10]在《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探討了新時期背景下文學與圖像的關系。
三、“紅色經典”圖像文獻整理與研究評析
從以上分析來看,“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已經引起了比較廣泛的關注,但研究成果還不夠多,研究也不夠深入。從文學視角對“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進行分析的研究成果視角比較單一,更多關注插圖的版本變化。插圖與封面在藝術形象塑造、版式設計、色彩選用等方面是如何同小說文本一起營造革命宏大敘事氛圍?如何在創作手法、空間場景的選擇、人物主副模式的安排上考慮工農兵讀者的欣賞趣味,并與之高度契合?目前對這類重要問題的探討都不夠深入。
從美術學、設計學視角進行探究的成果還停留在對圖像的收集與整理階段,得出的結論只是就插圖本身進行討論;有些插圖的版本考證尚不清晰;龔小凡在前人的基礎上將紅色書籍圖像放在整個政治意識形態大背景下來觀察,是目前做得比較深入的研究成果之一。但此類研究沒有將插圖視為“紅色經典”文本的一個重要部分進行探討,忽略了“紅色經典”文本與插圖是一個互文共義的整體,沒有將文學視角與美術學視角綜合起來進行觀察,解讀深度不夠。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應該總結“紅色經典”圖像怎樣突破語言和文字限制的經驗,為文學創作以及圖書裝幀提供更多參考,并滿足了讀圖時代社會受眾的審美需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從跨學科視角結合文學、美術學、設計學等視野,采用圖文互文的方法,分析“紅色經典”作品中的平面圖像,闡釋“紅色經典”作品的圖文關系,并深度詮釋該時期平面圖像設計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新的文學秩序的確立以及經典形象塑造等問題。
(一)“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圖文互文關系研究
“紅色經典”文本與插圖是一個互文共義的整體,它們之間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形成圖文互生的藝術效果。插圖將文學形象視覺化,并延伸主題、深化內容、拓展文本的表意空間,幫助讀者領略“文字之所不及”。“紅色經典”藝術家給小說做封面和插圖的前提是對作品進行深入了解,包括對小說背景的充分認識、對小說情節的準確把握、對人物性格的充分理解。有些長篇小說插圖就像一本連續性的連環畫,緊扣小說情節,一氣呵成。比如侯一民版《青春之歌》插圖大部分和林道靜有關:無助坐在海邊想要輕生的林道靜——怯生生地注視著革命人群的林道靜——如饑似渴閱讀革命書籍的林道靜——在監獄中接受革命引導的林道靜——走在革命隊伍前列、成為成熟領導者的林道靜。插畫家以線性敘事的手法表現了小說中的重要情節,再現了林道靜的成長史,成功吻合了小說的主題。
圖像對小說情節瞬間如何“定格”?作為空間藝術,插圖有其天然軟肋,即它不能自如地表現小說的連續性故事,只能選擇“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頃刻”表現文本內容,“那一頃刻”是“定格特寫”,選擇的好壞影響小說文本的思想闡釋。“紅色經典”插圖表現的多是最富有意義的瞬間,讓讀者能很快了解故事的情節、事件、人物等。場景和背景設計在“紅色經典”圖像中也不是隨意而為的,刑場、監獄這些場景會反復出現,看似偶然,實則體現了插畫家在場景刻畫上的良苦用心。刑場、監獄是最能夠考驗革命意志的地點,也是最能夠突出革命主題的選擇。
(二)“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的風格研究
“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形成了與工農兵讀者欣賞趣味高度契合的風格。第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直白的內容,臉譜化、程式化的人物塑造,極高的人物辨識度,迎合工農兵大眾簡單的、類型化審美習慣與欣賞習慣。在過去,“紅色經典”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是受到指責的,但也正是這一點使得“紅色經典”平面圖像在風格上與工農兵讀者欣賞趣味高度契合,他們最能接受的正是這種臉譜化的人物形象。第二,鄉村中國的空間場景描繪、左右圖文結合的閱讀模式、木板插圖為主的宣傳形式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具有鮮明的時代氛圍和泥土氣息。第三,人物“多寡”偏倚的主副模式、扣人心弦的情節刻畫符合中國大眾喜歡故事性強、情節引人入勝的欣賞習慣。
四、結語
對“紅色經典”圖像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順應了讀圖時代學術研究新趨勢。從文學、美術學、設計學等跨學科視角厘清“紅色經典”書籍封面與插圖全貌,把握其圖文關系,梳理其革命敘事內容以及工農兵大眾的審美風格,能全面了解“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問題,對“紅色經典”封面與插圖做出符合歷史事實的評價,還原其歷史創作現場,并對今天書籍插圖創作帶來啟示,最終拓展“紅色經典”作品研究與美術史研究的新領域,探尋“紅色經典”研究的新方法、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