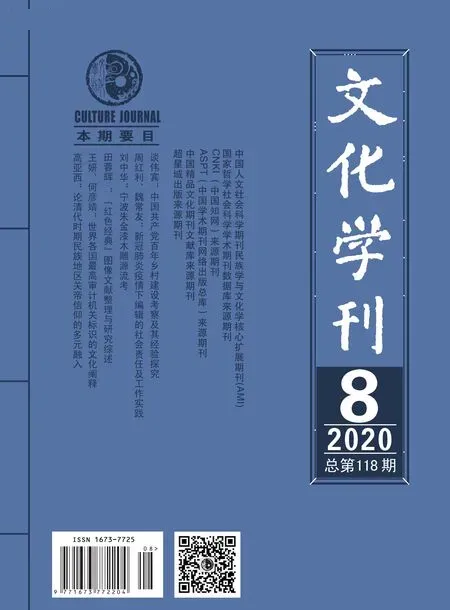禮制對中國法律文化發展的影響
王 樂
法律扎根于社會,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法律文化。禮,源于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宗教儀式,經過不斷發展,后來逐步形成具有法律屬性的道德之治[1]。禮制是以“禮”為核心內容而推行的一種規范和調整社會的制度和機制的總稱,目的是通過規范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禮法,為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秩序。它不僅是中國法律文化的起源,還影響著中國法律文化發展的歷程。
一、禮制的發展
西周初期,周公旦創立“周禮”并一直沿用到西周滅亡,可以說,西周是中國禮制的起源時期。周公制禮,是總結當時社會已經形成和存在的“奉神人之事”,是對人們已經形成的言行模式和在各種社會活動中形成的有次序的禮儀抽象概括和歸納總結后,進行的文字化、規范化和制度化。自此,“禮”成為一種制度,禮制也由此而生。經過歷朝歷代的不斷發展,“禮”成為中國法律文化的核心內容,滲透于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法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了東周,“禮制”崩壞,所以才出現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后來,雖然秦以“法制”統一中國,但“禮制”一直沒有完善。
唐朝初年確定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法律思想。人們崇德尚禮,統治階級開始實行德政、推行禮制,強調德本刑用,將禮、法融為一體,道德禮制為治國之本,刑罰鎮壓是輔助手段,形成以禮制為主、法制為輔相互支撐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順應了歷史潮流,禮制得以迅速發展,鞏固了統治基礎。禮制在唐代是空前的,在“貞觀之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根本性作用。南宋時期,朱熹提出“理學”,重新建立起了禮制的理論體系,之后的元、明、清都遵循此體系,尤其是明清兩朝。
二、禮制的特點
禮制是文明之治、道德之治,是一種至高的理想追求,迎合了人類進步的需要和社會群體的共性期望,從產生開始便為人們所接受,逐漸深入人心。盡管統治者將禮制作為一種統治工具,以加強對政權統治的鞏固,在禮制的實施過程中帶有強烈的封建統治色彩和統治者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氣息,但人們能夠普遍遵從禮制的束縛和要求,這樣便更大程度地發揮出禮制作為社會規范的實施效果。在禮制的發展過程中,主要具有德主刑輔、無訟息爭、等級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特點。“禮制”在價值層面上以德為核心,解決德和法之間的關系。禮以德為價值核心,經過歷代的發展最終形成“德主刑輔”的模式。禮制是道德之治的具體表現,其強調“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認為訴訟是道德敗壞的表現,提倡通過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爭議。禮制以等級秩序為處理社會關系的準則,不同的等級之間應該遵守相應的禮制秩序,不可逾越等級秩序。禮制對君王的統治地位極其維護,強調君權神授,是統治階級維持政治秩序、進行社會治理的工具,具有強烈的封建主義色彩。
三、禮制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
禮制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逐步形成自身的特點,其特點在禮制的實施過程中對中國法律文化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一)德主刑輔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
德主刑輔是在禮制的發展過程中禮法融合所產生的一種治理模式[2]。在這種模式中,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法家嚴刑酷法為輔助。由于這種模式在統治階級維護自身統治和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德主刑輔成為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法律文化進行不斷探索和完善的主要方向[3]。
秦朝注重法治,制定了完備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太過注重法治、刑罰太過殘酷,常常導致輕罪重刑的矯正過度結果。秦朝專任法治的失敗促使漢代統治者吸取教訓進行治理的探索。漢代儒家在秦朝構建的法律框架上融入道德與法律因素,進行新的法律制度創建,開啟了德主刑輔的“法治”時代。漢朝承襲了秦朝的法律制度,通過以經注律、引禮入律的方式改變了秦律的殘忍冷酷,彰顯法律的道德關懷。董仲舒通過對天地陰陽理論的推定明確了德主刑輔的主從關系,確立了儒家所推崇的禮治價值高于法律的優先性。自魏晉南北朝開始,我國歷代的統治者便不斷加強和完善德主刑輔的治理模式。唐朝初年,李世民以隋朝滅亡為鑒,在魏征和封德彝辯論的思想基礎上,從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以禮刑并用作為立法思想,制定了《貞觀律》,強調寬仁慎刑。唐朝也一直延續“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德禮”而設的遺風。宋代朱熹對禮法融合理論進行重構。他繼承“德本刑輔”的思想,但在司法上主張“明刑弼教,以嚴為本”,希望統治者在德主刑輔的前提下以重刑懲治“大奸”之罪,使人畏法,達到教化所不及的效果。明清時期,“明刑弼教”思想進一步發展,禮教被奉為最高價值,刑罰更為嚴苛,以刑輔德更加突出。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禮與法相得益彰,共同成為封建統治者治民理政的工具。從漢朝開始,禮法融合、德主刑輔的治理觀念成為各朝各代統治階級的共識,中國法律文化逐漸形成以禮教為主、刑罰為輔的發展潮流[4]。
(二)無訟息爭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
作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取向之一,無訟息爭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源。封閉的地理環境使血緣氏族被延續下來,形成家國一體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為無訟息爭奠定了社會基礎。禮制是道德之治的具體表現,強調“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認為訴訟是道德敗壞的表現。在注重禮制的朝代,無訟息爭成為法律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統治者通過立法來明文限制人們的訴訟活動,家族和等級制度也會影響人們的訴訟活動,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無訟息爭能夠得到較好發展和延續。無訟息爭能夠幫助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加強社會道德教化,也能節約司法資源[5]。
(三)等級主義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完全是建立在等級制度之上,這一制度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父權為核心。階級之間的差異非常清楚,社會習俗和法律地位上都具有明顯的等級差異。等級主義對法律文化產生的影響以立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統治階級通過立法對不同階層的生活方式進行規定,細至飲食、衣飾、房舍、車馬等均可以通過法律做出強制規定。法律針對不同階級做出了區別性的規定,也體現出階級間差序格局的現象,精準地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做出度量。這種帶有等級主義色彩的禮制通過影響法律文化的內涵而不斷影響著法律制度的創建,影響廣泛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便是禮制等級色彩的體現,它為中國古代等級制度以及法律制度奠下基石。
法律是統治階級統治臣民的工具,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階級屬性。某段時期出現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說法,強調所有人都在法律的規范之下,沒有人能夠違背法律的規定。然而,等級制度在人們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權貴階級總是會通過各種手段來脫離法律的規范,沒有絕對的實質平等。等級主義是禮制的重要特點,其對中國法律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歷朝歷代的法律都根據該法律文化進行了相關規定,以確保設立嚴格的等級制度來更好進行統治[6]。
(四)封建主義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禮”。“禮”指的是嚴格的等級制度,即西周初期周公旦創立的“周禮”。“周禮”是對人們在各種社會活動中形成的有次序的禮儀抽象概括和歸納總結后進行的文字化、規范化和制度化,是維護奴隸主貴族階級利益和等級社會秩序的強制性工具。“禮”強調的是嚴格遵循等級秩序,通過百姓對禮法的遵守來鞏固君主專制的社會。皇帝往往是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在社會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能夠根據意識觀念來不斷影響法律的制定,使得法律成為保障其統治權威的工具。封建主義強調的是君主的絕對的權力,禮制是君主維持統治的工具,這種“君權天授”的封建主義色彩對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影響,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根據制定相應的法律來維護特有的統治地位。
四、結語
中國自古就是遵循禮制的國度,禮制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始終有著重要影響,是基于我國本土文化而產生的一種延續數千年的規范社會關系的制度。禮制的發展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從而適合特定歷史時期統治階級的統治需求[7]。禮制的發展也在不斷豐富著中國法律文化的內涵,以期讓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法律文化。雖然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了法治社會,禮制依舊對人們的生活產生著影響,對如今法治社會建設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