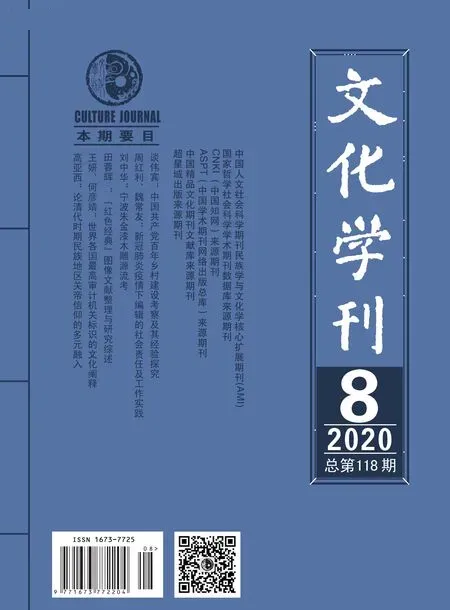關于刑事訴訟中瑕疵證據的研究
楊凱涵
作為最能還原案件事實的材料,證據是確保刑事訴訟得以有序進行的前提和基礎。早期,我國證據被劃分為合法證據和非法證據兩大類,但在刑事訴訟的實踐中,并非所有收集來的證據都能夠“一刀切”地劃分進合法證據和非法證據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對立排斥范疇中,介于合法證據和非法證據之間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被稱為瑕疵證據。目前,我國初步形成了以“合法證據采納,非法證據排除,瑕疵證據可補正”為標準的證據制度。然而,由于規定缺乏一定的明確性,加之司法實踐的復雜性,使得適用上爭議不斷。因此,針對瑕疵證據的相關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
一、瑕疵證據概述
根據相關理論,瑕疵證據是指收集證據的程序、主體或者證據自身存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錯誤的證據[1]。這些錯誤并非實質性錯誤,而是一些輕微的瑕疵,通常可以通過補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釋的方式進行彌補,從而恢復證據能力或證明力。除具有作為證據所必須具備的客觀性和關聯性,瑕疵證據還具備區別于兩者的獨有屬性。第一,輕微違法性。這是區別于合法證據和非法證據最顯著的特性。瑕疵證據雖不具備當然的合法性,但其也并不具備與非法證據等同的法益侵害性。非法證據侵犯的是公民憲法性權利,而瑕疵證據侵犯的只是程序性權利或一般實體性權利[2]。也正因如此,人們對瑕疵證據才有一定的寬容度,如此才有了“先補救再排除”的規則。第二,效力待定性。瑕疵證據的這一特性是由其輕微違法性所決定的。瑕疵證據因其本身存在著輕微違法,不能自始具有證據能力,遂無法作為合法證據被法官采信。按規定程序消除瑕疵的瑕疵證據可成為合法證據,無法補正也不能提供合理解釋的將被視為非法證據,不具備證據效力。第三,可轉化性。瑕疵證據并不是證據的最終形態,只是待轉化的中間形態,在審判機關做出裁決時,要么其是以“合法證據”被采信,要么是以“非法證據”被排除。暫且不論其轉化后是否能被采信,法律基于瑕疵證據的性質,為其提供了可轉化的機會。
二、瑕疵證據的相關法律規定
2010年出臺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兩個證據規定”)首次確立了瑕疵證據的種類以及補救規則。隨后,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瑕疵證據的補救規則做出了基本法律層面的認可。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進一步豐富了補救制度的內容,明確了補救規則的適用范圍從死刑案件擴大至所有刑事案件。201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對補正和合理解釋做出了進一步規定。盡管法律上對瑕疵證據種類進行了列舉,確立了補救規則,但還是比較籠統。相關法律規定對瑕疵證據的認定標準不夠確定、瑕疵證據的轉化方式適用不明、法官自由裁量性較大等問題始終困擾著這一規則的實踐運用。
三、實務中關于瑕疵證據規則的運用情況
以“瑕疵證據”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進行檢索,自2013年至2020年3月15日,包含瑕疵證據這一關鍵詞的刑事案件文書總計650篇。在司法實踐中,很多瑕疵證據是在審查起訴階段發現補正后得以適用的,因此并不會出現在判決書中。由此可見,瑕疵證據在司法實踐中是廣泛存在的。
(一)偵查機關對瑕疵證據的處理
偵查環節是瑕疵證據的“出生地”,盡管相關法律規定了一系列取證制度以規范取證行為,但在實踐中,由于一些客觀條件的制約,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仍存在諸多不規范之處,這便是導致瑕疵證據出現的最根本原因。偵查機關內部雖然擁有對獲取來的證據進行審查的機制,但往往僅是對證據的數量進行審查,缺少實質性審查。久而久之,內部審查機制流于形式,失去其真正意義,從而使瑕疵證據流入審查起訴階段。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因證據不足問題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偵查機關通常也只是進行形式上的補正和解釋,檢察機關又缺少其他行之有效的手段,這勢必會導致瑕疵證據的產生。
(二)檢察機關對瑕疵證據的處理
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一方面作為監督主體,承擔著對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審查的職責;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作為控方,承擔著打擊犯罪和保護公共利益的使命。在這兩方面的職責同時具備并產生沖突時,檢察機關很難做到完全中立。加之受我國傳統法律文化觀念的影響,司法實踐長期重實體輕程序,在對待證據的處理上,檢察機關往往更注重證據的真實性,通常會忽略偵查人員取證程序上的輕微違法。只有在影響到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時,才會采取相應措施。盡管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于需要進行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而在實踐中,進入補充偵查程序的,相關主體也多采取做出合理解釋的方式進行形式上的補正,補正后在審判中被法院的采信率較高。由此,法律所規定的補救措施在實踐中已逐步演化為使瑕疵證據形式合法的一種形式主義手段,并不能實現立法背后所追求的有效轉化。
(三)審判機關對瑕疵證據的處理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法官對瑕疵證據有資格依職權進行主動審查。實踐中,由于案多人少、案件復雜、審判壓力過大,法官往往會選擇運用已有證據或僅僅對瑕疵證據進行程序性的補正,以求盡快結案。因此實踐中瑕疵證據多數由辯護人提出,法官卻表現出對瑕疵證據極大的寬容。在適用瑕疵證據“先補正再排除”的規則時,由于法律規范模糊以及我國各級各地法院眾多,導致瑕疵證據取舍的標準參差不齊。在司法實踐適用中,我國瑕疵證據的規則處于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很多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也因此產生,嚴重地影響了法律秩序和司法權威。
四、關于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瑕疵證據制度的思考
(一)明確瑕疵證據的范圍
目前,我國針對瑕疵證據的法條過于零散混亂,“兩個證據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中也是僅采用列舉的方法規定了瑕疵證據的種類[3],列舉出的形式遠遠無法涵蓋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形。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有諸多相似之處,若無法明確的界定,加之實踐中法官自身素質和經驗參差不齊,就會導致判定結果不同的情況屢屢發生。當然,現實世界千變萬化,法律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涵蓋所有實踐中可能遇到的情形確實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此,相關法律可以對實踐中出現頻率較高的類型做盡可能明確的規定,且規定要力求嚴格細致。雖然此舉沒辦法一步到位,實踐中也可以采取排除法的方式將這一規定明確化、體系化,從而努力接近這一目標,達到明確瑕疵證據范圍的目的。
(二)規范瑕疵證據補救的方式
《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了兩種瑕疵證據的補救方式,即補正或做出合理解釋,但卻并未做出細致的規定。補正,根據字面意思可理解為補充及糾正,即對證據存在的瑕疵進行修補,從根本上消除瑕疵;合理解釋,是基于瑕疵存在的前提對產生的原因進行說明,消除嚴重非法嫌疑,但這種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排除證據的瑕疵。據調查,偵查機關在對瑕疵證據的補救中,采取后者的頻率遠遠高于前者。對于偵查機關來說,作合理解釋顯然是更簡便快捷的方式,因此,法律應對兩種方式的適用先后順序予以規定,補正在先,合理解釋作為補充。只有在無法補正的情況下,才退而求其次選擇做出合理解釋。且解釋的理由要符合常理及一般經驗,并足以消除合理懷疑。另外,需對補正以及合理解釋所需達到的標準和形式做進一步明確的規定。可運用聽證的形式對證據進行審查,保證控辯雙方的參與權及知情權,避免瑕疵問題補正制度流于形式。
(三)完善相關配套制度的支撐
瑕疵證據的合理適用光靠自身的規則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相關配套制度的跟進與支撐。一要建立嚴格的瑕疵證據補正監督制度。在整個訴訟程序中,基于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審判機關三方各自的利益追求,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瑕疵證據采取較為寬容的態度。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檢察院應當充分發揮其監督職能,對于偵查機關的過失取證行為,公訴機關的審查不細致使瑕疵證據流入審判環節的行為,以及審判機關追求效率而未按規定方式進行補救等行為,應采取相應的制裁措施。二要積極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目前,我國法官審判案件很大程度依據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法官要想在判決書上體現出結果的合理性,就要依靠完整的證據鏈,故不能輕易排除證據,從而對于瑕疵證據也就更容易采取對其瑕疵忽略不計的態度,這是“偵查中心”模式所帶來的弊端[4]。因此,應當堅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明確審查搜集證據的目的是審判工作,按照審判環節對證據的標準嚴格依法收集、運用證據。還要完善鑒定人、證人出庭制度,以此防止偵查環節成為決定性環節,切實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三要保障辯方訴訟權利的充分行使。前文提到,刑事訴訟中,審判機關出于種種原因對瑕疵證據有著較大的寬容度,而辯方通常是瑕疵證據發現的主體,保障辯方訴訟權利的充分行使也有益于從另一角度對偵查人員,公訴人員起到監督作用。例如,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讓其充分了解與案卷相關聯的信息,在瑕疵證據的轉化過程中也要保障辯方充分的知情及參與。另外,對于辯方律師的閱卷、會見、取證等權利,目前司法實踐中仍然需要進一步有效落實,進而最大限度促進瑕疵證據制度的運用與完善。
五、結語
一直以來,我國司法界和理論界都對非法證據的研究投入了大量心血,而對于瑕疵證據的相關制度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實踐中,基于瑕疵證據產生的一些問題及其帶來的重大影響,瑕疵證據的制度也是不可忽視的。只有從理論層面進一步完善關于瑕疵證據的規定,使之更加明確具體,配合實踐中相關制度的支撐,才能使這一制度充分發揮作用,從而更好實現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