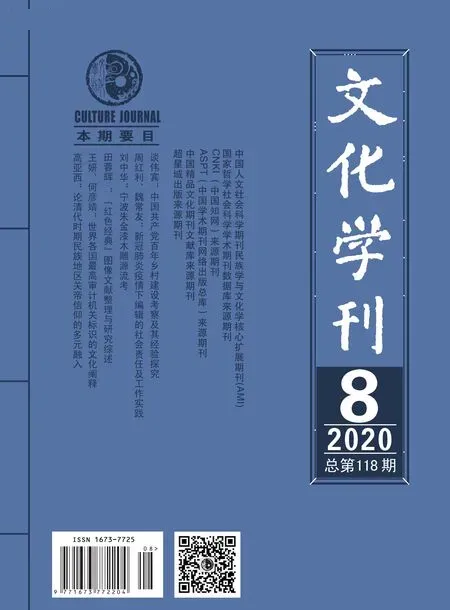抗日革命根據地婦女運動研究綜述
趙 楠
從1937年開始,中共中央就陸續發布了關于婦女工作的大綱與指示,如:1937年7月發布的《盧溝橋事變中北平和全國婦女界支援抗戰將士》;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頒布《婦女工作大綱》,9月13日頒布《陜甘寧邊區黨委關于邊區婦女群眾組織的新決定》,12月28日鄧穎超發表《對于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意見》……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中共中央對婦女運動的指示從未停止。本文主要對研究1937年以來各抗日根據地婦女運動的文章進行了簡單梳理,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
一、家庭婚姻與婦女運動
對于婦女家庭婚姻的研究,大多學者圍繞由于各邊區婚姻條例的頒布促使廣大邊區婦女從傳統婚姻的枷鎖中掙脫出來,以提高婦女的地位來論述。張志永將晉察冀邊區對傳統婚姻制度的改革分為反對虐待婦女、提倡婚姻自由和建設和睦家庭三個時期,他肯定了邊區在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與促進婦女解放運動中取得的成績,但同時指出邊區婚姻改革制度帶有一定的實用主義色彩,即改造舊式婚姻制度的初衷是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并不是以婦女解放為目的,從而導致婚姻制度改革流于形式而并不徹底[1]。田蘇蘇闡述了抗戰初期晉察冀邊區女性婚姻的真實狀態,著重強調了新婚姻政策的施行促使廣大邊區女性轉變了傳統的擇偶觀念,掙脫了封建陋習的枷鎖,因此大量邊區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與政治生活,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婦女們得到了解放[2]。郭磊與其觀點相似,他認為中共在山西頒布的婚姻法規推動了根據地的婦女解放運動,但也指出邊區的婚姻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改變,傳統封建習俗并未徹底被撼動,買賣婚姻和童養媳等現象仍然存在[3]。
岳謙厚通過研究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25宗離婚案,考察了中共在晉西北地區處理女性離婚問題的具體方式。他認為《晉西北婚姻暫行條例》的頒布使根據地婦女的婚姻思想發生了較大轉變,原來飽受婚姻苦痛的婦女因此走出家門,通過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婚姻自主權。同時他指出,婚姻自由原則在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變時不可能實行,真正的自由要靠社會多重因素互相作用才可實現[4]。叢小平則質疑西方女性主義學者“父權至上”的觀點,反對西方認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了與父權制勢力進行讓步而實行婚姻制度改革這一說法。她以1942年左潤與王銀鎖的離婚案件為出發點,認為由于種種社會現實,邊區婦女在婚姻改革的具體實踐中確實存在向地方勢力妥協的無奈,但是考察婦女解放要把婦女放置在歷史之內,才能真正理解婦女解放的意義[5]。
二、生產勞動與婦女運動
抗日戰爭以來,廣大邊區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勞動以支持抗戰,除春耕秋收外,還積極募捐物資、慰勞傷員、為軍隊縫洗衣物做鞋等,婦女運動取得了巨大進步。許淑賢以山西省武鄉縣為例,從社會性別視角出發,概括了婦女紡織運動的特殊背景、特點與開展的具體情況,她認為正是武鄉婦女在勞動中不斷創新紡織工具,改變分工方式,才使紡織運動的效率得到了提高。婦女紡織運動的開展對婦女解放的意義在于不但提高了武鄉婦女的地位,而且使武鄉婦女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婦女紡織運動的典范[6]。劉潔與何然以太行山婦女為研究對象,將婦女從1939年到1944年參加生產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詳細闡述了中共為了開發女性勞動力、鼓勵婦女參加農業生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認為根據地婦女參加社會勞動不僅使婦女產生了新的勞動觀念,改善了婆媳關系與夫妻關系,也極大提高了婦女的政治地位[7]。劉曉麗認為紡織運動成為根據地軍民渡過難關、堅持抗戰的有效手段,山西婦女的紡織運動使根據地婦女的地位得以提高,在最廣大意義上解放了婦女,并使她們認識到自己的人生價值[8]。
李常生探討了動員山西根據地的農村婦女參加生產建設的方式,如提高婦女的文化水平,培訓婦女的勞動技能,實行減租減息,組織婦女變工組、合作社等。山西根據地對婦女勞動力的開發,使大多數農村婦女擺脫了單一的勞動方式,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也為農村婦女的解放創造了良好條件。他認為婦女參加社會公共勞動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應該實現婦女自身的解放[9]。王穎在文章中主要講述從1943年開始,為改善婦女地位,陜甘寧邊區政府由動員婦女參政轉為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其內容主要包括組織婦女個體與集體生產、生產與家庭相結合、以各種合作生產方式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勞動。這一轉變提高了婦女的勞動自主性,使婦女真正擁有了經濟自主能力,廣大婦女紛紛走出家庭,在婦女運動中真正收益[10]。
三、風俗改造與婦女運動
目前學術界關于婦女風俗改造方面的文章,多集中于婦女的放足運動研究。黃正林以陜甘寧邊區婦女為研究對象,他認為邊區婦女風俗改造的重點是纏足陋習在法律上的廢除,這一改造讓婦女的日常生活與勞動變得更加方便,使婦女的家庭與社會地位得到提高,改良了當時社會輕視婦女的不良風氣,從而得到了婦女的大力支持[11]。呂倩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隴東地區為例,通過描述反纏足運動的歷史過程,指出婦女的反纏足運動是在解放婦女生理的基礎上促進婦女心理上的解放,使得廣大婦女沖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縛,婦女尋求自身解放的思想逐漸萌發,放足婦女因而成為特別的“戰斗隊伍”,為抗戰和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12]。
江沛和王微在文章中通過分析放足的必要性與具體情況,認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推行的放足政策的確卓有成效,形成了新的審美觀,同時指出多數中青年女性在放足后在身體上仍保有殘缺,因而在評價中共各根據地婦女工作的強度及廣度時需要謹慎[13]。楊興梅指出,1945年以后,中共的反纏足運動逐漸與土改、生產及支前運動結合起來,“禁止纏足”再次成為對農村婦女的具體要求,放足最終成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中共對陜甘寧邊區、山東根據地與太行山區等地放足的指示與措施,是爭取男女平等,反對一切封建束縛與壓迫,婦女得以解放的重要手段[14]。張雙鳳對抗戰前后和解放時期的甘肅隴東婦女反纏足運動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對上述不同時期反纏足運動的政策、宣傳和實際成效有深入的研究,她肯定了共產黨領導下反纏足運動的成功,為隴東婦女帶來了“新生活”[15]。
四、婦女教育與婦女運動
關于婦女教育的問題,多數文章是通過分析根據地的實際狀況來研究各根據地不同的婦女教育方式。董玉梅在文章中分別闡述了冬學運動、春學運動、民眾學校、鄉藝活動、黑板報等社會教育形式。這幾種教育方式取得了巨大成果,不但提高了農村婦女的政治思想與文化素質水平,也有效地把晉北婦女們動員到抗戰工作中,成為推動晉北農村婦女沖破封建牢籠、解放思想、徹底實現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徑[16]。周錦濤重點論述了陜甘寧邊區婦女教育從無到有的過程,認為發展婦女教育、提高文化水平是開展婦女解放運動的基礎條件之一,中共對農村女性的文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的教育體制,婦女們紛紛走出家庭,融入讀書識字的新型社會風氣之中;但也指出在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由于經濟與文化問題也存在著許多制約與問題[17]。張小梨指出,延安時期中共為適應抗戰需求不僅對婦女進行文化教育,還進行生活教育和政治經濟教育。通過這些方式,讓邊區婦女擺脫了陳舊觀念的旋渦,極大地提高了婦女的權利意識和參政積極性,使邊區婦女在文化思想等各個方面得到了普遍提升,成為新民主主義時期婦女解放的一面旗幟[18]。
王克霞則重點分析了沂蒙抗日根據地的婦女教育新模式,認為其采取的政治教育、思想解放、技能提高“三位一體”模式是符合黨要求和抗戰形勢的婦女教育方式,這種新模式極大保障了抗日根據地的婦女干部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婦女教育的順利發展,是中國抗戰勝利的重要推動力量[19]。胡小京在文章中總結出推行婦女教育是動員婦女參與抗戰的先決條件,中共在建黨初期就十分重視婦女工作,對根據地的婦女教育問題提出了較多指導思想,認為黨的領導是婦女教育的關鍵,應當積極實施婦女教育。在解放婦女思想的同時,也為黨培養大量的優秀婦女干部,使得邊區婦女在抗戰的烽火中“大放異彩”[20]。
五、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婦女運動的總體論述
目前學術界對各個抗日根據地婦女運動總體論述的文章數量繁多。程艷芳闡述了山西開展婦女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開展反纏足運動、推廣識字運動、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等。肯定了山西婦女在集資募捐、慰勞抗戰將士、宣傳堅壁清野等工作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同時指出山西婦女運動在組織上存在干部分配不平均、工作上存在會員發展不充分、工作內容不統一等問題[21]。郭小萍以瓊崖婦女為研究對象,著重闡述了瓊崖婦女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抗日宣傳工作、參軍參戰和支援前線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也肯定了瓊崖婦女在推動婦女運動和抗日戰爭中發揮的巨大作用[22]。童學蓮考察了隴東地區婦女解放的背景、具體內容及影響,肯定了隴東婦女為抗戰做出的積極貢獻。但她認為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婦女解放運動以及全國的婦女解放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我解放,婦女的自我意識并未覺醒,而是黨和政府為了革命的需要才對廣大婦女進行的宣傳和動員[23]。荊璐通過考察全面抗戰爆發前時期晉綏邊區婦女的生存狀況以及全面抗戰時期晉綏邊區婦女參加大生產運動、參加四大動員、參與政權建設、接受文化教育等主要內容,總結了晉綏邊區婦女運動的經驗和教訓[24]。
總體研究抗日根據地婦女運動的文章最多的則是研究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文章,如黃正林詳細論述了陜甘寧抗日根據地婦女的習俗、婚姻、教育、勞動、參政議政以及社會意識從“舊”到“新”的轉變。由于陜甘寧婦女們在家庭與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她們從受封建束縛的家庭婦女成為尋求自身解放的新時代婦女,她們的社會意識、民族意識覺醒,抗日積極性高,為中國的婦女樹立了新形象[25]。周錦濤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運用各種方式積極推進婦女自身解放:倡導放足與婚姻自主運動,鼓勵邊區女性進行身體解放,建立各種婦女組織等。他認為,中共在陜甘寧邊區的改革成功整合了邊區婦女力量,贏取了廣大婦女的政治認同,很大程度上增強了自己的后方保障[26]。王建華論述了抗戰爆發后,為了解放陜甘寧邊區婦女,中國共產黨通過努力擴大婦女組織、進行婚姻改革、提高婦女思想文化水平等方式動員婦女參加抗戰。他認為,在特定歷史與時空條件下,女性解放運動應該以女性為出發點[27]。
總體而言,目前學術界對于抗日革命根據地婦女運動的研究日趨完善,內容也很全面。通過研究抗日革命根據地的婦女運動,不但能使我們清晰地了解當時廣大婦女對婦女解放運動的真實反應,也為我們今天婦女工作的開展提供許多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