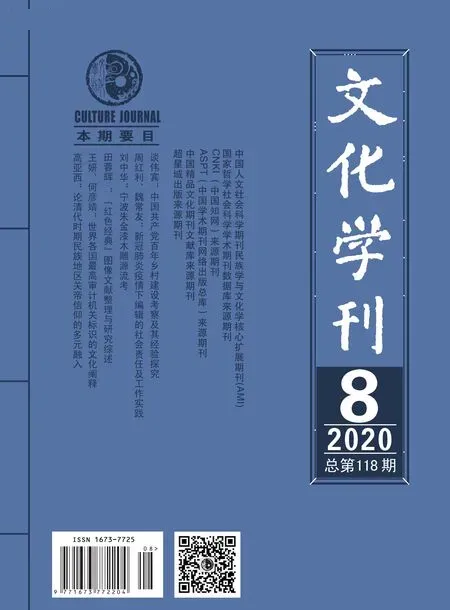從《世說新語》看魏晉世人的家族觀念
黃馨慧 范學新
《世說新語》成書于南北朝時期,據傳為南朝宋劉義慶文人集團所作。撰寫這部作品時,文人才子有意無意地在作品中展現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這使得這部作品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文人名士的言行生動地呈現家族觀念,其力量之強、影響之深,已然成為魏晉南北朝區別于其他歷史時期的特征之一。
一、家族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一種觀念的形成必然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觀念的興盛正是與那個時代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迅速提高相關。自漢高祖劉邦下求賢詔到漢文帝舉賢良、行策問,察舉制度逐漸成為漢代任用官員的重要手段。隨著察舉制度的深入施行,朝廷政治趨向混亂渾濁,舉薦賢才的名額逐漸落到了權臣手中。這些官員多徇私舞弊,任人唯親,在朝中形成了復雜而龐大的關系網絡。在這種關系網絡中,親族子弟間彼此扶持,不斷增加對權力的把控,其家族的社會地位也由此提高。許多家族依靠升遷在短時間內發達起來,躋身高門貴族之中。家族的快速發展使得族人的自信心不斷膨脹,達到頂端后就出現了排他性。這種依靠家族力量、以家族為中心、以家族利益為自身利益的家族觀念便由此形成。
隨著漢朝政權的衰落,中國進入了分裂割據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戰爭不斷、自然災害接踵而至,人的性命岌岌可危,此時家族的凝聚力便凸顯出來。為了躲避災禍,各家族內部成員之間、各家族之間通過聯姻等形式結成同盟,互幫互助,共同筑成一道抵御戰亂的堡壘,家族凝聚力空前增強。魏文帝曹丕為了鞏固政權拉攏世家大族,施行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發展到晉以后,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政治現象。此時,家族力量已經成為族中子弟進入仕途的主要政治力量,以家族利益為重的家族觀念也愈加強烈。作為漢代世家豪族的延續,經過了幾百年發展的士族,在《世說新語》的成書時期已經開始由盛轉衰,家族觀念也呈現出死板化、極端化的傾向。
二、家族觀念的表現
在《世說新語》中,人物的所言所行經常在不經意間將當時盛行的家族觀呈現在讀者面前。綜合書中事例,家族觀念主要體現在舉薦賢才、教育子弟、婚姻聯合、排斥寒門和重家族利益五方面。
(一)舉薦親族之人
推舉賢才之時,文人名士往往率先推舉家族中有德行才干的人,以家族為單位的士人集團在這一時期表現出明顯的“親親”思想。如《言語》第七則中,荀爽向袁閬舉薦才德之人時先及親人,且對自己的“親親”思想表現得理所當然、毫不避諱,后又舉祁奚、周公旦和《春秋》的例子作為佐證。這說明舉賢以親在當時已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為人所接受。又如《賢媛》第七:“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至,帝核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1]雖然許允推舉之人德才兼備,為官稱職,但相比于外鄉外族,許允更愿意推舉同鄉親族之人,其行為顯然是受到了以家族為核心的“親親”思想的影響。這種任人以親、親族優先的選官制度與中國古代普遍的“避親以避嫌”的思想相違背,是當時士族林立的社會大環境下的特殊產物。
(二)重視族中子弟的教育
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的興盛主要依靠族人在朝廷中的政治影響力。為了維持和穩固家族的社會地位,促使家族進一步發展,世家大族特別重視對族中子弟的培養。比如《言語》四十六則:“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2]在這段描寫中,謝仁祖八歲時就已經對迎來送往、人情世故之事熟練于心,其父謝豫章帶著謝仁祖送客,意在培養其世家大族之禮。再如《言語》七十八則,謝安就晉武帝賞賜山濤一事考驗子侄,這充分反映謝安對家族下一代教育的重視。只有后人德才兼備,依舊牢牢掌握政治力量和中央權力,這個家族才能繼續發展下去。這不是謝氏一族獨有的行為,而是當時眾多世家大族的普遍行為。《夙慧》第一中就言陳太丘責備兩個兒子沒有招待好客人,但聽到兒子們是因為學習而犯錯,陳太丘就原諒了他們。相比守禮,陳太丘更看重孩子們的學習之心。由此可見,嚴格培養族中子弟已成為當時社會的共識。
(三)通過聯姻促進各族聯系
世家大族之間的聯合往往以聯姻為主要途徑,形成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穩固士族關系網。在這種關系網中的士族之間多呈現一種互助形式。如《方正》二十五中:“于時謝尚書求其(諸葛恢)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3]這段借諸葛恢之口點明了世家大族之間聯姻結成同盟的目的是互相幫助,以穩固、擴大勢力,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同時,一些地位較低的家族或根基不穩的新興家族也通過聯姻攀附地位顯赫的世家大族,以提高自己家族的政治、社會地位,鞏固家族根基。如《賢媛》十八中李絡秀堅持嫁周浚為妾,欲利用與富貴宗族的聯姻,給李家帶來好處。后又半強迫自己的子女與李氏家族做親戚。為了家族利益,李絡秀自請做妾,并如實說出自己的真實目的,不但沒有招致夫家反感,反因其為家族的付出而受到夫家的公正禮遇。可見,當時通過婚姻提升家族地位的辦法較為普遍。李絡秀犧牲自我的際遇也說明,當時世人以家族利益為重。
(四)對寒門庶族的排斥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林立的家族之中,相比世家大族來說,寒門庶族數量之多無法細數。受家族彼此聯合的社會風氣的影響,這些家族大多想攀附高門貴族以發家進入仕途,或博取名聲。久而久之,真正的豪門大族開始對寒門庶族產生了一種排他性心理。加之其自身地位所帶來的自信和優越感,這種心理便演化成一種對寒門庶族的鄙視、厭惡的情感。[4]如《方正》五十一中劉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5]在劉真長看來,世家之人與平民百姓身份地位差距懸殊,世家大族的子弟不可輕易與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結交,這種高人一等的自信心理正是家族給他們帶來的。《方正》五十二講述了王修齡在貧乏之時也不接受寒門陶范的米,反而出言侮辱陶范一事。王修齡的家族本就是東晉的豪門大族,而陶氏一族出身寒門,作為高門子弟的王修齡對地位低下的庶族子弟有一種本能的厭惡與排斥,這說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世人對家族社會地位十分看重。家族間彼此的排斥和傾軋使當時本已混亂的社會環境更加混濁不堪。
(五)一切以家族利益為重
受社會環境以及當時九品中正制的影響,家族已然成為族中子弟遮風擋雨的屏障以及平步青云的臺階。俗語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使家族內部的成員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以家族為中心、維護家族整體利益的心理。如《賢媛》十六:“王司徒婦,鐘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鐘、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鐘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鐘。”[6]為了維護家族內部穩定團結,讓在外的子弟無后顧之憂,鐘夫人克制對寒門子弟的排斥,郝夫人亦隱藏身份帶來的自卑,兩人和諧共處,共同支撐王氏一族,為世人所稱贊,此乃收入《賢媛》之因。又如《排調》十二:“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7]諸葛恢和王導兩人有此爭執,乃是維護家族利益、意圖通過貶低其他世家來抬高家族地位的緣故。這一爭執看似幼稚可笑,背后卻是兩大世家貴族政治的糾葛和家族的較量。在內維護家族和諧團結、悉心培育族中子弟,在外為家族爭取榮譽地位、聯合其他世家鞏固權力,已經成為當時時代背景下的社會共識。
三、家族觀念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觀念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精神力量。在無休止的戰亂之中,家族觀念用它的凝聚性帶給世人些許的精神慰藉和人身保護。當這種凝聚發展到一定程度,家族觀念已經轉化為人們以權謀私、政治斗爭的精神動力和借口。在家族觀念的影響下,各個家族著眼于努力擴張自己家族在朝廷和社會上的地位、實力和影響力。也正因為如此,隨著門閥制度的不斷發展,呈現出家族內部的聯系愈發緊密、家族外部的聯合和傾軋愈發激烈的社會現象,進一步攪渾了當時本已混濁的政治池水。世家貴族的壟斷地位發展至后期,已然成為足夠威脅皇權的驚人政治力量。這也是隋唐時期大一統后,門閥制度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本原因。家族觀念促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的迅速成長,卻也給盛極一時的世家貴族模式帶來了滅亡。雖然門閥制度被專制君權壓制并最終消失,但家族觀念卻一直流傳下來,對后世也有重要的影響。
從《世說新語》中可以看到,在魏晉時期,受政治及社會環境的影響,家族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獨具特色的時代風尚。其對后世的影響之深遠亦是罕見,在歷史舞臺上占據了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