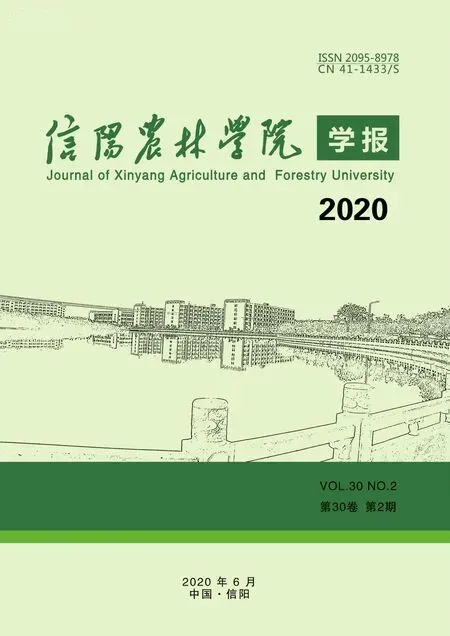田野札記、錄音筆與情感史
——阿列克謝耶維奇現代性記憶書寫方式
李柯霓
(華東師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上海 201100)
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一位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的白俄羅斯作家,雖然沒有親歷戰爭,卻誕生在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家庭之中,因此,擁有屬于蘇聯那一代人的“二手時間”。經歷過《普里皮亞季真理報》與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的新聞寫作訓練以及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訓練的阿列克謝耶維奇,擁有不同于一般文學創作者的“非虛構寫作”視角,也奠定了她其后所有寫作的基礎。她通過直接個人記憶與搜集而來的后記憶(postmemory),修筑起屬于蘇聯—俄羅斯一代人的“烏托邦”,再現了蘇聯衛國戰爭、切爾諾貝利核泄漏、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等一系列蘇聯歷史上的關鍵時間。作者在其中完成了他者與自我的記憶書寫,呈現了一本不同于官方文獻的田野紀念冊。
記憶書寫作為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與文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著眼點,其不僅具有史料價值,也具有較強的文學特征。近年來研究本身也發生了重大的轉型:從宏大書寫轉向個體化書寫,從追求唯一“真實性”到“增補”(supplement),從理性書寫轉向感性化書寫,從結構化轉向碎片、零散化。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文學書寫之中,展現了記憶的現代性轉向,從文學的層面展現了現代性的記憶應當如何書寫。
1 田野空間:話語體系的解構與建構
阿列克謝耶維奇構建了一個有別于上層政治空間的民眾空間,并且賦予被壓抑的群體以表達的話語權利。她解構了傳統的權力話語體系,在田野空間中找到了現代性記憶重塑的方法。
福柯在就任演說中提到,“在任何社會中,任何說話和論述規則,實際上就是強加于社會的某種‘禁令’。也就是說,通過語言表達形式所表現的各種說話和論述規則,實際上就是對于說話和做事的某種‘限制’,即向人們發出某種‘禁令’,在教導人們怎樣說話的時候,實際上禁止人們說某些話和做某些事”[1]132-133。社會中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歷史講述話語機制,縱使是看上去被小人物講述的歷史,由于他們選取的語言本身已經制定了一套邏輯與論證系統,他們無法跳脫出這套體系進行記憶書寫。社會上層的話語體系是一種懸浮在社會整體之上的“幽靈”,它制造了一種政治真實。在《鋅皮娃娃兵》中,它既成為欺騙娃娃兵們走上阿富汗戰場的工具,也成為欺騙他們家人的理由。娃娃兵回憶“可是我兩次受騙,沒有告訴我真相,沒有說明那是一場什么戰爭”[2]31,他們的妻子得到的官方回答是“他自愿申請去的”[2]31,而實則他們卻是在酒醉之后被投入鐵皮艙之中。上層話語體系將阿富汗戰爭包裝成為一場正義之戰,為保存阿富汗革命成果,并在現實生活中隱瞞鋅皮娃娃兵們的死因,也禁止幸存者回國言說自身在阿富汗戰場上的經歷,使得處于“田野”之中的小人物們的話語被閹割,成為潛藏在海洋之下的巨大冰山。
然而阿列克謝耶維奇仍試圖去打破這種既定的話語機制,她運用錄音筆作為記錄工具,幾乎記錄了對于受訪者采訪的全過程,在整個話語記錄之中,她企圖尋找到話語本身的裂隙。每個人的講述本身就存在大量的矛盾點,作者的工作便是在大量龐雜繁復的口述之中找尋二元對立的沖突點,不是抹平,而是呈現,并用這種沖突的并置,凸顯記錄文學的獨特的“戲劇沖突”。她曾發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存在著兩種真實:一種是強行掩藏于地下的個人真實,還有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的整體精神”[3]100-101。《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一位上等兵拒絕去回憶這段可怖的歷史,她說“我能記住的就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孤獨感”,在殺死第一個人之后“心里害怕極了”,這與官方話語中宣傳的“英勇善戰的女戰士”形成強烈的落差。《鋅皮娃娃兵》寫到:“您千萬不要寫我們在阿富汗的兄弟情義。這種情誼是不存在的,我們不相信這種情誼。打仗時我們能夠抱成團,因為是恐懼。我們同樣上當受騙,我們同樣想活命,我們同樣想回家。”[2]21官方宣稱阿富汗戰場上的軍人們同仇敵愾,而實際回憶之中,戰士們不過是因為過于恐懼而抱成團。作品中的每個個體身上都存在著有悖于表層話語的部分,正是這種呈現引發了歷史觀察者們的深度思考。
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的獨特話語處理方式,是將多種聲音并置,形成一種復調色彩。但這種“復調”并非先前研究者所分析的,是作品內不同的敘事者的“復調命運交響曲”[4]489。先前研究者大多忽視了阿列克謝耶維奇“復調”之中的另一層指涉——上層空間與田野空間的兩重性。田野的聲音與上層的聲音并非簡單的交織關系,而是具有多重性。其中的小部分,是交織的關系,即講述主人公既認同主流話語,又對其保持一定的懷疑。而大部分,兩者對于同一事件的闡釋是相互對立的,即主人公認為主流話語具有欺騙性,他們對于事件本身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主流話語。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種類型,即上層空間與田野空間仿佛處于完全異質的時空之中,他們互不干擾,幾乎沒有交集。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二手時間》一書中摘錄了一個十分獨特的人物的采訪。這個生活在偏遠農村的老人仿佛是整個國家的“局外人”。對她來說,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樣,在巨大的時代震蕩中,她什么都沒有失去,也似乎什么也未得到。她只等待春天,那時候又可以開始新一輪的播種,而春天總是會來的——不像某些別的希望。這些小人物處于一種閉鎖的狀態,幾十年來都只關心那些生活必需品。普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
2 錄音筆:從唯一“真實性”到“增補”(supplement)
歷史學研究轉向后,出現了具有現代性的新的歷史研究方法,人們開始關注歷史本身的真實性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歷史研究不再追求唯一的“真實性”,而是找尋到了一種歷史真實的建構方式——“增補”(supplement)。不再強調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而是通過不斷增加他者,產生無限趨近于歷史真實的效果。就如同阿列克謝耶維奇手中的錄音筆,它客觀地、無選擇性地記錄下眾聲喧嘩,不主觀制造二元對立。它通過不斷記錄下碎片式的記憶,使其共同拼接成為一面完整的記憶墻,使歷史的玻璃去霧、祛魅(Disenchantment)。正如阿蘭·巴迪歐所言“正是事件突現和主體介入構成了真理生成機制”,多重主體的引入促成真理浮現。
《二手時間》對于傳統的單一“真實性”的質疑最為強烈,因為在蘇聯解體這段劇變時刻,沒有“高高在上”的國家意志占統治地位,只有紛繁、混雜、失落與找尋。大眾傳媒已經不能再提供所謂“真相”,或者哪怕只是一種官方宣傳的“真相”。人們說:“我買了三份報紙,每份報紙都在說自己寫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5]正如同作者在一次采訪中寫道,“她們兩人的故事中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名字。不過她們兩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有她們自己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5]33。處于這一時代背景下的每個人的故事都不相同,但也并非對立,他們的存在不是為了否定他者,而是為讀者提供一種跟隨口述者進入歷史本身的入口。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所有作品都在試圖尋找一些邊緣的“增補者”。從二戰中只出現在不為人知的隱秘角落中的女兵、被無辜卷入戰爭的兒童與一些下等士兵,到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中消防員的妻子、流離失所的難民;從經歷蘇聯解體政治信仰失落的普通人,到成為阿富汗戰爭犧牲品的娃娃兵。他們無一例外都站在官方核心歷史的邊緣。
這些“增補”看似是破碎、隨機與零散的,但實則他們形成了新的“容貫的平面”。這個平面與皮埃爾·諾拉提出的“自我盤繞的莫比烏斯環”[6]24有相似性,它們雖然彼此之間并沒有銜接,但永遠在同一個單側曲面上,是對同一歷史事件的描繪,擁有共同的歷史任務。這個新生成的“容貫的平面”,是一種“沒有開端與終結”、“體系中的任意兩點之間皆可連接,體系內部保持內在的開放性、動態性與多維關聯性”的新場域。從某種程度看,文本中的不同講述者之間也存在對話關系,他們之間是開放互動的。《二手時間》中每一位后蘇聯社會中的普通人,仿佛都在針對“無產階級生活與資產階級生活的選擇”這一命題進行研討與對話。《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中,每一位被迫納入“切爾諾貝利人”身份的普通人,開始共同思索這次慘絕人寰的、空前的災難。他們的生活被這次災難聯系在一起,共同書寫了一部邊緣的災難史。不同的講述者可能持有類似的觀點,抑或完全相反的觀點,而這也是歷史本身的開放性造就的,也使歷史有多重的入口,即德勒茲所言:“一個根莖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斷,但它會沿著自身的某條線或其他的線而重新開始。”[7]10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我們不需要從頭開始,我們可以從任何一個故事進入,向前或者向后閱讀,選擇自己希望跟隨的講述者進入歷史之中,以新的視角觀看歷史。讀者仿佛掌握了一種“上帝視角”的權利,跟隨著作者的增補去還原歷史,淡化早期歷史研究的中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歷史是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烏托邦”,而這也許就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為何稱其作品為“烏托邦之聲五部曲”的原因,縱使通過不斷的“增補”與解構,逐漸接近歷史本身的面目,但終究不可能達到歷史的絕對真實,但正是類似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文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們不斷的努力,才使得我們更加趨近歷史。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說:“一切都不可靠。今天被認作是真理的東西,明天就不是了。一切都處于變化中,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迷信。”
3 情感史編撰者——“情感文獻”與“創傷修復史”
阿列克謝耶維奇仿佛一位人類情感宮殿的塑造者,她不拘泥于單純的口述記憶或者歷史記憶的單純講述,而是融入“多汁而豐沛”的情感,使得其筆下的作品都化為一卷卷情感史文獻。正如其自身談到,“我不只是干巴巴的歷史,一個個事件,一個個事實,而是在寫一部人類情感的歷史。人在事件發生期間想了什么、理解了什么,又記住了什么”。薩拉·鄧尼斯說:“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里……她所寫的不是單純的歷史,也不是僅僅敘述事件,而是寫下了一部部情感史為我們描述了人們的情感世界。”[4]489
現代性的記憶書寫更加強調“個體化”“解構”以及“口述歷史”,而這些關鍵詞都與情感密不可分,感性對于理性的超越促成了不同于傳統的記憶書寫。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文本同時具有兩種特征:一方面,她的作品可被認為是一種情感創傷的揭露與反映,是一部“情感文獻”;另一方面,它們也起到情感修復的功能,被認為是一種創傷的愈療手段,是一部“創傷修復史”。
作為“情感文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存在較多“刺點”,促使講述者與讀者一同走進那些鉛字背后的“創傷記憶”。“情感文獻”的一種“刺點”是依靠感官知覺激發的,作者常常運用的感官是視覺與嗅覺。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我還是想你,媽媽》中,兒童對戰爭的回憶大多與色彩、味道緊密相連。他們對戰爭的記憶是印象畫派式的。他們會關注到夏日盛開的繽紛花朵,“丁香花就這樣盛開了……綢李花也這樣盛開了……”[8]15。絢爛盛開的鮮花與記憶之中最血腥、殘酷的戰爭并置,使記憶中的殘忍更加凸顯,激發潛藏的創傷;作品中一位心理學家回憶“我從小就記得宰殺野豬時家里的氣味”[9]42,一位鉗工回憶幼年經歷戰爭時說:“我記住了什么?新鮮的樹木的氣息……活生生的氣息……”[8]28,這種看似與戰爭、災難無關聯的碎片嗅覺感知,卻成為講述者每次回憶的觸發點。類似事件的觸發也是創傷記憶被揭露的一種途徑。一位口述者在深夜中聽到采石場中的巨響,會立即回想起戰場。另一層面來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記憶講述,本身也是一部“創傷修復史”。阿維夏伊·瑪格麗特談到“被壓抑的公共記憶被公開、被言說、被感知時,社會集體的創傷才有被療愈的可能性”。阿列克謝耶維奇為被壓抑的小人物們提供了一個言說途徑,他們的記憶由歷史底層被翻出,重見日光,從而使這部分記憶有疏解與愈療的可能。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文本之中展現的愈療手法有多種,如生物愈療、信仰愈療與文學愈療。
生物,包括動物與植物,預示著生命力與活力。在災難與戰爭之中,人表現得脆弱不堪,生命隨時會消逝,而有時候在此種孤獨境遇中,生物的存在狀態為人自身的生活提供了希望。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作品中大量描述生物。《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中,疏散區居民巴達耶娃在講述的最后說:“莊稼發芽了……長得真壯實……”[9]75;一位受災的語文老師說:“墻上、房門、天花板、屋頂,我都插滿了柳條”[10]204;一位講述者說:“現在我的鐳(講述者的狗的名字)跑出去了……我擔心,它跑到村外會被狼吃掉,那樣的話,就只剩我一個人了”[10]60。這些生物是講述者們的情感寄托,也是帶其走出黑暗創傷的治愈之物。信仰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是另一種治療的方式,能夠帶給苦難中的人以存活的希冀。俄羅斯民族性格一直以來受到宗教影響較大。在早期多神教之后,東正教成為國家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系統,這種宗教觀念也融注于俄羅斯的文學傳統中。信仰愈療來源于宗教教義,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后,經歷者開始閱讀“上帝創造了世界,世界一定是完美的”[9]90等教義;一位火箭燃料專家與人們一起“建立一個教堂……切爾諾貝利教堂”[9]210;《二手時間》中馬利克娃講述在蘇聯解體之后,“每個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著去,開始畫十字、吃齋”[5]379。蘇聯解體之后,據統計數據顯示,宗教教會大規模增長,1991年俄羅斯聯邦的宗教群體數目5502個,到1997年已經達到14688個。在經歷了一系列難以言說的苦難之后,宗教信仰在情感上的支撐作用遠遠超過科技本身,人們企圖在宗教信仰中獲得救贖,“人們又開始相信上帝了”[5]81。文學愈療也是阿列克謝耶維奇常用的方法。一位受難者回憶,“前些時候,我找到了一大本普希金的集子……‘死亡在我看來十分可親’”[9]90-91,文學觸發人們思考,也使人們更加平靜地面對人生、死亡等事件。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確在書寫一部情感史,但其目的并非僅僅為了呈現,她更希望提供一種疏解方式,使經歷者與閱讀者能通過文字的途徑得以凈化。
4 結語
阿列克謝耶維奇開拓出獨具一格的記憶書寫方式,她將文學領域的記憶書寫無意識地帶入現代書寫場域,賦予其現代風格。在她筆下,記憶已經遠遠超越個人范疇,成為民族、國家與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檔案,甚至成為歷史類影視作品拍攝的參考背景之一。近期HBO(Home Box Office)電視網新出了一部有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電視劇,故事大多取材于《切爾諾貝利的祭禱》。在某種程度上,記憶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已經實現了合法化的歷程,同時,更進一步,她也為邊緣記憶的疏導與愈療提供了方法,讓那些擁有還未被挖掘出的記憶與難以言說的記憶的承擔者看到了希望。“非虛構文學”與“文獻文學”的社會價值與功用性得以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