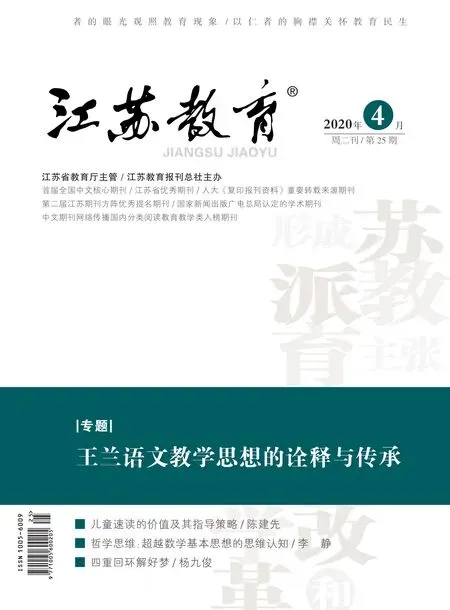蘭幽香風遠: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
成尚榮
王蘭老師是我敬仰的前輩。評說她的教學風格,正是向她學習的過程,是對她教學思想、教學藝術、教學經驗詮釋的過程。在詮釋中理解,在詮釋中學習,在詮釋中發現和弘揚。
記得在她70 歲生日時,我曾送給她一盆蘭花,因為她名字中有個“蘭”字。不僅如此,王蘭老師就是高潔、美麗、優雅的蘭花,用“蘭幽香風遠”來描述她的風格是恰當不過的。名如其人,教如其人,在王蘭老師那兒都是統一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這是一種自然的邏輯,是一種美的象征。而美又召喚著道德,又滲透著情感。借用李澤厚“情本體”的表述,我倒認為,用“美本體”來描述王蘭老師是恰如其分的。
于是,大家都公認,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就是三個詞:本真、美麗、和諧。她的語文課是一件件藝術作品,稱她為“四十分鐘里的藝術家”,準確、形象。她的教學藝術,絕不是個教法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藝術讓她走向本真,是本真讓她美麗,是美麗讓她走向和諧的境界;是本真價值觀照下的藝術,又是美學精神在她教學中的高度凝練和生動體現,是和諧的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鍛造了她的教學文化性格與教育精神。
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如此鮮明地“立”在我們面前,是我們的標桿,引領我們向往詩與遠方。但她的風格又是那么親切、實在、鮮活地在我們的生活里,永遠散發著鼓舞的力量。
一、風格即特殊的人格,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是她美麗心靈的透射
法國博物學家布封說過,風格是關于人的。江蘇省教科院的孫孔懿說,風格是特殊的人格。吳冠中用一句比喻也道出了同樣的道理:風格是人的背影。無數事實證明了這一判斷:風格是人格的折射,沒有高尚的人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學風格。
王蘭老師有自己高尚的人格,她的心靈是透明美麗的。首先,她對祖國的摯愛。她經歷過戰爭年代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寄寓北京舅舅家,所目睹抗日戰爭的一切,在她心靈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是中國人,我愛自己的祖國。我是屬于祖國的,我是為了祖國的。其次,她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和擁護。她最喜歡唱的歌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20 世紀80 年代初,她終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把對黨的忠誠化為對教育事業的忠誠,化為對學生發自內心的愛。在王蘭老師心中,對黨的熱愛聚焦于為祖國教好每一個孩子。再次,她對偉大時代的感恩。她說:“改革開放是科學的春天,也是教育的春天。時代賦予我更重要的使命,時代也給我搭建了更廣闊的舞臺。”“如果說當年的我憑借著一腔熱忱,一股拼勁,出力流汗,踏踏實實,那么改革開放年代里的我則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膽創新。”
在王蘭老師的詞典里,不僅有大寫的“愛”,還有大寫的“真”。王蘭老師最看重真,最講真,對工作、對同事、對青年教師、對學生最真。從不說假話、大話、空話,而是講真話,講真情,不隱瞞,不回避,有時很尖銳。青年教師把她叫作“嚴厲而又溫和的奶奶”。內心的真,因而表現在教學中就是本真、求真。她認為,教學、語文教學來不得半點假,一切都真實地呈現在課堂上,就像陶行知所說的,在孩子面前,不能讓烏云擋住真理的光芒。因為本真,所以,王蘭老師的課堂里,南京市長江路小學的課堂里,一片明亮、一片燦爛。
王蘭老師以她的心靈告訴我們,教學風格不是刻意追求的,是在自己的人格中自然生長起來的。要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首先要鑄造自己的人格,風格是美麗心靈開出的花朵。
二、思想是風格的血液,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源于她的兒童觀,源于她的赤子之心
王蘭老師愛學生,學生也愛她。她有個習慣,每接一個新班前都要家訪。不是一般的家訪,而是有她的獨到之處。走訪每一個學生那是肯定的,她的家訪在于全面、深入、具體、真實。了解學生的情況,連家里人講什么方言,學生在家里和哪些人接觸,有什么愛好,家里有什么課外讀物,會認會寫哪些字,等等,都一一問到。有老師這么說:“這是在做一般的開學準備工作嗎?不!這是王老師把一顆老園丁的火熱的心,在學生未進學校前就貼在他們身上啊!”往深處說,王老師在追求教育的公平,讓每個學生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王蘭老師對兒童的認識是全面、深刻的。其一,基于兒童觀的教學過程,在于師生關系的和諧。她自己這么說:“我認為師生關系的和諧,是和諧教育的核心。因此,我們教師與學生情感的交融、心靈的溝通是至關重要的。其二,對兒童真正的愛,在于“用寬容的心態對待學生的過失,用期待的心態對待學生的每一點進步,用欣賞的眼光去關注學生的每一個閃光點,用喜悅的心情去贊許學生的每一點成功。”她還說,和諧的師生關系是牽動教育的“綱”。其三,對兒童既要愛,又要嚴。愛學生絕不是一味地“捧”學生,王蘭老師對學生慈嚴相濟,用藝術的方式對待學生的不足、犯錯。她的兒童觀是完整的,她的兒童立場里是有規則的,有批評甚至是有懲戒的。王蘭老師把愛與意志統一在一起,顯現了大愛和大智慧。
懷特海說,在風格之上有諸神的力量。這“神”的力量不是別的,就是思想,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是風格的血液,風格則是思想的雕塑。兒童觀,完整而又深刻的兒童觀,讓王蘭老師擁有思想的力量。王蘭老師告訴我們,教學風格離不開兒童,離不開兒童研究。
三、風格是教學過程中的整體風貌和鮮明的獨特性,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是兩者的自然而藝術的融通
有人對風格下過這樣的定義:風格是在藝術創作中,主體與客體的本質性聯系,用藝術作品表現出的整體風貌與鮮明的獨特性。風格必須具有鮮明的個性,而個性往往表現在獨特性上。老舍說,風格就是這朵花與另一朵花,顏色與香味都是不同的。但是,只把關注點、興奮點、著力點放在獨特性上又是很不夠的,甚至是不準確的,丟棄了整體性就無所謂獨特性,獨特性的背景是整體性,獨特性是整體風貌中顯現的一個最美麗的側面、最燦爛的那個點。所以,國外有個比喻:風格是一個立方體,而長比寬要多得多。這比喻不可深究,但主導意思是無可非議的。
在長江路小學有過關于“好看”的課的討論。比如有一位老師上二年級的《秋游》,一個個精彩的課件,忽而金黃的稻浪,忽而火紅的蘋果,忽兒黃澄澄的甜梨,學生一次次地大呼:“哇!秋天真美啊!”青年教師想上這樣的“好看”的課。一位青年教師在備《真想變成大大的荷葉》這首詩歌時,設計了一個環節:“小朋友,你們自己喜歡這首詩的哪一部分,就讀那一部分,學習那一部分。”王蘭老師看了教學設計,和老師有番對話:“來,請你說說自己喜歡讀哪段就讀哪段,你是怎么想的?”“我覺得這一設計體現了學生的主體性。”“你想過作者為什么這么寫嗎?”“這……真沒想過。”“說明你還沒有深入文本啊!作者的寫作思路是有一定順序的……文中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做老師的應當引領著學生深入文本,通過語言文字,思作者之所思,感作者之所感。”最后,王老師說:“我們不能和學生一起迷失在自我里,而失去學習語文本應該賦予我們的一切!”
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很多。如果說,獨特性是追求教學風格的一個著力點,那么追求教學的整體風貌應是追求教學風格的一個著眼點。這個著眼點,用王蘭老師的話來說,就是語文教學的“一切”。這是什么?這叫本真,這叫和諧,這叫精準,這就是真正的美麗。
其實,王蘭老師的教學風格,不只是體現在她自己的課堂里,而更多的是在她弟子的課堂里,在長江路小學老師的課堂里。這又告訴我們,一個特級教師、一個名師的教學風格,存在的最高價值在于薪火相傳,在于引領、培養一大批教師。王蘭老師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范。向教學風格致敬,先向王蘭老師致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