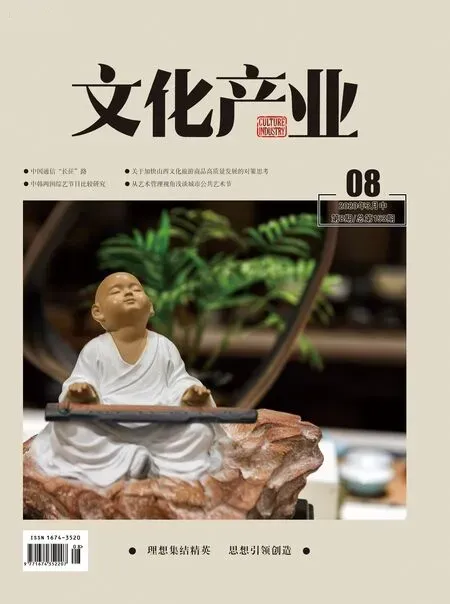淺談中國電影中江南影像的呈現
◎孫靖媛
(海南大學 海南 海口 570228)
關于中國電影的文化脈絡,香港作家倪震曾將之分為兩條:一條是邊塞大漠的西北文化,另一條則是杏花煙雨的江南文化。“江南”在地理空間上的界定為北起長江,南至福建武夷,東臨大海,地處長江下游地區,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區域。江南影像在中國電影史中豐厚文化意蘊的形成,離不開長江文明的滋養和哺育,自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以來,中國電影便與江南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溯源:中國電影的本土化地域空間選擇
在早期中國電影史上,江南影像的形成離不開上海,而上海又掌握著當時電影界相對權威的話語權:一方面,上海受其地理因素影響,自覺接受了江南千百年來歷史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上海從三四十年代開始迅速崛起,成為現代都市影像的標志,賦予了周圍江南地域以新的生機與活力。
上海是早期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隨著大量人口的遷入,中國電影產業化運作中觀眾和投資等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同時,一些新興電影設備的購入也吸引了大批電影工作者。袁牧之、史東山、張石川、吳永剛等著名導演,趙丹、王漢倫等演員皆與江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們或生于江南,或長于江南,在耳濡目染中感悟和揣摩江南的氣韻與風度,并將對江南文化的理解融入早期電影的創作之中,打造出《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等中國電影史上的杰出作品,極大程度上展現了早期東方電影之美。
在歷史的前提與背景下,中國電影對于江南地域空間的選擇絕非偶然,江南為早期中國電影輸送了大量人才,提供了先進的理論和學習的契機,使得江南成為中國電影重要的影像空間,也使得上海這個電影的發源地有足夠的文化內涵得以不斷發展壯大。
二、意蘊:剛柔兼濟、至柔至剛的東方美學
(一)梅雨時節下的“哀而不傷”
江南氣候溫潤,每到梅雨時節,江南的雨便綿延不絕。故而電影工作者們常常將其塑造成一個多情而柔情的空間意象,悲而不戚、哀而不傷,頗具東方美學和民族美學意味。
霍建起導演在作品《暖》中通過“暖黃色的陽光”和“綿綿的細雨”將影片的時空劃分為現在和過去,如果說,過去的時空中那金燦燦的暖陽為江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籠罩上一層美好的色彩;那么現在時空中所展現的陰暗潮濕,便是時過境遷、美好褪去后現實的苦悶。一切景語皆情語,這種如散文詩般含蓄蘊藉的表達方式,將東方電影之美在熒幕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可謂是詩意盎然、詩境充沛。
(二)沉重悲痛的“歷史喪鐘”
自古以來,文人墨客便喜歡稱道江南的美好,常常通過詩意化與虛構性來完成自身對江南約定俗成的想象,忽視了濃厚歷史煙云中侵略者留下的創傷。南京這座城市,便是在極盡的繁盛與瘡痍間輾轉輪回,又在戰爭的洗禮中蛻變、沉淀,歷經滄桑卻又不失溫和天真。
新千年后,陸川、張藝謀等導演將目光聚焦在抗日戰爭時期歷經磨難的南京城,通過塑造一批批善良勇敢、充滿人道主義光輝的江南人物形象,直面殘酷的歷史,捍衛民族的尊嚴。在電影《金陵十三釵》和《南京!南京!》中,江南女子外柔內剛的性情與法西斯冰冷的刺刀形成鮮明的對比。當中國電影對江南影像的描繪從自然逐漸轉向人文的同時,也將江南堅韌、剛強的一面展現在觀眾面前,而其折射出的“人情美”“人性美”剛柔兼濟,至柔至剛,使江南文化意蘊變得更加深厚、立體。
(三)藏匿于內心深處的“江湖想象”
江南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文明之美,亦藏匿著中國人內心深處對于江湖的想象。
早在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神怪武俠片《火燒紅蓮寺》就曾在浙江取景,掀起了中國武俠片的新浪潮,使得江南成為中國早期武俠電影中實現武林夢想的虛幻空間——江湖。2000年,在李安導演拍攝的《臥虎藏龍》中,江南再一次以“江湖”的想象回歸到觀眾的視野之中。安徽宏村這片江南水鄉,正是影片開篇李慕白閉關歸來一幕的取景地,一人一馬,小橋流水,李安導演在影片中賦予江南影像以歸隱、恬淡之感,展現出東方美學詩意化的意境美。
三、江南影像空間的藝術化表達
(一)藝術手法
在中國電影發展過程中,不乏出現以優秀文學作品作為劇本改編而成的影片。然而,在以影像方式呈現文學作品的同時,許多導演會選擇新的地域空間來代替原來文學作品的地域空間,并通過視聽上的藝術手法來表現原作中的精神內涵,實現對原有文學作品的重新解讀和創造性挖掘。
這一替代性的手法最具典型的便是霍建起導演在改編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時,將原作中高密東北鄉發生的故事轉移到了江南村落,為原作品的影像化表達尋找到了更為合適的表達方式。霍建起導演將江南的雨作為抒發命運哀傷的工具,將暖兒一生的坎坷和井河的愧意都融進了綿密的雨絲和濕潤的雨巷之中,并以離別之時贈送一把紅色的傘作為結局,賦予現實全新希望的同時傳達出一種暖暖的情意。
如此種種皆能表明:江南地域影像在無數導演的探索之中已經形成獨特的視聽表達方式,其氣候條件也能為東方電影的詩意化表達增添色彩;而江南地域空間的特征和意象,也為導演們更立體的表達出原有文學作品的中心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文化符號
在以江南為背景的電影影像中,“江南庭院”已經成為最常見的文化符號,其空間所構成的壓抑感與自由感相互制約,使得江南影像的呈現既有“庭院深深深幾許”的頹廢美,又有“人生長恨水長東”的理想消解之美。
在1948年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中,由破敗的墻壁和荒廢的庭院所構建的“廢園”中,寄托的是戰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內心的苦悶和蕭條;破落的庭院是戴禮言內心的外化,代表著他的消極與無望;墻外行人、墻里家人的狀態和有情與無情之間的糾結在散文詩般的敘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若果說,《小城之春》中壓抑的庭院帶給觀眾的多是理想的消解之感,那么張藝謀導演在《菊豆》中便更加注重對庭院開放空間的表現。電影中染坊空間局促狹隘,唯有那一方天井成為了封閉空間中唯一的突破點。壁壘森嚴的染坊象征著封建制度對人性的壓迫,而在鮮艷的染布上方,那一隅照有陽光灑落的天井成為這壓抑的時代中渲染生命的亮色。
江南電影在發展過程中始終秉持著剛柔兼濟、至柔至剛的美學意蘊,并將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貫穿始終,二者相輔相成,推動了我國電影的美學民族化。在全球化語境之下,江南影像更應該承擔起傳承民族美學的重任,將自然江南與人文江南融于一體,通過詩意化的表達方式,從多個角度表現出江南地域的“風景美”“人情美”與“人性美”,帶領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從而獲得真正的尊重與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