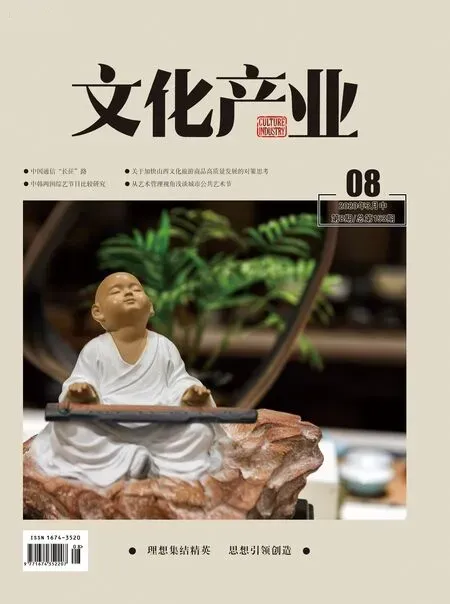西寧賢孝藝術傳承的文化生境研究
◎黃 成 李繼曉
(青海師范大學圖書館 青海 西寧 810003 )
我國民間傳統曲藝流傳悠久,形式種類紛繁眾多。“賢孝”作為一種流行于西北地區的民間說唱藝術,顧名思義就是弘表賢良、敷宣孝義,其內容大多以講唱忠臣孝子、敦勸良善為主,敘事性強,曲調流暢頗富韻律,地方特色濃郁。西寧賢孝曲目內容貼近生活且能反映普通大眾的所感所想,唱腔以本地方言為主,鋪事婉轉、聲調悠揚,聽來十分親切悅耳,廣受河湟當地各族群眾喜愛,是青海省獨有的一支古老而又重要的藝術曲種。
一、歷史淵源
西寧賢孝是土生土長的民間藝術,反映本區域的歷史與文化、表達著當地人民的理想和愿景,其頌賢道孝斥惡揚善的主題與歷來社會固有的道德主旨在本質上相符;其傳情寫意寓教于樂的形式最為各階層群眾所接受。
有研究認為,西寧賢孝最初發端于明朝中期,內容來源承襲自明清時代由經文演變來的一種曲藝品種——“寶卷”,諸如《四姐寶卷》《鸚哥寶卷》《趙氏寶卷》等分別移植變異為西寧賢孝中的《蘭玉蓮擔水》《白鸚哥吊孝》《趙五娘吃糠》;在西寧賢孝逐步形成和不斷發展過程中,還從其他姊妹曲種曲調中不斷汲取營養,拓寬并充實自身的藝術內涵。經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和積累嬗變,最終于18世紀形成如今曲詞悠長、動聽易懂,兼具現實風格與浪漫色彩的曲種形式,迄今已有數百年的歷史。西寧賢孝的發展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度達到高峰,曲目數量、表演形式以及伴奏配器都有所提升。然而西寧賢孝本身并沒有專業的演出團體,和大多數小曲種一樣,其曲目唱腔主要憑從業者口傳心授、師承相續。這些從業者也可以說是傳承者,基本都是盲瞽人員,以行乞糊口為目的,表演場地并不固定,走街串巷踽踽而行;演唱方式多為一或兩人拉弦碰鈴,席地蜷坐于市井田間或茶舍庭院隨口開唱,賣藝果腹而已,其中之苦令人惻憫。
西寧賢孝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其形成發展是河湟地區歷史文化進程的一個縮影,是當地人文藝術的珍貴組成元素,同時也為當地民俗學、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因而能夠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在2008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西寧賢孝》作為擴展項目被入選(類別:曲藝;項目序號:255;編號:V-19)。
二、發展現狀
西寧賢孝雖然是一種單曲體曲種,但曲調音律有其自身張力。盡管曲目大多沿用舊名,可內容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改變,如根據現實題材反映不同歷史階段現狀而新編的《歌唱英雄華子良》《法圖瑪回娘家》《脫貧致富奔小康》等曲目,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和存在價值。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成立的西寧市城東區文化館“地方曲藝研究社”、西寧市城中區文化宮“新苑曲藝社”,多年來致力于包括西寧賢孝在內的特色曲藝的發展與傳播,在表演內容與形式上也進行著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創新。面對傳統曲藝受眾呈現萎縮的困境,采取成立少兒曲藝隊的方式,招收有條件的孩子們進行培養,并且定期進入社區參與活動,使得這一曲藝形式較為普及。西寧市群眾藝術館為了進一步傳承保護西寧賢孝,積極響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校園,于2014年先后在所屬三縣(大通、湟中、湟源)建立了若干傳承基地,邀請當地老藝人進入學校實地教唱,從孩子入手,普及和培養傳承人。
此外,近年來西寧市群藝館在與海東市群藝館聯合建立民間曲藝培訓班的基礎上,相繼舉辦以賢孝為主的曲藝大賽,在山陜會館等場所進行展演、匯演,持續擴大西寧賢孝的生命力和影響力。西寧市城中區總寨鎮自發組成的曲藝隊伍穩定增加,民間曲藝大賽迄今已舉辦了多屆;西寧市城北區大堡子鎮組織曲藝演出隊,深入農村社區進行包括賢孝在內的曲藝專場巡演,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黨的政策,受到廣大群眾普遍歡迎。2019年5月,由青海省文化廳報送的西寧賢孝《老百姓笑了》登上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舞臺,參加第十二屆中國藝術節群星獎決賽,促進了青滬兩地文化交流,面向全國觀眾展示出青海省獨有的文化魅力。
隨著時代的發展,各級政府重視群眾藝術、關心民間藝人,組織“曲藝合作隊”,提倡內容創新,鼓勵編新唱新,西寧賢孝逐步向一門綜合藝術過渡,開始登上舞臺,進入藝術殿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寧賢孝的一些曲目曲調得到系統挖掘和整理,演唱形式上有了長足的進展,音樂表現力更為飽滿流暢。目前,由西寧市群藝館開展并對西寧賢孝進行數字化保護工作的“記憶工程”已順利實施。
三、文化生境
第一,豐富的藝術形態。西寧賢孝流行范圍包括以西寧市為中心的青海東部地區,一般統稱河湟地區。賢孝按照表演形式和流行地區的不同一般分為青海、甘肅兩大流派,前者以西寧為主,后者盛行于張掖和臨夏等地。在青海東部這片土壤上滋生化育的民間曲藝,帶有鮮明的自然地理生態特征。明清之際,本地各土生族群與遷徙族群漸趨融合,江淮、秦隴、中原地區各種曲藝唱腔流入,與當地社會生活狀態、審美心理相匯合,蘊育出諸多地方曲藝形式,如賢孝、道情、平弦、越弦、打攪兒等等。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西寧賢孝一步步成熟起來,逐漸形成自身特有的演唱形式及風格。
西寧賢孝的表現方式靈活多樣,其唱腔曲牌有大調、小調之分,還融入官弦、老弦、越牌調等舊時小曲的唱腔,風格協調統一,成為西寧周邊地區所獨有的音樂曲調。曲目按篇幅長短又可分“大傳”“小段”兩類,演唱時在段式、節奏等方面也有相應的藝術處理,如具有代表性的《子胥過江》《蘆花計》《丁郎找父》《白猿盜桃》《韓信算卦》等等,唱白間雜抑揚頓挫而饒有趣味。作為一種坐唱曲藝,西寧賢孝一般由一或二人坐唱,以男拉板胡、二胡,女彈三弦次第講唱為基本方式,敘事敷陳娓娓道來,極具韻味。整體形式除了前奏和過門,還包括前岔、主曲、后岔,結構比較完整。其間也有臨場即興發揮,烘托氛圍,具有濃厚鮮明的地方特點,一些高水平藝人善于根據具體內容情節和情感需要,很好地把握表演節奏,時而低緩沉郁,時而高亢激昂,藝術感染力十分強烈。
第二,復雜的社會生態環境。西寧賢孝是真正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的講唱曲藝。如前所述,西寧賢孝早在明代時期就開始在民間出現并流傳,從事這一曲藝的大多為民間眼疾盲瞽人員,表演大都表現出凄涼悲苦的狀態。
西寧賢孝不是一種家族相承的曲藝曲種,據說清朝時期就曾出現專門組織盲瞎藝人傳習賢孝的現象。民國以前,地方上存在一種類似慈善救濟性質的場所,稱作“養濟院”或“孤老院”,是殘障貧瘠者賴以棲身之地,在此可相互學藝以為“飯碗”。這種傳藝方式也有其嚴格的師承關系,類似門派般各個獨立不可逾界,譜系較為復雜。因此從小范圍來說,存在著不同的風格差異和藝術水準的高低。
當時人們把這些平日游走市井走街串戶的瞎眼殘疾藝人及其賣藝行為,稱為“瞎仙”“唱曲兒”,其表演一般就是在巷口街邊、坊間村戶隨地起唱,現場發揮,如泣如訴深沉婉轉;也常趕廟會或受紅白諸事相招,運用地方語匯并加以夸張的想象,進行大段整篇地表演。內容宣揚忠孝節義因果報應,故事浪漫曲折,人物形象生動,藝術氛圍濃厚且兼具勸善教化功能;其間不乏有較高藝術表現力、感染力的優秀作品和高手藝人出現。
第三,多民族文化的融匯。河湟地區在歷史上和現今都是個多民族雜居、多種文化融匯之地,在漫長歲月的發展過程中,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在同一塊土地上繁衍生息、勞作經營,相互借鑒、互通有無,逐漸形成共生共存的社會生活狀態。直至清代中期前后,本區域各族關系進入相對平穩的交融狀態,康乾盛世客觀上加速了河湟地區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多民族文化的興盛發展,形成了地域特色十分濃厚的民間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造就出彼此相通且又各具特點的地方民間曲藝品種。作為一種特有的曲種形式,西寧賢孝的流傳時間悠久,影響范圍和深度廣泛而又巨大,廣受各民族群眾喜愛。
西寧賢孝有著不同的流派,存在不同的風格與側重。其曲目包含有演義、勸喻、言情、傳奇、志怪等多個類型,總計已達百余部。這些內容涵蓋各民族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很多曲目能深刻反映各族人民的喜怒哀樂,表現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所追求的理想愿望,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四、對于保護傳承方式的思考
盡管由于社會變革與時代發展,有的傳統藝術種類凋零以至消失,但一路坎坷的西寧賢孝始終沒有被時代大潮所堙沒,西寧賢孝努力汲取營養,強化自身生命力。當前,各級相關部門著手推進保護振興民間藝術,在資金保障、人員培訓、市場開發等多方面開展扎實有效的措施,社會各界也在共同參與和努力扶持,處于轉型期的西寧賢孝應正視現實,與時俱進,立足自身特點,保障傳承發展。
針對今后具體工作,筆者有如下思考:第一,文化主管部門應著力做好從業者及現有曲目的普查摸底,及時完成建檔、回訪工作,并做好資料的交流與共享。第二,要切實立足當地中小學以及職業院校,推進建立包括賢孝在內的民俗民間藝術基地,定期邀請老藝人走進課堂、走上講臺,真正從孩子抓起,培養曲藝苗子,補充新鮮血液。第三,結合市場杠桿,增加現有團體演出場次,采取巡演匯演甚至比賽等形式,對其演出周期、演出范圍進行量化規定。第四,利用社會合力,及時發布演出資訊,加工音像制品,制作專業的文本和影音數據庫,編輯匯總歷年演出視頻資料。第五,建立微信公眾平臺以便普及賢孝,吸引更多愛好者參與其中,互通交流;利用快手、抖音以及諸多有一定影響力和覆蓋面的多媒體、自媒體方式,鼓勵團體及個人上傳演出演唱視頻,增加基本受眾,擴大影響范圍,使西寧賢孝的傳承發展邁上新臺階、展現新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