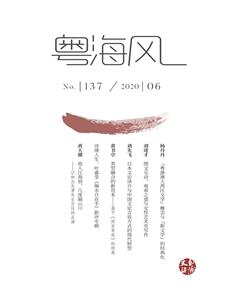“興、觀、群、怨”
戰玉冰
摘要:新冠疫情的暴發使暫時性的“居家隔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狀態和日常經驗,既包括某種“工作時間的中斷”,也形成了“空間移動的阻隔”,更涉及個體心理的焦慮與恐懼等問題。而疫情期間頗具廣泛性的“瘟疫題材”文學經典閱讀、長篇紀實作品《鐘南山:蒼生在上》的發表、紀錄片《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的播出,以及實體書店空間的線上轉型等個案,可以看到廣義上的文學(閱讀)在疫情期間填補“空余時間”,在信息、經驗與情感方面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撫慰,并在“空間阻隔”的特殊環境下建構新的人際聯絡與文化交流等方面,呈現出文學“興、觀、群、怨”的基本功用。
關鍵詞:新冠疫情 文學閱讀《鐘南山:蒼生在上》《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庚子故事集》
孔子在談及文學的功用時曾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在這段話中,孔子已經初步指出了文學的四項基本功用,即“興、觀、群、怨”。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發的特殊時代背景之下,暫時性的“居家隔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狀態和日常經驗,既包括某種“工作時間的中斷”,也形成了“空間移動的阻隔”,更涉及個體心理的焦慮與恐懼等問題。文學(閱讀)如何在疫情期間填補“空余時間”,在信息、經驗與情感方面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撫慰,并在“空間阻隔”的特殊環境下建構新的人際聯絡與文化交流,成了文學工作者(包括作家、編輯、出版人和線上/下書店工作人員等各環節)在特殊時期需要思考的問題和承擔的責任。本文試圖結合兩千多年前孔子對文學功能性的初步概括與當下全球疫情的背景,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反思和總結。
“興”:瘟疫題材文學經典的閱讀
2020年全球疫情的突然暴發使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上下班制度受到沖擊(無論是傳統的8小時工作制還是新興的“996”),被迫的暫時性“居家隔離”與跨地域流動受阻,加上手機互聯網時代信息交流方式的變革導致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以來司空見慣的公司/家庭、工作/休息、上班/下班的時間二分法在一定程度上被干擾,甚至被打破。這不僅是一個涉及生產方式與生活狀態的經濟學或社會學話題,更是在本質上影響尼爾·波茲曼的“鐘表時間”或者愛德華·湯普森的“時間紀律”的根本性時間觀念。
具體而言,時間的現代性體現在鐘表技術與工廠制的時間宰制之中。隨著現代技術(鐘表)與制度(工廠制)的出現,自然的時間變得越發“非自然化”,如美國傳播學者尼爾·波茲曼所言:“在制造分秒的時候,鐘表把時間從人類的活動中分離出來,并且使人們相信時間是可以以精確而可計量的單位獨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圖,也不是大自然的產物,而是人類運用自己創造出來的機械和自己對話的結果。”[2] 這就是齊美爾所說的“由于貨幣的精打細算,人的關系中便出現了確定相等和不相等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懷表的普遍使用導致了約會和商定時間的明確性”[3]。英國學者愛德華·湯普森在《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中則為我們更加詳細地描摹了鐘表發展、普及與工廠制不斷演進的歷史過程及其對人們的時間觀念與勞動習慣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靠使用所有這些方法——勞動分工、勞動的監管、罰款、鈴和時鐘、金錢刺激、說教和正規學校教育、壓制定期集市和娛樂,新的勞動習慣形成了,一種新的時間紀律得到了實行。”[4] 鐘表時間由此成為構建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和內在節奏,換句話說,現代世界實際上是被鐘表時間所組織起來的,并且可以精確至“分秒必爭”。嚴格按照精確的時間感知去生活和工作是現代社會得以維系和持續進行的基礎,這種精確的時間感同時具備高度強制性。
新冠疫情的暴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削弱了現代社會的時間強制性。社交媒體上常用的“停擺”一詞不僅指經濟生活秩序的停擺,也可用于描述人們在時間感受層面具備解釋上的有效性。這種“削弱”與“停擺”造成的結果之一在于,當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的刻板二分開始變得模糊,通勤時間被壓縮,暫時性的“居家隔離”便相應地產生了新的“空余時間”。但必須注意的是,“空余時間”的產生并非出于自然狀態下的原因,而是由臨時的全球突發性事件所致,因此,這里的“空余時間”不同于凡勃倫所說的“閑暇”——雖然兩者都具備“可支配的時間”這一基本特點,但仍存在兩點根本性差異:一是如前文所言,“空余時間”產生于特殊的歷史契機和社會狀態;二是面對這種“空余時間”時人們的心理狀態。全球新冠疫情帶來的“空余時間”因其突然性和外在空間的危險性,使得人們的心理感受并非是“閑暇感”,而更多是一種“空虛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伴隨著焦慮與恐慌等負面情緒。面對這種“時間空余”與“精神空虛”,瘟疫題材文學經典的閱讀便成為一種很好的精神食糧與心理安慰劑。
從阿爾貝·加繆的經典名作《鼠疫》到若澤·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長篇巨著《霍亂時期的愛情》到毛姆的《面紗》以及托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等,瘟疫題材文學經典的閱讀顯然成為很多讀者在疫情期間應對“時間空余”與“精神空虛”的主動選擇。據《北京日報》2020年4月16日的相關報道顯示:“開卷日前發布2020年第一季度圖書零售市場分析,2020年第一季度,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整體圖書零售市場同比下降15.93%,網店渠道同比上升了3.02%,實體店渠道同比下降了54.79%。”但在此圖書市場的環境之下,“瘟疫、病毒或者流行病學相關的圖書銷量出現明顯的增長,增長最為明顯的是文學類圖書,在2月份的開卷虛構類榜單中,《霍亂時期的愛情(2015 精裝版)》強勢返榜,排在第11名,成為返榜圖書中名次上升最多的圖書。《鼠疫》《新知文庫·逼近的瘟疫(第二版)》《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雖然未上榜,但銷量也創近兩年來的歷史新高”[5]。
一方面,瘟疫題材文學作品銷售量的增長和線上讀書推廣活動有關,比如頗具影響力的線上平臺“看理想”App在疫情期間推出的“八分”特別節目,由主持人梁文道帶領讀者細讀《鼠疫》《死于威尼斯》《失明癥漫記》等瘟疫題材經典文學作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八分”特別節目由以往的每周兩期臨時改為疫情期間每天一期,并且每期時長皆在一個小時左右,評論區的討論數量也遠多于節目平時的討論數量)。又如筆者所在的復旦大學在疫情之下也推出了“復旦通識”組織的“學人疫思”系列文章,“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6],并在“澎湃新聞”客戶端推送相關內容,其中郁喆雋教授對于瘟疫災難與科幻電影的哲學思考,顧春芳教授對于“文藝中的莎士比亞”的文本細讀,毛尖教授對于瘟疫、愛情與死亡的關系探討,以及王宏圖教授對于“瘟疫文學史”的仔細梳理皆在不同程度上引發人們對于瘟疫題材文學經典的關注,增強人們的閱讀興趣。
另一方面,瘟疫題材文學經典在疫情期間被閱讀和重讀也和這些文學經典本身的內容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這些文學經典具備穿越時空的不朽性因素與恒久性魅力,才讓處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讀者從這些文本中感受到慰藉、汲取到力量。以阿爾貝·加繆的《鼠疫》為例,小說虛構的發生在小城奧蘭的一場鼠疫和現實中的新冠疫情之間存在巨大差別,但書里的很多情節和細節依舊能夠召喚讀者的想象,具備打動當下讀者的力量。例如,描寫鼠疫引起群眾心理恐慌,“薄荷片可以防止感染”的謠言肆虐,引發薄荷片的搶購與脫銷:
“他還提到,瘟疫的景象有時哀婉動人,有時聳人聽聞,譬如說有個婦女,在一個百葉窗緊閉的冷清街區,突然把窗子打開,大叫兩聲,然后重又把窗子關上,房間里再次漆黑一片,但他還作了記載,指出薄荷片已在藥房銷售一空,因為許多人口含薄荷片,以防止感染。”[7]
又比如小說中鼠疫引發封城,作者描寫城里城外、親人愛人之間情感聯絡表達的不便、簡單以及格外的真誠:
“于是,電報就成為我們跟外界聯系的唯一方法。一些人因智慧、感情和肉體關系密切,這時只好從一封用大寫字母寫成的十個詞組成的電報中,去尋找過去水乳交融的種種跡象。但由于電報里能用的常用語確實已迅速用完,長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激情,就概述為定期相互發送的習慣用語,如:‘我好。想你。愛你。”[8]
第一段引文能夠讓身處新冠疫情中的讀者感同身受,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具備“紀實性”的特點;第二段引文則可以在特殊的艱難時期傳遞出一份愛與溫暖的力量。正是這些足以跨越時空的文字表達,為疫情中的讀者提供了一份面對“時間空余”與“精神空虛”的精神支持與心靈慰藉。
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作家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白雪烏鴉》在疫情期間也引發了廣泛的閱讀與討論。該小說描寫了100多年前俄國西伯利亞地區傳到哈爾濱的大鼠疫,面對疫情,清政府任命畢業于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伍連德前往哈爾濱指導防疫。小說中有兩章恰好叫作“封城”和“口罩”,相信對當下的讀者而言,這兩個標題一定會帶來不同的感受。此外,小說描述伍連德發明了雙層紗布中間夾一層棉花的口罩,當時稱之為“伍氏罩”;東北鼠疫期間出現哄抬物價的不良商人、慷慨捐資支持防疫的商人、被鼠疫嚇得精神異常的人,以及不懼感染給患者送水送飯的志愿者等各類人群,人們還迷信用生銹鐵釘煮水喝可以防治鼠疫等,此類人物、情節與細節也都緊緊扣住了當下人們的生活經驗和心理感受,因此,在出版11年后的新冠疫情背景之下,該小說再次獲得讀者的關注。
“觀”與“怨”:
從《鐘南山:蒼生在上》到《庚子故事集》
除了從經典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文學的另外一重功能在于見證和實錄。身為這一特殊時期的親歷者、見證者和參與者,作家有責任對這段歷史進行自己的觀察、記錄、書寫和反思,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首推熊育群的非虛構長篇《鐘南山:蒼生在上》(刊發于《收獲》長篇專號2020年春卷)。在這部非虛構作品中,熊育群一方面用簡約的筆墨勾勒出新冠肺炎的來勢洶洶及其造成的巨大影響:“三天后,1月26日0時起,武漢中心城區實行機動車禁行管理。喧鬧的大街轉眼間空無一人,一場真實的魔幻劇上演了。無形無影的病毒叫停了巨大世界喧嘩的生活。”[9] 另一方面,作者又將目光聚焦到此次疫情中臨危授命、已經84歲的鐘南山院士身上。在描繪鐘南山院士個人形象之時,熊育群采取了將鐘南山2003年對抗非典與2020年對抗新冠肺炎的經歷交叉書寫的方法,既能有效避免與書寫對象和事件過近造成的新聞化寫作傾向,又能在這組看似平行的對照性敘事中抵達更深入的反思和理解,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
“兩次疫情都在他年事已高的時候出現,都如此兇險。竟然都是他一次又一次出征。看到他84歲還如此操勞,關在家里盯著電視看,我感到羞愧、不安。這個事情本身就值得反思。
相比非典與新冠肺炎疫情,十七年之間,到底我們哪些方面進步了,哪些依然如故,重復著類似的劇情,發生著同樣的悲劇?如何保證若干年后,這樣的劇情不再上演?如果沒有鐘南山,我們是否能夠做得更好?或者相反!”[10]
與此同時,熊育群也沒有完全把鐘南山局限在兩次“抗疫”中,而是從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愛情經歷,以及從醫經歷等多個角度來塑造鐘南山立體而豐滿的形象,尤其是體育與醫學這兩個愛好,與鐘南山的家庭傳統密切相關,甚至成為鐘南山一家三代人生命中的某種“基因密碼”:
“鐘南山的家有兩大特點,一是運動器具多,有跑步機、單車、拉力器、單杠、啞鈴;二是書多。這充分體現了鐘南山的兩大愛好——醫學和體育。這兩者也成了他家庭最自豪之處:一是醫生世家,父親鐘世蕃是兒科專家。母親廖月琴是高級護理師。兒子鐘惟德子承父業,早已當上了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二是體育之家,妻子李少芬曾是籃球明星,擔任過中國籃球協會副主席,在1963年亞洲太平洋新興國家運動會上,作為中國女籃副隊長,她隨中國隊出征。女兒鐘惟月是優秀蝶泳運動員,1994年打破了短池游泳的世界紀錄,獲得過世界短池錦標賽100米蝶泳冠軍。兒子鐘惟德也是醫院籃球隊的“中流砥柱”。鐘南山本人則在首屆全運會上以54.4秒的成績打破400米欄的全國紀錄。1961年,他還獲得了北京市十項全能亞軍。鐘南山高齡之下抗擊疫情的毅力與體力都能從這里找到答案。他奔走各地之間,兩腳仍然生風。”
此外,作者也毫不回避地揭示了鐘南山曾經犯下的一些錯誤,正像作者自己所說:“我不造神,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樣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當普通人來寫。”[11] 比如文中寫鐘南山剛剛從內科調到急診室時,因為經驗不足而錯把一起胃嘔血誤診為肺咯血,受到領導批評,甚至勸他換到門診工作等。由此,在熊育群的筆下,鐘南山不僅僅是一名醫學專家與抗疫戰士,更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家庭、有事業、有著七情六欲并經歷過順境坎坷的立體的人的形象。
除了《鐘南山:蒼生在上》之外,紀錄片《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的推出也起到了廣義上的文學記錄功能。一方面,已經推出的兩季《人間世》原本就是一檔關注醫院、疾病與生命的人文醫學類紀錄片,在此基礎上制作“抗疫特別節目”可謂有著相當成熟的拍攝經驗和高度一致的節目調性;另一方面,作為廣義上的“紀實文學”,紀錄片有著比文字更便捷的傳播優勢,在社會上引起了更多關注和討論。和《鐘南山:蒼生在上》相類似,《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也不避諱表現醫生在馳援和急救過程中的快樂、焦慮、悲傷和無助。這組紀錄片讓廣大觀眾了解到,在武漢疫區和醫院中,哪怕是在最危險的ICU病房,除了病魔、痛苦與死亡之外,仍舊有陽光、溫暖、希望與愛的存在。此外,還有一些作家從私人視角出發,采取“日記體”的形式對疫情進行了觀察和記錄,引起很多網民的關注和爭議。
此外,除了從宏觀和典型的角度書寫“疫情”,文學更為擅長的可能還是把握“疫情”背景下個體生活中具體而微的細致感受及變化。比如,弋舟新近推出的短篇小說集《庚子故事集》(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9月)就是這方面很好的代表性作品。從《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再到最近的這本《庚子故事集》,弋舟的幾本近作中非常核心的一個概念就是“時間”。“時間”既構成了這幾本小說集的名字,也深深地嵌入每篇小說的深層肌理。在最新的《庚子故事集》中,一方面弋舟延續了對過往的懷念與對重逢的恐懼相伴相生的復雜情感,簡而言之,就是“近鄉情更怯”;另一方面其作品具備了更加勇于直面當下變化的力量。具體而言,《庚子故事集》中《人類的算法》《掩面時分》和《羊群過境》這3篇創作于疫情期間的小說所表達的主題不再是追溯過往,而“完全是‘現在進行時當中的情緒”。如果說《人類的算法》尚且保留了弋舟之前小說的某些特征——借用賀嘉鈺在《庚子故事集》“代后記”中的精準概括,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中年女人如何藏住她逸出的往事與心事”——那么《掩面時分》和《羊群過境》則完全是寫于當下且寫給當下的作品,無論是《掩面時分》中對口罩的反復提及,還是《羊群過境》里因為“疫情”與妻兒分隔且工作收入遭遇壓力的男主人公,都是頗具“當下感”的情節與細節。在書寫當下之外,弋舟還想努力突破當下,進而抵達一種更為普遍的時間感受,用他在《掩面時分》中的話來說,就是“世界當然還會重啟,到那時,勢必還會有人源源不斷地離我而去,形成新的閉環或者套娃”。一般而言,文學對于時代生活尤其是社會歷史事件的反映往往有一定的相對滯后性,即作家需要足夠長的時間去感受、沉淀,才能寫出有分量的作品,因此,《庚子故事集》這類文學作品目前還不是很多。但從弋舟的《庚子故事集》開始,我們可以期待未來中國作家能夠更為體貼且細膩地描摹出這一特殊時期的人們在感受與生活上的變與不變。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間,還出現了一些矯揉造作、流于口號、生搬硬套的“抗疫詩歌”。這些詩歌作者往往缺乏在疫情一線的生活體驗,也沒有做到對醫生與病人的感同身受,只是一味地主題先行,以淺薄的歌頌取代深厚的理解,以拙劣的陳詞濫調褻瀆了內心的共情與力量。這種現象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嚴肅對待。
面對新冠疫情這一如此巨大的歷史事件,如何深入理解、把握和書寫這段歷史是每一個當代作家都繞不過去的課題。我們必須承認,文學表達相對于新聞和歷史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作家有時需要跳出這段歷史,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歷史的地貌特征和深層脈動,同時作家也需要足夠的時間來對這些歷史事件進行理解和沉淀。比如畢淑敏的《花冠病毒》寫于“非典”結束后9年(2012年),阿來的《云中記》則是寫于汶川地震后11年(2019年),10年左右的消化與積累才保證了這兩部直面21世紀以來中國歷史大事件的文學作品具有了相當的深度和力度。在此意義上,我們離新冠疫情這一歷史事件的距離還是太近。從這一角度來看,寫于新冠疫情中的《鐘南山:蒼生在上》絕非是熊育群的臨時性/即時性寫作,早在17年前,作者在《羊城晚報》當編輯時就已經對鐘南山其人其事有一定的了解,甚至當年很多事件都是親自在場。文中關于新冠疫情的內容則是作者經過認真采訪和艱辛寫作才完成的:“一個多月,除了晚上五六個小時睡覺,一分一秒我都不敢耽擱。我一直與鐘南山的助理蘇越明先生保持著熱線聯系。他一直跟在鐘南山身邊,幾乎寸步不離,我一邊寫一邊問,他提供了很多細節,重要的事情也得到了鐘南山的印證和解答。呼研所的黃慶暉書記、廣醫醫院中醫科張志敏主任等都提供了幫助。”[12] 正是作者豐厚的經驗積累和長期對鐘南山本人的關注和思考,才使得《鐘南山:蒼生在上》并未流于平庸和簡單的“歌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學“觀”與“怨”的作用。
“群”:以書籍傳播與銷售的線上轉型為中心
此次新冠疫情期間,除文學經典的閱讀與文學新作的書寫之外,文學傳播方式的變化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現象。步入互聯網時代以來,傳統書店、網絡電商與電子書閱讀平臺在閱讀領域的“三分天下”已然成型,但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空間移動的阻隔”使線下實體書店遭受巨大沖擊。如前文中所引述的銷售數據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實體店渠道同比下降了 54.79%”,具體來看,“受本次新冠疫情影響,2月份全國多地實體書店關門停業,當月實體店指數出現直線下滑的情況。進入3月以來,隨著疫情逐漸好轉,各地實體書店也逐步恢復營業,但銷售情況依然明顯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位于一線城市的書店和規模較大的超大書城、大書城受疫情影響更為嚴重,負增長幅度均在60%以上,二線城市書店的降幅也接近60%”[13]。銷售格局的變化一方面為電子閱讀領域的規模開發與拓展提供了便利條件,正如劍橋大學湯普森教授的預言:“數字出版使得圖書具有了永垂不朽的潛力”[14],另一方面也為傳統書店的生存提出了新挑戰。疫情之前互聯網電商和網絡閱讀平臺的興起蠶食了傳統書店的經營邊界,單純以“圖書銷售”為主營業務的書店往往很難存活,常常要搭配咖啡、餐飲、文創、講座和讀書會等多元服務與線下活動,將實體書店打造為綜合性文化閱讀空間,才能勉強生存。而疫情導致線下顧客人流量驟減,人群聚集的潛在風險增高,對處于生存困境中的傳統書店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既可以說是對傳統書店的嚴厲打擊,也可以被視為逼迫傳統書店加速轉型的一針催化劑。
以上海市建投書局在疫情期間的線上轉型為例。在此次疫情之前,建投書局基本以線下店面活動、銷售和服務為主營業務,同時配合微信公眾號宣傳與部分產品的線上銷售。面對疫情,建投書局聯合上海市虹口區委宣傳部和廣西師范大學(上海)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了“彩虹書單·在線共讀計劃”。該活動以14天隔離期為1個閱讀周期,通過4期層層推進、緊接時事的主題,搭配20本精選電子書,邀請17位業內領讀人進行導讀,以每日在線閱讀打卡小程序的形式為載體,將傳統的線下讀書會搬到了線上。從活動結果來看,4期線上讀書計劃共有來自全國29個省級行政區的2047位讀者參加,打卡留言共計4552條,參與人數遠超以往的線下讀書會(建投書局線下讀書活動的承載量上限一般為80-100人/次)。在無法正常開店營業的情況下,建投書局反而收獲了遍及全國讀者的關注和熱烈的活動反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讓這家原本立足于上海北外灘的地方性書店打開了新的經營局面。借用廣西師范大學(上海)有限公司代表尹冬的說法:“疫情讓許多人習慣了線上消費,促進了圖書與閱讀行業的線上線下融合,形成新的產業閉環。”“新的產業閉環”是否已經形成現在或許還言之尚早,但從參加此次讀書計劃的讀者反饋來看,此類線上讀書活動在疫情期間起到了很好的激勵與陪伴作用。
作家孫甘露認為,書店作為一處線下實體空間,主要是提供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連接渠道,畢竟讀書并不完全是一種個體行為,也需要與他者的交流、討論和反饋來作為補充和刺激。當新冠疫情暫時性地切斷了這種線下鏈接方式之后,以建投書局為代表的書店經營者們將線下鏈接暫時性地轉移到線上,這既是面對突發事件的應急性經營策略調整,也可以視為特殊社會環境下書店線上線下經營模式融合的一次探索性嘗試。同樣重要的地方在于,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書店所起到的對于讀者的“群”的作用被一以貫之地保存了下來,只是“群”的具體形態有所調整。這種“群”的功能和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在新冠疫情這一巨大的突發型災難面前,對于安撫情感、凝聚力量、穩定人心有著重要且不可取代的積極作用。
除了書籍銷售與傳播方式的轉型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傳播方式上的變化是詩歌朗誦的重新流行。從央視“元宵節晚會”的詩朗誦《相信》《你的樣子》《中國阻擊戰》《因為有愛》,到諸多微信公眾號與喜馬拉雅等音頻平臺推出的詩歌朗誦、接力詩朗誦的相關音頻內容,這些詩歌從不同側面和角度贊美以鐘南山為代表的醫學專家、廣大醫護工作者與志愿者的職業堅守與奉獻精神,詩歌朗誦又一次以較為密集的姿態進入人們的視野。作為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流行的詩歌表現形式,詩歌朗誦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曾一度落寞并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這種趨勢背后隱藏著新時期以來文學閱讀逐漸演變為孤立化、原子化的個人行為的趨向。此次疫情期間詩歌朗誦的再度流行(雖然很可能只是短暫流行)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疫情時期人們對于集體/“群”的某種渴望和依賴。當然,這背后還涉及文學表現形式和文學主體特征建構/召喚之間的復雜關系,非本文所能涵蓋,此處就不再贅言了。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注釋:
[1] 本文已入選“全球化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與應對:從公眾健康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國博士后論壇(2020年11月7日舉行)征文,并在論壇上進行口頭匯報。
[2] [美] 尼爾·波茲曼著,章艷、吳燕莛譯:《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14頁。
[3] [德] 齊美爾:《大城市與精神生活》,收錄于G.齊美爾著,涯鴻、宇聲等譯:《橋與門——齊美爾隨筆集》,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262-263頁。
[4] [英] 愛德華·湯普森:《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收錄于愛德華·湯普森著,沈漢、王加豐譯:《共有的習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7頁。
[5] 路艷霞:《瘟疫題材文學類作品銷量增長》,《北京日報》,2020年4月16日。
[6] 摘引自“澎湃新聞”App中“學人疫思”專欄的文前引語。
[7] [法] 阿爾貝·加繆著,徐和瑾譯:《局外人·鼠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80頁。
[8] 同[7],第144頁。
[9] 熊育群:《鐘南山:蒼生在上》,《收獲》長篇專號2020年春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第15頁。
[10] 同上,第90頁。
[11] 同上,第90頁。
[12] 同上,第89頁。
[13] 路艷霞:《瘟疫題材文學類作品銷量增長》,《北京日報》,2020年4月16日。
[14] [英] 約翰·B.湯普森著,張志強等譯:《數字時代的圖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4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