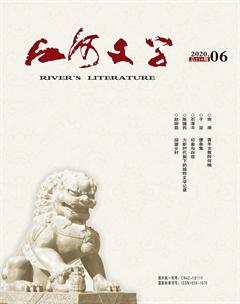鄉(xiāng)間過年
李雪非
小時(shí)候盼望過年,往往與美食有關(guān)。燙豆絲、燙粉、炒炒米、做麻糖、捏糖果、磨粉子、磨湯圓,揣糍粑、炸翻散……到了臘月,各家各戶就熱火朝天忙開了。
燙豆絲工序比較復(fù)雜,淘洗干凈的大米加入適量的黃豆或者綠豆,清水浸泡一晚,再用石磨磨成漿備用。燙豆絲火候很重要,必須用大鍋大灶。鍋邊放一只碗,倒一點(diǎn)菜油并加入適量的水備用,等鍋燒辣了,母親便用干絲瓜囊纏成的小帚子蘸點(diǎn)油水,擦擦鍋底,鍋里便開始冒煙,母親左手舀一瓢漿沿著鍋四周旋著倒下去,右手攥一只很大的蛤蜊殼,趁著火候,用蛤蜊殼光滑的背面迅速把漿刮勻,使之厚薄一致,蓋上鍋蓋,一會(huì)兒鍋里便滋滋作響,香味從鍋蓋縫里竄出來,揭開鍋蓋,一張又大又圓又薄的豆皮已成形了,母親用雙手輕輕一揭,起鍋,放在我端著的大托盤里,我再送到堂屋里早已擱好的大簸子里。豆皮兒涼了之后就卷起來,切成絲放到太陽(yáng)底下曬干,干豆絲可以存放很久。
然而還是剛燙好的豆絲最好吃,用油把兩面炕得黃亮亮的,再把事先炒好的大蒜或者腌菜放在里面包起來,咬一口,那個(gè)香啊簡(jiǎn)直沒法形容,吃一整張還不夠。每每燙豆絲,那香味往往飄得滿塆子都能聞見,不論誰(shuí)來家里串門,都少不了吃一頓。母親還包很多新鮮豆皮,讓我送給隔壁左右的人家。
燙粉的原料是大米,用水浸泡后磨成漿備用。往鍋里倒進(jìn)少量的水,沒過鍋底就行,將適量的米漿倒進(jìn)搪瓷平盤(農(nóng)村常見的圓形托盤),薄薄一層即可,平放在鍋里水上,蓋上鍋蓋大火蒸一會(huì)兒就好了,然后用一根竹針沿著搪瓷盤邊緣劃一圈,使粉皮兒與平盤脫離,就可將整張粉皮兒揭起來。為了圖快,往往是兩只搪瓷平盤交互使用,這只在鍋里蒸,另一只就倒好米漿備用。剛燙好的粉皮兒,又白又嫩,趁熱撒上白糖,卷起來咬一口,香香甜甜軟軟,極為爽口。將粉皮兒卷起來,切成絲,曬干,也可以像干豆絲那樣保存。干的豆絲和粉絲,一般是煮著吃。加點(diǎn)青菜臘肉之類,也是特色美味。
湯圓也是必不可少的美食,用石磨把泡好的糯米磨成漿,靜置半天,用干凈紗布包好瀝水,放在木盆里,再蓋兩層紗布,上面蒙上灶灰(草木灰),將水分吸干。也可將包好的湯圓漿吊起來,瀝干水分(俗稱吊漿湯圓)。這種半成品,可以直接搓湯圓吃新鮮的;也可以存入水缸用清水泡著,使之與空氣隔絕,常換水,隨時(shí)取用,常溫下可以保存一個(gè)月之久;還可以掰成碎塊,曬至完全干,密封在壇子里,置于陰涼處,儲(chǔ)存一年都沒問題。想吃的時(shí)候拿出來,給適量的水和一和,即可搓湯圓了。
我喜歡搓湯圓,將手洗干凈后,掰開一小塊,先握拳捏一下,使之緊致,再雙手對(duì)掌而搓,直到搓得溜溜圓。搓得好的湯圓大小一致,整整齊齊擺在盤子里,煞是好看。當(dāng)然,如果有條件,可以包進(jìn)芝麻、桂花餡。即使不加餡,用白水煮好后,盛一碗,濃稠的湯里,一只只湯圓小巧玲瓏,珍珠般雪白晶亮,拌上白糖或者紅糖,也饞得人直流口水。“心急吃不得熱湯圓。”母親和祖母總這么告誡,若不小心吞下熱湯圓會(huì)燙著心的。于是我們便小口品嘗,慢慢咀嚼,那糍糍糯糯的感覺、香香甜甜的滋味便格外綿長(zhǎng)。
父親則喜歡變花樣,將搓好的湯圓滾上芝麻,用油炸了蘸糖吃,色澤黃亮,外焦內(nèi)軟,更是香甜可口。還可以用油將湯圓炕到焦黃,再給少量糖水,大火燒干即盛起,又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湯圓也叫元宵,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美食,相傳起源于宋朝。過年尤其是元宵節(jié),一家人圍坐一起吃湯圓,象征團(tuán)團(tuán)圓圓、和和美美、幸福安康,因而備受人們喜愛。
揣糍粑是個(gè)力氣活,糯米須泡透,再用木甑蒸,剛蒸好的糯米熱氣騰騰,倒進(jìn)一只大木桶里,母親雙手握著忙錘(一種木棒狀工具),死勁揣,將糯米搗碎,漸漸地,糯米有了勁道,越揣越粘,粘在棒子上,拉都拉不動(dòng),糍粑才算揣好了。再用圓盤、方盤,固定成型,做成圓餅、方餅或者長(zhǎng)餅皆可,再晾干保存,像湯圓那樣泡在清水里能保存更久,要用的時(shí)候取出來,切成小塊,煮著吃,或用油炸蘸糖吃,口感都好。糍粑比湯圓有韌性,也更有嚼勁。
那時(shí)候物質(zhì)匱乏,過年吃的零食也是自己做。炒米、麻糖、糖果、粉子、翻散都是我家每年必備的。
白炒米不是我們最愛的,往往在壇子里存放得最久,一般是母親干活忙時(shí)充饑用,用開水沖泡,拌點(diǎn)白糖呼啦啦就吞下去了。外出勞作時(shí),也可以抓一把放在口袋里,餓了填填肚子。白炒米的制作工序比較繁瑣。先將糯米浸泡一兩天,瀝水,倒入木甑蒸熟,待涼,再掰散,鋪在大簸子里陰干,俗稱陰米。半干的糯米往往粘在一起,一小團(tuán)一小團(tuán)的,必須用手掰、搓,一遍又一遍,使之一粒粒完全散開。我最不耐煩干這個(gè)了,而這十分磨煉耐性的活兒,卻滋養(yǎng)了我安靜的性格。完全干后的陰米,似一粒粒半透明的小玉石粒兒,好看而有質(zhì)感。陰米可以存放很久,什么時(shí)候拿出來加工都行。隔年的陰米即陳陰米是治小兒腹瀉的偏方,放鍋里干炒到冒煙有糊味兒的時(shí)候,給半杯紅糖水,及沸騰,盛起,用小勺喂服,有的一次就能見效。
陰米是制作白炒米的原料,先將一大碗鹽(或干凈的細(xì)沙)放入大鍋里炒熱,撒一把陰米,用小帚子(多根細(xì)竹條纏成的工具)快速攪動(dòng),使受熱均勻。很快炒米就熟了,母親用一只沙撮快速撮起,搖晃幾下,鹽便篩下去了,炒米則倒進(jìn)備好的框子里。然后再撒一把陰米繼續(xù)炒。我常常目不轉(zhuǎn)睛地看著母親嫻熟的動(dòng)作,驚異于那些小小的半透明的陰米粒兒迅速膨脹變成雪白的炒米,覺得好神奇,我懵懂的心似乎受到某種震懾,覺出這尋常勞作里也藏著我所不知的奧秘。
人的智慧真是無窮無盡,將曬干的豆絲代替陰米,便可以炒出香香的干豆絲,它是虼蚤炒米的輔料。
虼蚤炒米,也叫硬蚤炒米,是真正的美味,我們最愛吃。以秋谷米為主料,用熱水加適量的明礬、鹽浸泡半天,瀝水,再倒進(jìn)鍋里小火焙干,盛起,像炒白炒米那樣,借助鹽一鍋一鍋炒熟。此道工序完成后,將鍋洗凈擦干,再將炒米倒入鍋里,拌以香油和事先炒熟的黃豆、干豆絲、芝麻,微火翻炒和勻,香味便只往鼻孔里鉆,忍不住抓一把塞進(jìn)嘴里,香酥可口,舌頭都醉了。母親做的虼蚤炒米格外好吃,我和妹妹的同學(xué)都這么說,每次回家我們都要多帶些去,室友們百吃不厭。
麻糖、糖果的主原料是白炒米,將適量的麥芽糖放進(jìn)鍋里,加少量水,小火熬化熬干水分,再倒入適量的炒米,輔以芝麻,用鍋鏟充分翻炒和勻,盛起,趁熱捏成一只只蘋果大小的球兒,即為糖果。若做麻糖,就將其盛進(jìn)一只大的方形器具里,趁熱壓緊壓實(shí),稍涼凝固,再用刀切成薄片狀,即是麻糖。剛做好的麻糖和糖果整整齊齊碼在簸子里,色澤金黃,香味誘人,嘗一口,甜甜酥酥,連咀嚼的聲音都好聽。盡管麻糖和糖果味道一模一樣,可我卻不大愿意吃糖果,又大又圓的,很不好啃,且容易掉渣兒,吃相狼狽,不像麻糖,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嘗,讓人不由得滋生幸福的感覺。
麻糖和糖果的主原料也可以是炸米泡,就是用米泡機(jī)(我們稱之為“沖”,讀第四聲)爆出來的那種,和現(xiàn)在的爆米花同類。
磨粉子,原料是糯米,泡半天,放鍋里小火焙干,至嫩黃色,熟而不老,盛起來,加入適量的熟芝麻,用石磨磨得細(xì)細(xì)的,可以干吃,也可以用開水沖泡著吃,加白糖,香香甜甜,跟現(xiàn)在的芝麻糊相似。
翻散有咸和甜兩種口味,我們都愛吃咸的,和面粉時(shí)便加入鹽、姜、蔥、生芝麻,給點(diǎn)明礬或者堿,炸的翻散會(huì)更酥松。面粉和好后,要揉,死勁兒揉,揉出勁道來。然后揪一大塊,用長(zhǎng)的搟面杖搟成一張大的薄餅,搟得好,可鋪滿整張桌子。再用刀畫格子般將其分解成眾多長(zhǎng)方形的小片片,每片中間豎向劃一小口,將一頭塞進(jìn)小口翻過去,翻散大概是因此而得名的吧。翻好的翻散,一批批放進(jìn)油鍋里炸至金黃,撈起來,瀝油,放涼,品嘗一口,香香酥酥脆脆的,真是無上美味啊!
本來翻散可以提前做,但為了開油鍋之便,我家往往要拖到臘月二十八九,和肉圓子、酥魚一起炸。開油鍋,一年也就這么一次,家里裝上100瓦的燈泡,徹夜燈火通明,誘人的香味四處彌漫,嗅覺味覺乃至所有感官都興奮無比。我和妹妹最喜歡這樣的時(shí)候,父母不會(huì)催著我們?nèi)ニX,而是由著我們想玩到多晚都行。平時(shí)從沒有放開肚子吃那么多好東西,現(xiàn)在卻可以坐在灶門口吃個(gè)夠。最有誘惑力的是剛炸好的肉圓子和酥魚,我們吃得滿嘴油膩、肚子撐不下了還舍不得停下。
與過去相比,現(xiàn)在過年美食要豐富得多,然而我仍覺得童年鄉(xiāng)村的年才是真正的年。那忙碌歡愉的氛圍,那親手做美食的點(diǎn)滴樂趣,那從臘月開始就飄滿整個(gè)鄉(xiāng)村的濃濃年味,都讓我難以忘懷。
每年春節(jié),母親都要把曬干的豆絲、湯圓粉子、糍粑、炒米、糖果、麻糖、翻散之類分別用塑料袋封裝好,等城里的大伯和姑伯兩家回來,給他們帶走。在鄉(xiāng)下,只有過年才做的這些美食,是農(nóng)忙時(shí)節(jié)充饑的主食,是伢們半年乃至一年的零食,也是待客時(shí)擺在茶幾上的小點(diǎn)心,還是走親訪友的禮品。拜年的時(shí)候,一塊圓圓的糍粑餅,一袋雪白的湯圓粉、一籃香香的糖果、麻糖,用干凈的紅布包著、蓋著,那份真摯而純樸的情義,也艷艷地、暖暖地紅著,是鄉(xiāng)間過年最美的風(fēng)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