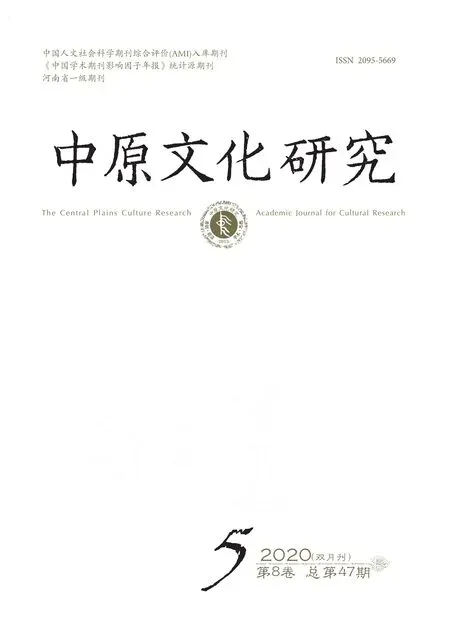影游融合、想象力消費與美學的變革*
——論媒介融合視域下的互動劇美學
陳旭光 張明浩
“媒介融合”是新世紀以來媒介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近年來中外學界研究的熱點①。關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外學者多有討論。飛速發展、日新月異的媒介融合與我們的藝術、文化、傳播和日常生活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不僅催生了種種新媒介的創生,改變著我們的視聽感知與想象、思維的方式,實際上更是發生一場“媒介文化革命”。“媒介文化把傳播和文化凝聚成一個動力學過程,將每一個人裹挾其中。于是,媒介文化變成為我們當代日常生活的儀式和景觀。”[1]2無論是技術層面的革新還是文化層面的變遷,“媒介融合”都是時代的產物、歷史的產物,是當下物質與精神消費的產物,也都是當下文化、媒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
一、媒介融合時代的游戲新美學與“影游融合”新態勢
游戲是“媒介融合”時代的一種重要媒介,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與滲透力。一方面,游戲似乎成為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了體驗性消費、享受式消費時代人們生活的重要內容。正如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在《在線游戲互動性理論》中說,“游戲在公眾中的普及程度已經達到了與業務應用程序或Web 瀏覽器一樣的高度”[2]3,游戲已經在潛移默化中成為新媒介時代人們尤其是青少年、網生代的“生活必需品”。游戲美學在潛移默化中滲透人們的生活,并影響著人們的消費需求與價值理念等,使人們喜愛具有游戲美學特征的作品。具體而言,游戲所帶來的美學革新與文化變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游戲具有互動性、交互性等互動美學特質。桑德拉·高登西認為,“交互性就是觀眾置身于作品之中的一種手段,通過這種交互,觀眾與作品所要傳達之真實進行協商”[3],“游戲為人們提供了在作品中使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以及玩家與玩家的互動性的機會”[2]39。正是基于此種變化與特質,弗里德里提出“互動”是在線游戲的關鍵甚至是核心屬性與美學特征。他認為在線游戲的互動性基于三種維度,并提出了互動性的三維概念,“即玩家與計算機、玩家與玩家、以及玩家與游戲的互動性”[2]40。
其二,游戲具有體驗性、沉浸性。游戲可以提供給受眾“身體介入”的體驗感與探索感,游戲“為玩家提供了空間、工具、規則、即時的反饋與明確的目標,并且還為之找到一個‘能力與挑戰的平衡’[4]33點,在使玩家介入的過程中不斷吸引玩家的再介入,終使玩家“沉浸”其中[5]。正如馬修·維斯與亨利·詹金斯所言:“游戲設計者或許無法控制我們的情感,盡管如此,他們提供了一種強烈情感體驗所需要的資源。”[6]
其三,游戲具有“身份匿名性”與“自我掌控性”,傳達出一種團隊協作與個人奮斗“合謀”的品格。游戲提供給玩家相對公平的、可以自我決控的環境,玩家可以在虛擬中依靠個人努力或策略以及團隊合作進行“打怪升級”滿足自身對“身份”的需求,完成一次“象征性權力表達”[7]。
此外,游戲還具有規則性、重啟性、虛擬想象性、部落劃分性、腦神經刺激性等多種美學特質,這種美學特質與文化特征也必然會潛移默化地滲透、影響當下人們的審美選擇與文化觀念,進而促使受眾喜好具有體驗感、刺激感、探索感、身心介入感的影視作品。另一方面,游戲還提供給當下諸多媒介進行媒介融合探索的機會,大多媒介都可以與游戲進行聯姻,進而借助游戲的受眾群體與美學特質革新美學形態,吸引青少年受眾主體。
“影游融合”是“媒介融合”時代下影視作品緊抓游戲媒介進行探索、實踐、創新的產物,是“媒介融合”的一種重要類型與方式。廣義而言,具有游戲化風格與游戲特質的作品都可以稱為“影游融合”類作品。狹義而言,影游融合類作品包括直接改變自游戲的作品、模擬游戲或以游戲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作品以及“互動影視”[8]。
如亨利·詹金斯所言,“影游融合”同樣也帶來了一場文化變遷、美學變遷。在美學層面,影游融合類影視劇具有“身體介入影像”的美學特質,具有參與性、交互性、體驗性等特質,可以使受眾在鑒賞過程中產生“心流”,滿足受眾體驗式消費、互動式消費的需求[5]。在文化層面,影游融合類影視劇是青少年進行“象征性權力表達”“部落劃分”與“身份彰顯”的“符號”,代表了游戲文化、二次元文化等青年亞文化,自身即具有青年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文化功能等[9]。從受眾接受的維度看,影游融合類作品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對姚斯、伊塞爾等的讀者反映—批評或接受美學理論構成了某種僭越和挑戰。影游融合類作品具有“‘虛幻的真實感’和視聽沖擊力的‘數字美學’和虛擬美學特征,這強烈地改變了作為第二主體即接受主體的觀眾的接受態度、接受方式和接受觀念,也使得藝術理論中關于藝術傳播和接受的理論面臨著劇烈的挑戰”[10]。
具體而言,影游融合類作品具有直接互動性與參與性,不是一種主體靜觀式、夢幻化的觀影狀態,影游融合的觀眾(玩家)觀看影片的過程更像是游戲過程,更為強調受眾的主體性、能動性、參與性、游戲性。另外,影游融合類作品中受眾的“期待視野”更多基于受眾的游戲體驗、游戲感受與以往所玩的游戲作品,是一種立足于個體文化、鑒賞水平之上的體驗式、互動式、刺激式的“期待”。與接受美學強調受眾主體性不同,影游融合類作品強調的是受眾參與性、受眾與作者直接對話的交流性,是一種客觀基礎上的主客統一,建構的是一種平等溝通的平臺。這與接受美學理論的相對主義、主觀化的批評觀是不一樣的。由此,以近年來發展迅速的互動劇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析其帶來的美學變革與想象力消費趨向,具有重要意義。
二、媒介融合視域下作為“影游融合”新形態的互動劇
互動劇是“影游融合”的一個重要子類型,最早或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具有“互動體驗”效果的影視作品。如1967年“偽互動電影”《一個男人與他的房子》中的“互動”只是一種“偽”的形勢,因為其結局或者說其游戲結果不具有可操縱性。該片通過讓觀眾投票來選擇主人公命運,但是無論觀眾如何選擇,其結果或者說結局只有一種固定式結局。廣義而言,互動電影游戲也屬于“互動影視”的范疇,互動電影游戲對于互動電影、互動劇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早期的光碟游戲《太空地帶》(1983),21世紀的《幻象殺手》(2005)、《暴雨》(2010)、《超凡雙生》(2013)、《夜班》(2017)、《直到黎明》(2015)、《底特律:成為人類》(2018)等,這些作品為互動影視的發展夯實了基礎。
2018年互動電影《黑鏡:潘達斯奈基》借助《黑鏡》的品牌優勢,在世界范圍內取得了成功,并促使業內產生了各種互動話題、互動作品以及相關平臺的互動戰略,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互動影視的發展。2018年威尼斯電影節上的VR互動電影如《星球》《精靈鼠伙伴》《咕嚕米的眼睛》等作品,也都昭示著互動影視作品的發展潛力與創新能力。在2019年之前,國內互動劇似乎一直沒有得到顯著發展,2008年香港林氏兄弟制作了《電車男追女記》,2017年騰訊打造了國內首部武俠互動劇《忘憂鎮》,這些作品總體影響力與熱度并不大,并沒有形成清晰的類型生產模式。2019年可謂國內互動劇發展的井噴期與加速期,上半年以愛奇藝、騰訊、優酷等為代表的平臺競相給“互動劇”加注籌碼并不斷探索其新形式,相繼產出了《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騰訊,2019年1月,互動微劇)、《明星大偵探頭號嫌疑人》(芒果平臺,2019年1月,互動微劇)、《隱形守護者》(騰訊,2019年3月,互動游戲)、《他的微笑》(愛奇藝,2019年6月,互動劇)、《廣場救世主》(B 站,2019年7月,互動短視頻)、《因邁思樂園》(騰訊,2019年9月,互動劇)等具有互動性質的短劇或微視頻。它們或在影視中融游戲,或在游戲中融影視,在內容和形式等方面對傳統游戲、影視都造成了解構。
近年來,國內互動劇在急速發展的同時也取得了較好的產業成績,證明了其所具有的較大商業價值與廣闊的市場前景。以《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為例,該劇以復線式的總體布局與多樣式結局吸引著受眾復玩,在增加受眾觀劇黏性的同時甚至間接提高了網劇《古董局中局》的收視率。芒果TV 的《明星大偵探之頭號嫌疑人》更是收獲了豆瓣8.6 的高分,話題微博累積閱讀量高達3.5 億,討論數達133.9 萬,進而達到了間接反哺劇集、擴大劇集影響的作用。再以愛奇藝自制互動劇《他的微笑》來講,該劇制片人李蒞櫻在北京大學“新媒體大講堂”上表示,作品達到了目標受眾與實際受眾的高度吻合,《他的微笑》人物畫像中女性用戶占比為75.7%,年齡多為19—30 歲,一線、新一線城市的用戶最多,與最初目標受眾“90—00 后”的年紀分布高度吻合②。對于一個處于探索期的新樣式來說,能夠達到實際受眾與目標受眾基本吻合的成績是難能可貴的。一方面,作為一種較新的形式、較新的概念,互動劇的群眾基數并不是很大,知道的人也比較少,在創造初期便精準人物畫像、精準受眾群體是十分難得的。另一方面,從人物畫像進行深入分析,從青少年、女性受眾、19—30 歲等關鍵詞中,我們便可以明顯看到此類作品在未來廣闊的發展前景:因為當下的受眾主體多為“90—00 后”的女性群體,未來也將遲早是95 后、00 后等青少年的天下,而此類作品又恰恰符合他們的口味,其未來廣闊的發展前景與發展空間不言而喻。
從疫情期間影視行業新變化與受眾游戲化審美向好的現實背景來看,互動劇在“后疫情時代”將會有新的發展空間。“疫情期間受眾游戲化的審美趨好新變、游戲產業的高速發展以及影游融合的發展趨勢為它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現實基礎和心理需求及消費空間;IP 品牌,網影兩棲等產業運作優勢構成其發展的產業、工業基礎;‘身體介入影像’將是它的總體美學特征,也將是其吸引受眾的重要因素。”[11]由上,正如愛奇藝CEO 龔宇所言,“‘互動’是內容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12],無論是從互動劇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與百花齊放的現實布局來看,還是從互動劇良好的產業成績、較大的市場號召力來看,抑或是從疫情之后受眾游戲化審美、消費需求以及游戲產業高歌猛進的趨勢來看,互動劇都將會成為今后影視生態版圖中至關重要、吸引受眾的一種重量級作品類型,先聲奪人之后必將持續發展。互動劇的崛起也必然會給影視行業帶來美學革新。互動劇的自身屬性、敘事特征、文本建構及藝術鑒賞等多個方面體現出游戲特征,表現出不同于以往常規影視劇的獨特性。
三、互聯網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文本之變
(一)從“只讀”式文本到“可寫”式文本
互動劇帶來最為顯著的美學革新是使影視作品的“文本”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將以往僅具有“只讀”性質的文本(這里的“只讀”是指以往的文本往往都是作者設置好的,受眾只能在實際意義上被動接受與閱讀的文本),變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可寫的文本”、開放的文本。關于“可寫的文本”,羅蘭·巴特在《S/Z》中曾有過闡釋[13]56-57,認為作品應該讓讀者參與進來,強調讀者主體性的觀念相同,也與接受美學認為文本是一個多層面的開放式的圖式結構,是一個未定性結構與啟示性結構,需要讀者參與進來進行“填空”的理念相同,互動劇的“可寫性”也是強調讀者的中心位置,強調讓讀者參與進來。
互動劇的“參與”“可寫”是一種真正實踐層面“創造式”的可寫與參與、互動,可以使受眾直接“創造”敘事,改變敘事,按照自己的主觀意愿進行敘事,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給受眾創造新文本的機會。而以往就算是極具開放性與可寫性的文學文本或影視文本,例如具有數據庫敘事特質的影視作品《無問西東》《快跑羅拉》《羅曼蒂克消亡史》等,或具有瑪姬·斯伯林所提出的超故事敘事特質的影視作品等,它們的可寫性、互動性依然被可控制在創造者提前預設好的情節數據庫與故事建構之中,提供給人們的“可寫”空間也僅僅是依靠提供給受眾“留白”或“召喚結構”來完成的,是不能改變文本原貌的一種“間接式的可寫”,是一種“心理”層面的參與,不能直接改變文本的結構與敘事。
互動劇在總體布局上由作者提供了人物背景、敘事節奏與環境設置,交互者(受眾)利用可能的步驟進行即興創作,便是每個受眾所生產的“不同的敘事”,而互動劇也于此為大眾提供了一個“可寫”“可再生”“可創造”的開放性空間。例如,《他的微笑》中共設置了21 個互動情節點,不同的互動情節點對應兩個或三個選項,而不同的選擇便會觸發不同的劇情走向,進而引發不同的結局。無疑,此種總體布局在創作初期便已調整、設置好。盡管如此,每個人依然會走出不同的路線,進而產生不同的敘事。正如蘇珊娜·托斯卡總結的,角色扮演游戲可以進行敘事生產,不同的游戲玩家可以把完全一致的故事情節通過驚人的、截然不同的方式表演/講述出來③。
受眾作為游戲玩家,可以選擇、操縱“千鳥”這一游戲角色,進而將總體布局較為相似的故事框架以不同的方式講述出來。以第一個互動情節“千鳥的叫醒服務”為例,受眾不同的選擇就意味著至此要開啟不同的敘事。例如,選擇“雨林”后主人公便開始了與肖遲、肖也的故事,進而衍生出主人公陷入兩者情感糾葛中難以選擇的情節設置,而選擇另外的則對應“啟太”或“艾斯博”故事。再比如,劇集中的小選擇也會影響到劇集的發展。當受眾在“胃疼危機”中選擇“不求助啟太”時,該劇便走到了最后“被迫辭職”,進而結束了故事發展;而當在“胃疼危機”中選擇“求助啟太”后,故事便又有了新的進程,如啟太的關心、啟太生病等。決定該劇結尾或影響該劇敘事進程的就是受眾(玩家),正是因為他們不同的選擇才創作出了不同的敘事,而作品本身也變為了一個“可寫的文本”,具有了“再創造性”與“可寫性”。
例如,《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中三種不同結局,即冰釋前嫌、踽踽獨行與眾叛親離,分別對應了三種敘事方式與敘事邏輯,也代表著受眾在“寫作”后的結果。全劇分為“金剛杵/蛇洞、責備/安慰、徒弟先走/自己先走、解釋/隱瞞、救徒弟/保護馬燈”幾個重要的關鍵選擇點。以“救徒弟/護馬燈”節點為例,當我們選擇“救徒弟”,那么主人公則要在12 塊玉中選擇兩個正確的;而選擇護馬燈的話,則僅僅需要選擇一個正確的玉石。由此,不同的選擇生產了不同的敘事,該劇也于此提供給了受眾幾次直接“寫作”的機會,并為受眾帶來了不同的結局。受眾探索、決定的過程,便是生產、創造的敘事過程。誠然,互動劇的可寫性或者說互動劇所提供給受眾的可寫空間,也是由作者精心設計的,其可寫性也是一種“限度內的可寫”,是一種代碼、編程后的“可寫”,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給了人們以“寫作”與再創造的自由。
(二)從“只讀”文本到“游戲文本”
互動劇的文本不僅是可寫式、開放式、可創造式的文本,而且還是游戲文本。互動劇有著游戲的規則、可計量的結果等多重屬性,仿佛是一個大型游戲文本。其一,互動劇有一套嚴格的游戲規則,即受眾要代入角色身上,完成角色的任務。其二,互動劇有多樣且可計量的結果,互動劇有多條故事線,每一條故事線都對應不同的結果,并且受眾可以根據自身的選擇計量出該劇的結果走向。其三,互動劇不同的結果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價值,該劇每一條結果都對應人物不同的境遇,每一個選擇的背后都有著明確的價值與意義。其四,互動劇具有可協商性質的結果,可協商性是指受眾在玩的過程中(鑒賞的過程中)可以根據進度內容自主選擇退回“上一個關卡(選擇)”或重新開始游戲(從第一個選擇重新開始),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重啟游戲或者后退選擇。
值得強調的是,互動劇游戲文本的屬性不僅體現在其作品構造上,還體現在其文本本身所表現出來的互動性、趣味性等游戲特質,互動劇總體表現出一種類似于養成類游戲或角色扮演類游戲的基調。
首先,互動劇具有“交互”性或說是“互動性”。互動劇將觀眾置身于作品之中,因為觀眾需要根據劇情或根據自身喜好代替主人公進行選擇,進而促使著主人公進行下一步行動,而觀眾的這種選擇行為便是一種“協商”行為。由此,觀眾與作品之間、觀眾與作者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關系。當然,普通影視劇也具有互動性,在普通影視劇中受眾可以通過人物境遇、環境狀況產生認同心理,進而進行精神層面、情感層面的互動。但互動劇不但具有情感互動,還直接可以使受眾參與作品之中,可以使受眾選擇,是一種更為直接的互動。例如,《他的微笑》不僅可以滿足女性戀愛的需求,還可以滿足女性養成類游戲消費的需求。這種互動性,也是影片游戲性的一種展現。
其次,互動劇具有“游戲”的趣味性。眾所周知,游戲有著極高的趣味性,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游戲具有探索性,不同的選擇對應著不同的結果,不同的工具也對應著不同的效果。再如,游戲可以使人產生成就感,玩家通過贏得比賽的形式從中可以獲得快感等。相應地,互動劇也具有如上的特性。一方面,互動劇不同的關卡可以使玩家面臨不同選擇,不同選擇背后便是不同的結果,受眾會在每一次選擇的背后都獲得一種新奇感,并且期待下一次選擇,循環以往,受眾也可從中感受到趣味與樂趣。另一方面,互動劇每一個故事線都有一個相對較好的結果,或者說該劇中受眾不管選擇哪一條進程線索,都可以獲得成功、贏得比賽。例如,《他的微笑》中女主角大部分的選擇都會產生較好的結果,即與男主角產生情感關系或收獲愛情,受眾便可以從中獲得認同感與成就感,進而感受到趣味性。
最后,互動劇在整體上還表現出一種養成類游戲、角色扮演類游戲的總體美學基調。例如,《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中我們需要扮演好師傅的角色,在《他的微笑》中則要以養成明星為目的,扮演好經紀人的角色。以《他的微笑》為例,一方面,該劇總體設置為一個女生與多個男生的故事,作為男明星的經紀人或負責日常生活的工作人員,女生有著讓男生出道、監管男生們練習、幫助男生們調節心情等責任,這種類似于養成類小游戲,即玩家在游戲中需要把自己的“寵物”養大,并讓他上學、生活等。另一方面,該劇也具有角色扮演類游戲的特質,女主角面對不同的男生會擔任不同的角色,受眾在整個故事進程中也可以產生一種認同,進而代入女主角的角色身份之中,代替她進行選擇,扮演好她的角色。
綜上所述,互動劇使“只讀”的文本變為了“可寫”的文本、游戲文本,在真正意義上使受眾成為了敘事的生產者與作品的創造者,讓單向的較為固定的“文本—閱讀—文本后生產”模式,變為了雙向的“文本—互動—文本內生產”的模式。
四、互聯網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接受主體之變
接受主體(受眾)在藝術生產環節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與作用。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認為接受者是消費者,他們影響著生產并促進著生產,進而表達出接受主體的重要性。接受美學則認為,作品只有在接受者鑒賞之后才可以稱之為作品,否則便是未定性文本,如伊瑟爾將文學作品劃分為未定性的文本和讀者的具體化兩部分。只有讀者的期待視野與文本相融合,即進行“視野融合”后,才能談上接受和理解。互聯網新媒介時代下影視作品接受主體的組成與布局發生了變化:“當下電影觀眾即作為大眾文化之主體的‘大眾’有四種頗為重要的樣態,一是網民或游戲玩家觀眾,二是青少年觀眾,三是女性觀眾,四是市民觀眾。”[14]而在媒介融合、影游融合背景下,游戲玩家與電影觀眾互相重合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不妨說,現在的影視受眾主體——青少年網生代受眾,其實很大部分也是游戲玩家。
互動劇接受主體維度帶給影視行業的美學革新使其改變了接受主體的“身份”,使接受主體從“鑒賞者”變為了“游戲玩家”。一般而言,影視作品與受眾之間是“被鑒賞者”與“鑒賞者”,或者說被鑒賞的客體與鑒賞主體之間的關系。但受眾在鑒賞過程中不一定能很好地發揮主體性,并不一定能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參與,只能通過作品預設的場景、人物關系和情節發展而間接參與,達成情感共鳴。但在互動劇里,受眾的身份發生變化,他們由鑒賞者變為了直接的游戲玩家,具有了決定權、選擇權等游戲性質的權力,他們不僅成為了主人公,更成為了掌握游戲進程的玩家。
受眾的游戲玩家屬性體現在他們需要完成身份扮演上。馬林·C.貝茨認為:“大型角色扮演類游戲玩家身上呈現出的不僅僅是一種身份,還有演繹和更改這種身份的方法。身份是依照軟件本身、網頁以及其他玩家提供的原則建立起來的。”[15]例如,當受眾觀看《他的微笑》時,該劇就已經如游戲一般給玩家(受眾)設置好了身份,即一個需要養成明星的經紀人身份,受眾在觀影過程中需要“扮演”好這一身份,他們需要代入情景、劇情之中進行思考,進而代替主人公進行選擇。在這種過程中,受眾已不僅是一個旁觀者,他更像是一個玩家甚至是一個在游戲之中不斷進行選擇的玩家,他需要參與進游戲之中,扮演成游戲女主角,并根據“網頁設置”(游戲規則)演繹好這一身份,完成這一身份所需要執行的任務。
受眾的游戲玩家屬性體現在他具有的可操縱性權力上。“(人機)交互的信息性觀念特征就是‘控制’。”[16]168游戲之所以吸引諸多玩家流連忘返,是因為它可以使玩家成為“上帝”,它可以給玩家以自主選擇、自主操控的權力,玩家可以在這個虛擬世界里“后悔”,可以選擇重新啟動或可以選擇“不滿意”的關卡重新闖關,他們對于游戲的結果、游戲關卡的進程、游戲的總體進程都具有可操作性。《他的微笑》中的受眾便具有此種可操縱性權力,一方面,受眾(玩家)可以在該劇中自主選擇后退或前進,對于之前的選擇如果不滿意可以重新選擇、重新進行,進而具有了控制整個劇情發展的權力,也自然具有了可控結果的權力。另一方面,受眾可控制劇中的人物或直接決定人物的選擇,這種設置下就會使受眾明顯感受到如上帝般的“支配”權力和快感,因為他們具有掌握別人人生、感情與意識形態的權力。
《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中的受眾也具有可操縱性權力,該劇具有“游戲引擎”式的內部設置,將游戲裝置中的“手柄”“鍵盤”等進行影像化呈現。在該劇接近結尾處有一段主人公躲避日本軍官的打斗式游戲環節設置,需要不斷點擊屏幕以達到躲避射擊的目的,需要不斷用手進行左右滑動,在打倒軍官前也需要“上滑”再“右滑”等操作。在此,如果我們以手機進行操作的話,手機便變成游戲可操縱的“手柄”,不停滑動也仿佛是游戲中“出大招”的步驟,整個過程就將受眾變成了游戲玩家,因為受眾需要不停滑動、不停思考、不停對抗、不停游戲,才可以取得成功。
綜上所述,馬修·維斯與亨利·詹金斯曾將游戲的情感傳達方式形容為“自我中心”[6]:我們全然沉浸于情節之中,我們的選擇決定了事件的結果。其實,互動劇也為受眾提供了一個“自我中心”的空間,提供給受眾進行角色扮演、自我操縱性權力的機會,使受眾從被動“解碼者”變為了主動“編碼者”④、從鑒賞者變為了游戲玩家。
五、想象力新美學與想象力消費
互動劇不僅為影視行業帶來了文本之變與接受主體身份之變的美學革新,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受眾想象(或接受、消費)的方式,表現出異于以往的,更多趨于游戲性、以及影游融合新媒介特性的“想象力新美學”[8],滿足了受眾奇觀化審美消費、體驗式審美消費、想象力消費等需求。
相對于以往影視作品依靠“未定性空白”或“不確定性”來促使受眾想象或依靠奇觀呈現來滿足受眾想象,互動劇更具有不確定性與刺激性,更需要玩家充分調度自己的想象與思維。以往作品并沒有給受眾可選擇的機會,受眾也僅僅跟著劇情走,或根據劇情想象之后的情節發展。但是互動劇卻提供給了受眾“可選擇”的機會,并且每個選擇節點背后預示著不同的情節與關卡。這種設置類似于游戲的“地圖選擇”,不同的地圖預示著不同的關卡,玩家每次選擇都會在腦子里根據地圖名稱想象出地圖場景。互動劇也是如此,當受眾遇到每個選擇時,在腦海中會快速想象出選擇之后的場景與變化,受眾會根據選擇關卡的字面意思想象背后的故事,進而通過自己的想象,選擇出最想看到的或者說想象中最期待看到的故事。此時,受眾的想象力便會被充分調動起來,進而期待、想象自己選擇后的故事。換言之,受眾每次選擇的過程也是受眾充分想象的過程。
互動劇的想象力美學與想象力消費所帶來的是一種“創造想象—滿足想象”的過程。互動劇的巧妙之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可以通過關卡或選擇節點促使受眾進行想象,進而“創造想象”。因為無論是何種選擇都會在選擇前充分想象選擇后的結果,比如在《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中,我們選擇救徒弟或護馬燈時,會充分考慮到選擇后的結果,并會想象出選擇后所遇到的問題。再如在《他的微笑》中,我們從一開始選擇進不同的房間時便開始了想象,想象每個房間里是哪位練習生,女主角和他們會經歷什么。另一方面,它可以及時地、最大程度地滿足受眾的想象,可以給受眾即時反饋,受眾選擇之后對應不同的場景、情節、關卡。例如,《他的微笑》中選擇進入“雨林”房間后,主人公便開始了與肖遲、肖也的故事,進而衍生出主人公陷入兩者的情感糾葛之中,難以選擇的情節設置等,選擇另外的則對應著“啟太”或“艾斯博”的故事。而當受眾選擇后,其實無論是什么結果,都會沖擊受眾的審美期待。如果是和受眾預期相同的結果與場景,受眾則于此滿足了想象力的需求,如果是和受眾預設完全不同的結果,受眾的期待便于此被沖擊,進而促使受眾繼續想嘗試、想游戲,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想象與作者想象的相近性。
于此,受眾在互動劇預設的框架中按照一種游戲式的、期待的心理不斷地進行“選擇—想象—選擇”,“再次選擇—再次嘗試—再次證明”……在此過程中,受眾的心理被充分調動起來,互動劇也在心理層面促使受眾“沉浸”或促使受眾產生了“心流”。正如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所言:“在目標明確、能夠得到即時反饋,并且挑戰與能力相當的情況下,人的注意力會開始凝聚,逐漸進入心無旁騖的狀態。”[4]36不僅如此,在受眾“想象—選擇—再想象—再選擇”的過程中,那些沒有被受眾選擇到的“按鈕”,也在吸引著受眾再次、重新進行選擇,它如游戲一般提供給了玩家“復玩”“重啟”的機會。而復玩、重啟也更需要受眾的想象力,因為從一開始便預示著不同的選擇有不同的結果,受眾在走完自己最初想象道路后,必然會更想看看另一條道路的風景,這種想法與觀念也必然會調動受眾的想象力與興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大部分選擇都是單向而不可重新選擇的。
就社會價值與受眾現實情感宣泄、精神需求層面而言,互動劇的想象力美學其實還體現在它提供給人們一種類似于“人生可以重啟”式的想象與愿景,滿足了人們重啟人生、重新選擇、多樣嘗試的想象力消費的需求:當受眾在代入角色進行身份扮演時,可以對錯誤的選擇進行及時修正,甚至可以在一開始改變源頭的選擇。例如,在《他的微笑》中,如果感覺與一開始選擇的練習生不合或者不喜歡他,可以跳回到最初的“叫醒服務”這一互動情節點重新選擇。此外,互動劇的想象力美學還體現在互動劇本身的奇觀場景呈現與奇特情節營造上。例如,在《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中,觀眾可以跟隨主人公進入奇妙詭異的古墓中,并且不斷通過“操縱”主人公而闖過重重關卡。以“九宮迷陣”為例,這一場景不僅需要觀眾根據指示選擇出相應的磚塊,而且也充盈著一種中國道家文化中的陰陽八卦感,這種具有奇幻色彩的情節設置與場景布局,無疑會滿足受眾對古墓包括古墓布局、古墓機關的奇幻化想象,進而滿足受眾奇觀化、夢幻式想象力消費的需求。
此外,互動劇的“想象力消費”還體現在它可以協助受眾尤其是青少年玩家,進行“象征性權力表達”與進行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功能上。一定程度上,互動劇是一種受眾所需的“消費符號”,它代表的是青少年群體、網生代受眾,或者說它在產生之初的目標受眾或理想受眾就是青少年群體,它天然與網生代、青少年受眾同體共生。青少年參與消費互動劇的過程也是自覺進行“身份劃分”與“部落歸屬”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傳達、生產著獨屬于青少年群體的青年文化。例如,《他的微笑》傳達出了一種粉絲文化、造星文化。由此,互動劇所帶來的想象力新美學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互動劇中受眾的每次選擇都是一次發揮想象力、調動想象力的過程;二是互動劇提供給受眾一個“創造想象—滿足想象”的“即刻反饋”式的想象機制與想象空間;三是互動劇可選擇、可重復、可重啟的功能,尊重觀眾的自主性和主體性,能滿足受眾現實宣泄與情感需求;四是互動劇的奇觀化場景與想象式情節,能滿足受眾夢幻化、奇觀化藝術審美式想象力消費需求;五是互動劇是青少年的符號化代表,在想象力消費中進行意識形態再生產。
結 語
就互動劇的發展而言,作為一種新媒介藝術的新形態,互動劇的發展面臨諸多需要探討的產業問題、藝術問題和美學問題。鑒于此,業界、學界還應積極探索思考互動劇的“影—游融合”屬性,如何確定最佳的劇集時長,如何在關鍵節點設置精準的互動情節,如何賦予不同的敘事線索和結局不同意義,以及如何進行多元樣式、類像發展的探索,互聯網語境下如何利用大數據分析受眾群體的需求和互動特點。盡管當下人們對互動影視的看法褒貶不一,但作為時代、媒介融合發展和受眾想象力消費需求的產物,必然會繼續可持續發展。互聯網新媒介時代下,游戲文化、互聯網文化已然逐漸成為當下的“主導型”文化。基于此,我們需要更加注重“想象力消費”類作品,尤其是“影游融合”類作品如互動作品的創作。因為這些作品符合當下青年網生代觀眾的審美喜好,拓展了影游融合類影視劇的發展,而且不僅具有體驗、交互、沉浸等游戲特性,也具有著價值與情感表達、視聽呈現、感官滿足等美學價值。當然,以《他的微笑》《古董局中局之佛頭起源》等為代表的作品只是國內互動劇的開始,但昭示了一種新媒介藝術、新影游融合藝術形態的未來發展前景。其所帶給受眾的體驗、享受、互動,將打破受眾的審美定向思維,也將不斷解放受眾的想象力,促進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的發展。
注釋
①筆者通過知網檢索關鍵詞“媒介融合”,2015—2019年學界關于研究探討“媒介融合”的文章每年維持在1200篇以 上。2015年1271 篇,2016年1315 篇,2017年1349篇,2018年1403 篇,2019年1279 篇。檢索時間,2020年7月22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kw&skey=%E5%AA%92%E4%BB%8B%E8%9E%8D%E5%90%88&code=。②參見李蒞櫻:《互動影視初登場:百花待放的互動視頻》。具體內容來自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2019年11月12日舉辦的“新媒體大講堂”中,制片人李蒞櫻的講座內容整理。③參見蘇珊娜·托斯卡:《遠非私人笑話:角色扮演游戲中的跨媒介戲仿》,《世界電影》2011年第1 期。④參見斯圖爾特·霍爾:《編碼/解碼》,載于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