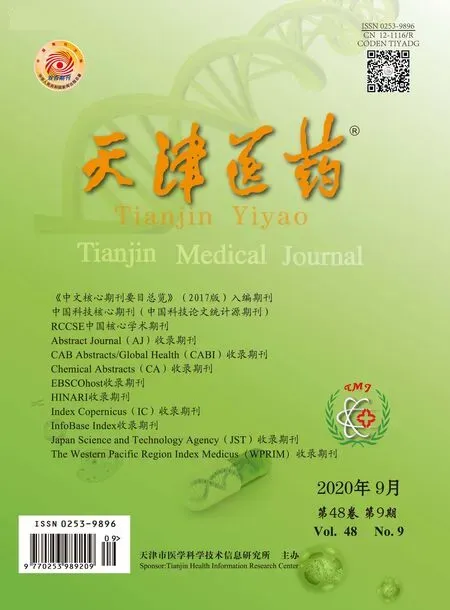2型固有淋巴細胞在變應性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劉力,鄒映雪
人體免疫系統分為固有免疫系統和適應性免疫系統兩大類。固有免疫系統是防御入侵病原體或抗原的第一道防線,應答迅速、無特異性;隨后激活的適應性免疫系統對特定抗原進行徹底清除[1]。固有淋巴細胞(innate lymphoid cells,ILCs)作為固有免疫的重要效應細胞群,主要有3個標志性特征:不經歷受體基因重排和克隆選擇、缺乏髓系細胞和樹突狀細胞表型標志物以及其形態屬淋巴譜系[2]。ILCs多為組織駐留淋巴細胞,主要分布于扁桃體、支氣管-肺、腸道、皮膚等黏膜屏障部位,參與黏膜免疫形成、淋巴細胞發育、組織損傷修復及上皮屏障保護,在抗感染、調控炎癥、維持免疫穩態中起著重要作用。根據ILCs 的表型和分泌的細胞因子,分1、2、3 型固有淋巴細胞(ILC1s、ILC2s、ILC3s)3 個亞群,功能上近似對應 Th 細胞的 Th1、Th2 和 Th17[3]。ILC1s 包括自然殺傷細胞(NK)和ILC1 細胞,依賴轉錄因子T-bet(T-box transcription factor)并產生大量干擾素(IFN)-γ;ILC2s為一個單獨的細胞亞群,能產生Th2型細胞因子和其他效應分子,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4、IL-5、IL-9、IL-13 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從而驅動2 型免疫反應的發生;ILC3s 活化時產生細胞因子 IL-17 和 IL-22[4]。與識別特定抗原的T細胞不同,ILC2s對非特異性的細胞因子有反應,IL-33、IL-25、胸腺間質淋巴生成素(thymicstromal lymphopoietin,TSLP)和花生酸類物質是刺激ILC2s 活化與增殖的主要激活因子,活化后的 ILC2s 可產生大量的 IL-5 和 IL-13(IL-5 和 IL-13又被稱為前過敏細胞因子),導致氣道炎癥形成和氣道高反應性,這提示人類ILC2參與Th2免疫反應[5]。此外,在變應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哮喘、特應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嗜酸性粒細胞性食管炎(eosinophilic esophagitis,EoE)等多種變應性疾病患者的病變組織中均有ILC2 數量增加[6-7]。因ILC2s的持續激活會破壞機體內穩態,故體內亦存在其抑制因子,如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s)、兒茶酚胺類神經遞質、IL-27、IL-10、脂氧素 A4 和 IFN等。固有免疫可能比適應性免疫更早、更強地參與過敏反應,本文就ILC2在變應性疾病中的研究熱點予以綜述。
1 AR
AR 患者暴露于過敏原環境后,迅速出現打噴嚏、流鼻涕、鼻癢、黏膜充血等典型癥狀,這是IgE介導的經典Ⅰ型超敏反應。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固有免疫反應也是AR的發病機制。
有研究發現,AR 患者鼻上皮受到過敏原刺激后,上皮內的前炎性細胞因子增加,屋塵螨(HDM)過敏患者的鼻腔灌洗液中可檢測到IL-25、IL-33 和TSLP[8-9]。此外,AR 患者鼻黏膜中 IL-33 和 TSLP 的mRNA呈高水平表達[10-11]。IL-33不僅可以引起IgE介導的組胺釋放,也可通過非IgE途徑激活ILC2,從而刺激肥大細胞釋放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12]。有研究顯示,樺樹、花粉過敏患者的嗜堿性粒細胞受到過敏原刺激后,會出現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BMC)釋放的 IL-25 水平上調,此外 PBMCs 中 CD4+T 細胞能夠表達高水平的IL-25R mRNA,IL-25 可增強ILC2 介導的肥大細胞脫顆粒[13]。上述研究表明,IL-25、IL-33和ILC2通路可能是導致AR發病的重要環節。周明輝等[14]研究顯示變應性真菌性鼻竇炎患者鼻上皮細胞中ILC2 數量增加,并受上皮細胞衍生的IL-25正向調控,兩者與鼻黏膜內的IL-5、IL-13 表達水平呈正相關。
關于AR 患者外周血中ILC2 數量是否增加,目前研究結論并不一致。Bartemes 等[15]研究發現AR患者外周血中ILC2數量并未增加,但哮喘患者外周血中ILC2數量增加。另有研究顯示,HDM過敏患者外周血中ILC2數量增加,且其數量變化與癥狀嚴重程度呈正相關[16]。Fan 等[17]研究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HDM 過敏的AR 患者外周血中ILC2 數量增加,然而艾蒿過敏的AR 患者ILC2 數量卻無明顯變化,提示HDM 對ILC2 的刺激強于艾蒿等植物過敏原,HDM過敏的免疫反應機制可能與植物過敏原不同。對于植物過敏原導致AR的研究發現,在草花粉季節,草花粉過敏患者外周血中的ILC2和ILC3數量增加,而ILC1數量則無明顯變化;此外,在非草花粉季節,舌下過敏原免疫治療對ILC1、ILC2 和ILC3 數量無顯著影響[18]。
Kato 等[19]建立了經鼻腔接觸豚草花粉致敏的AR小鼠模型,研究發現在小鼠模型的鼻黏膜中存在ILC2;研究人員進一步建立敲除T 細胞和B 細胞重組激活基因2(Rag2-/-)小鼠模型研究其固有免疫功能,結果顯示,盡管Rag2-/-小鼠過敏早期出現嗜酸性粒細胞浸潤減少,但仍高于磷酸鹽緩沖液對照組,推測ILC2 可能在過敏早期嗜酸性粒細胞浸潤中起促進作用,但在后期則不發揮作用。
2 哮喘
哮喘的主要特點是氣道炎癥、氣道高反應性和可逆性氣流受阻。既往研究普遍認為哮喘主要與Th2 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相關,然而新近研究表明哮喘不僅是Th2 細胞主導的免疫反應,也是一組異質性疾病[20]。當哮喘由Th2細胞介導時,Th2細胞通過產生IL-4、IL-5 和IL-13 等細胞因子在哮喘中起關鍵作用。IL-4刺激B細胞的增殖與分化,促進IgE的合成和肥大細胞的生成;而IL-5能夠促進嗜酸性粒細胞的增殖與分化;IL-13則通過刺激上皮細胞和氣道平滑肌細胞引起氣道高反應性,這是哮喘的重要標志之一。哮喘也與其暴露的因素有關,如二手煙、汽車尾氣、臭氧、病毒感染、運動、精神壓力和肥胖等,這類情況通常與中性粒細胞相關氣道炎癥和非Th2細胞依賴的固有免疫有關[21-22]。
ILC2s與哮喘氣道炎癥密切相關。有研究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哮喘模型小鼠支氣管上皮組織和外周血中ILC2數量明顯增加,肺泡灌洗液和外周血中IL-4、IL-5、IL-13 水平亦顯著升高,提示ILC2是哮喘發病機制中重要的免疫細胞[23]。Préfontaine等[24]研究顯示,當病原微生物、過敏原等環境因素刺激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時,上皮細胞和氣道平滑肌細胞會產生大量TSLP 和IL-33,其水平與疾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TSLP和IL-33可直接刺激ILC2分泌Th2 型細胞因子。有研究顯示,哮喘患者外周血中ILC2數量及ILC2相關的Th2型細胞因子、轉錄因子和信號轉導分子表達水平均明顯增高,另在哮喘患者肺泡灌洗液中亦可檢測到ILC2[25-27]。此外,符合氣道嗜酸性粒細胞炎癥的嚴重哮喘患者在口服糖皮質激素治療后,痰液中仍可檢測到大量IL-5、IL-13和ILC2s,提示ILC2在氣道炎癥中發揮持續作用,全身用糖皮質激素不能完全控制氣道炎癥[28]。但也有研究發現,哮喘患者接受過敏原刺激24 h后,痰液中IL-5、IL-13水平和ILC2數量顯著增高,而血液中ILC2 數量減少,提示 ILC2 僅在氣道內增加[29]。綜上,哮喘患者外周血中ILC2 數量是否增加,目前研究結論尚不一致,但多項研究證實支氣管上皮和肺泡內ILC2數量明顯增加。
ILC2 參與氣道高反應性。氣道上皮受到刺激或損傷后可直接分泌一系列炎性因子,其中IL-33可以迅速激活ILC2,發生Th2 型免疫反應。ILC2 可通過分泌IL-5調節B細胞分泌IgE,同時促進嗜酸性粒細胞生長、分化和聚集,分泌IL-13直接誘發氣道高反應性[30]。哮喘患者肺內ILC2 數量增加是Th2細胞因子的重要來源,在無CD4+淋巴細胞的情況下即可驅動嗜酸性粒細胞的炎癥反應[31]。
ILC2參與氣道上皮損傷和重塑。Sugita 等[32]研究哮喘患者支氣管上皮細胞中ILC2 對上皮緊密連接和屏障功能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當ILC2 與人支氣管上皮細胞共同培養時,ILC2 可通過釋放IL-13破壞上皮屏障功能,表現為上皮間電阻抗降低和上皮通透性增加。Saglani 等[33]研究發現,IL-33 是肺內ILC2的強效激活因子,ILC2數量增加和持續激活是導致兒童糖皮質激素耐藥型哮喘氣道重塑的重要因素,因此ILC2 和IL-33 可能成為防治氣道重塑的靶點。
除促炎作用外,ILC2 也具有部分炎癥調節作用。有研究發現,存在一類ILC2亞群在轉化生長因子(TGF)-β1 協同作用下,可產生 IL-10,被稱為ILC210[34]。小鼠模型中嗜酸性粒細胞炎癥的減弱與ILC210的合成增加有關,提示ILC210具有炎癥調節作用[35]。
3 AD
AD 是一種慢性瘙癢性炎癥性皮膚病,其在14歲以下兒童中的發病率約為20%,在成人中的發病率約為3%。AD發病機制復雜,可能是基因易感性、皮膚屏障缺陷、免疫紊亂、微生物感染、環境因素等多因素共同作用致病,常伴發哮喘、AR 多種變應性疾病,免疫學特征屬于Th2 型免疫反應[36]。Salimi等[37]研究顯示,成人AD患者皮損區域內ILC2s數量明顯多于健康對照組,但外周血中ILC2數量與健康對照組無明顯差異。Kim 等[38]研究顯示,TSLP、IL-33可刺激表皮內ILC2產生Th2型細胞因子,皮損區IL-5、IL-13 水平顯著升高,導致皮膚炎癥反應。另有研究發現小鼠皮膚ILC2中存在IL-4受體,IL-4可誘導ILC2增殖并發生AD樣皮損改變[39]。ILC2與皮膚屏障功能障礙具有交互作用,上皮組織受損后釋放 IL-33、TSLP、IL-25 等細胞因子,刺激 ILC2 產生Th2 型細胞因子,導致皮膚炎癥反應;同時,由于上皮屏障缺陷,E 鈣黏蛋白水平降低導致ILC2 的負調控機制減弱,加速局部炎癥[40]。
4 食物過敏
近十年來,食物過敏的發病率呈顯著增長趨勢,特別是在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發病率可達10%,兒童食物過敏較成人更常見。常見的食物過敏原包括花生、堅果、魚類、貝類、雞蛋、牛奶、小麥等,食物過敏癥狀多表現在胃腸道、皮膚、呼吸道,其中呼吸道癥狀較少見,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41]。食物過敏的發病機制是腸道免疫耐受異常,導致IgE和非IgE介導的Th2型免疫反應,目前對食物過敏發病機制的研究主要采用鼠模型。
Noval等[42]研究發現,IL-4受體功能突變的小鼠表現為食物過敏和ILC2 數量增多,ILC2 受IL-33 刺激可分泌更多的IL-4,IL-4 能抑制調節性T 淋巴細胞(Treg)生成并促進食物過敏。另有研究顯示,小鼠口服抗原佐劑可通過刺激腸上皮細胞表達IL-33,增加ILC2s數量,ILC2s分泌Th2型細胞因子的同時,IL-33 直接作用于肥大細胞并增強IgE 介導的超敏反應,引起食物過敏[43]。以上研究提示IL-4、IL-33是控制食物過敏的可能治療靶點。肥大細胞被認為是過敏反應的重要效應細胞之一,占腸黏膜細胞的2%左右,被IgE 致敏的肥大細胞可以誘導ILC2 增殖,而ILC2 又可以反過來增強肥大細胞釋放組胺、蛋白酶、白三烯等炎性介質,因此阻斷IgE信號傳導和肥大細胞活化可能同時抑制IgE 和非IgE 介導的Th2型免疫反應[44]。
5 EoE
EoE 是一種食管慢性復發性炎癥,患病率呈增長趨勢,其組織學特點是嗜酸性粒細胞浸潤食管壁,成人患者表現為吞咽困難、食管狹窄以及反流樣癥狀;兒童患者主要表現為拒食、嘔吐和營養不良[45]。有研究顯示,EoE 的發病機制是由食管上皮細胞受到刺激后產生的TSLP 和炎癥細胞產生的IL-5、IL-13驅動,IL-5可導致食管嗜酸性粒細胞增多,而IL-13 誘導血管生成和組織重構[46]。Doherty 等[7]研究發現,EoE患者活動期食管活檢顯示ILC2數量增多,緩解期ILC2數量減少,而ILC2是產生IL-5和IL-13的重要固有淋巴細胞。也有研究利用免疫組化聯合流式細胞學檢測作為替代EoE 病理檢查的方法,結果顯示,在對照組和活動期EoE 受試者上皮中均存在固有淋巴細胞,但活動期EoE 受試者上皮內ILC2數量更多[47]。有研究發現,IL-9是調節ILC2生物活性的關鍵細胞因子,活動期EoE 患者ILC2 中IL-9R表達上調,ILC2 主要被IL-33 激活從而導致食管的持續炎癥[48]。EoE 由多種環境因素誘發,如食物或空氣中的過敏原,經常與其他變應性疾病伴隨存在,目前缺乏診斷的金標準,ILC2能否成為具有診斷意義的組織學證據尚需要更多的研究。
6 展望
ILCs 作為固有免疫的重要部分,分布于組織黏膜下層參與免疫反應的始動環節,其中ILC2s 參與多種變應性疾病的發生發展,但是具體機制尚未完全明確,特別是在非IgE 介導的過敏反應中的作用值得關注。隨著對ILC2s細胞的研究和認識的不斷加深,有希望為探索變應性疾病發病機制提供更好的證據,發現新的評估指標和治療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