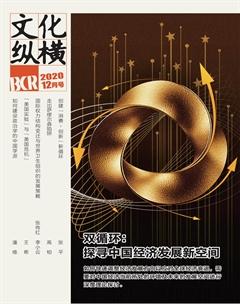被架空的援助領(lǐng)導(dǎo)者*
徐加 徐秀麗
[文章導(dǎo)讀]
作為本刊的特色欄目,“新發(fā)展知識(shí)”自2019年12月創(chuàng)立以來(lái),推出了一系列總結(jié)各種發(fā)展援助實(shí)踐的深度文章,倡導(dǎo)突破西方霸權(quán)主導(dǎo)的發(fā)展知識(shí)體系,探索受援國(guó)的自主發(fā)展之路和更為平等的全球發(fā)展模式,獲得了學(xué)界的廣泛好評(píng)。
本期徐加、徐秀麗的文章介紹了20世紀(jì)90年代日本單純依靠援助數(shù)量支撐起“援助大國(guó)”地位,但由于缺乏對(duì)本國(guó)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的獨(dú)創(chuàng)性研究總結(jié)和國(guó)際影響力打造,最終被傳統(tǒng)援助體系架空的教訓(xùn)。借此,文章指出了中國(guó)當(dāng)前對(duì)外援助合作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即如何在援助知識(shí)體系中構(gòu)建中國(guó)話語(yǔ)。彼時(shí)日本從國(guó)際地位、援助理念到來(lái)自西方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抵制壓力,都與今天中國(guó)的境況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何構(gòu)建出一種既貢獻(xiàn)自身發(fā)展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又真正具備國(guó)際引領(lǐng)地位和話語(yǔ)權(quán)的對(duì)外援助制度,是日本的前車之鑒留給我們思考的重要問(wèn)題。
在整個(gè)20世紀(jì)90年代,日本一直以對(duì)外援助為重要的國(guó)際戰(zhàn)略,并且成為世界第一大援助國(guó)。但是,日本很快削減了援助金額,于2001年被美國(guó)再次超過(guò),并且一直沒有恢復(fù)90年代在國(guó)際援助上的突出地位。[1]《蒙特雷共識(shí)》《發(fā)展籌資問(wèn)題多哈宣言》《亞的斯亞貝巴行動(dòng)議程》等文件多次重申,發(fā)達(dá)捐助國(guó)的官方發(fā)展援助(ODA)應(yīng)占到國(guó)民總收入的0.7%,但日本近年來(lái)的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0.2%左右。
日本20世紀(jì)90年代在全球政治經(jīng)濟(jì)和國(guó)際援助中所處的位置,與我國(guó)今日所面臨的環(huán)境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日本在援助項(xiàng)目中強(qiáng)調(diào)基于受援國(guó)的請(qǐng)求、援助雙方的伙伴關(guān)系、受援國(guó)本身的自助努力等,都與我國(guó)今天的援助理念相似,體現(xiàn)出作為一個(gè)后發(fā)國(guó)家有別于西方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獨(dú)特援助哲學(xué)。并且,日本在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jī)之前經(jīng)濟(jì)一直快速增長(zhǎng),曾位列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與一些西方國(guó)家形成了一定的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同我國(guó)今日的國(guó)際地位也非常相像。所以,對(duì)日本援助歷史,特別是90年代援助的國(guó)內(nèi)主體和國(guó)際背景進(jìn)行詳細(xì)解讀,剖析日本在這一時(shí)期如何成為援助領(lǐng)袖國(guó),其援助領(lǐng)導(dǎo)地位又為何在短短十年內(nèi)衰落,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在完善對(duì)外援助機(jī)制、形成中國(guó)話語(yǔ)、應(yīng)對(duì)世界局勢(shì)有著重要的借鑒價(jià)值。

日本如何成為援助領(lǐng)袖國(guó),又為何迅速走向衰落,值得我們反思
從援助金額的猛增到獨(dú)特理念的褪色:日本援助歷史回顧
日本對(duì)外援助始于20世紀(jì)50年代。當(dāng)時(shí)日本在國(guó)際上的形象仍然停留在“二戰(zhàn)軸心國(guó)”上,為了重新融入國(guó)際體系,[2]日本開始積極向亞洲鄰國(guó)提供賠款。[3]這一時(shí)期,日本政府采用“基于請(qǐng)求”的方法來(lái)決定資助的項(xiàng)目:先由政府把款項(xiàng)支付給日本企業(yè),再由企業(yè)向受援國(guó)指定的項(xiàng)目提供產(chǎn)品和勞務(wù)。[4]這一時(shí)期援助的主要特點(diǎn),是迎合日本國(guó)內(nèi)企業(yè)擴(kuò)大出口的經(jīng)濟(jì)需求,且雙邊援助幾乎全部針對(duì)亞洲國(guó)家,特別是印度尼西亞、韓國(guó)、菲律賓等與日本有密切貿(mào)易關(guān)系的國(guó)家。[5]
20世紀(jì)70~80年代,石油危機(jī)使國(guó)際油價(jià)突然上漲,石油供給變得不確定,這加劇了日本的資源脆弱性和商業(yè)波動(dòng)。在這一背景下,援助成為日本與亞洲和非洲資源豐富的國(guó)家建立良好關(guān)系的工具。[6]20世紀(jì)80年代,日本援助在非洲的最大接受國(guó)贊比亞、蘇丹、肯尼亞等,都是日本工業(yè)重要的原材料來(lái)源國(guó)或潛在來(lái)源國(guó),也是有能力吸收日本出口的市場(chǎng)。[7]然而,這種過(guò)于偏重商業(yè)利益、資源導(dǎo)向的援助逐漸招致西方的強(qiáng)烈批評(píng)。美國(guó)和其他G7國(guó)家認(rèn)為日本在國(guó)際貿(mào)易中存在不公平競(jìng)爭(zhēng)、保護(hù)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的行為,出口可能涉及傾銷,[8]因此要求日本將部分貿(mào)易順差用于增加援助。
這些來(lái)自西方國(guó)家的指責(zé)顯然不利于日本國(guó)際地位的提升。于是,日本開始通過(guò)擴(kuò)大援助規(guī)模來(lái)應(yīng)對(duì)國(guó)際輿論壓力。1978年,政府宣布了“ODA倍增計(jì)劃”,使日本在1983年成為世界第二大捐助國(guó)。[9]1988年,日本發(fā)布了“第4次ODA中期目標(biāo)”,使1988~1992年的ODA金額比1983~1987年翻一番,達(dá)到500億美元。[10]同年,日本對(du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qū)的雙邊援助總額達(dá)9.43億美元,超過(guò)了美國(guó)(7.72億美元)。[11]到1989年,日本ODA撥款達(dá)到109.5億美元,[12]超過(guò)美國(gu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雙邊官方發(fā)展援助捐助國(guó)。到20世紀(jì)90年代,援助成為日本最具擴(kuò)張性的戰(zhàn)略之一,其援助金額位列世界第一且范圍遍及全球,引起了國(guó)際社會(huì)關(guān)注。
除了擴(kuò)大援助規(guī)模應(yīng)對(duì)西方國(guó)家指責(zé),日本也發(fā)展出了自己的援助理念。20世紀(jì)90年代的日本已經(jīng)是一個(gè)經(jīng)濟(jì)強(qiáng)國(guó),也希望借助兩極格局結(jié)束的契機(jī),成為世界上有分量的大國(guó),因此較為主動(dòng)地對(duì)自身的發(fā)展理念和援助政策進(jìn)行宣傳。此外,一方面由于冷戰(zhàn)結(jié)束后非洲對(duì)于西方國(guó)家的戰(zhàn)略地位不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非洲大多數(shù)國(guó)家在接受了數(shù)十年援助后依然貧困,這使得傳統(tǒng)援助國(guó)出現(xiàn)了援助疲勞。在此背景下,日本開始批評(píng)西方國(guó)家在非洲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政策中的負(fù)面影響,不完全贊同華盛頓共識(shí)等新自由主義政策。日本強(qiáng)調(diào)的是受援國(guó)的“自助努力”,讓各國(guó)實(shí)現(xiàn)自力更生,擺脫對(duì)援助的依賴。在對(du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政策提出批評(píng)后,基于對(duì)亞洲經(jīng)濟(jì)快速增長(zhǎng)的解釋,日本提出了一種以自身發(fā)展型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為中心的替代發(fā)展方式,[13]在援助中關(guān)注道路、通信、電力等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
然而,20世紀(jì)80年代《廣場(chǎng)協(xié)議》引起了日元升值,擴(kuò)大了日本的經(jīng)濟(jì)泡沫,加重了90年代的大規(guī)模通貨緊縮和嚴(yán)重的財(cái)政赤字紀(jì)錄,終止了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jì)奇跡。預(yù)算危機(jī)迫使政府通過(guò)削減公共開支和增稅來(lái)減少赤字,第五個(gè)援助翻倍計(jì)劃也被放棄。1998年,日本首次削減ODA預(yù)算,2001年又削減預(yù)算至98億美元,低于美國(guó)的114億美元,從此失去了“最大捐助國(guó)”的身份。此后,以自助努力為要旨的日本援助也逐漸被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方向同化,轉(zhuǎn)變成同時(shí)關(guān)注安全、減貧、環(huán)境、人道主義等多項(xiàng)議題的發(fā)展合作。
東亞奇跡與“發(fā)展型國(guó)家”:日本發(fā)展知識(shí)的形成
在20世紀(jì)90年代,日本的援助理念并非對(duì)西方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復(fù)制,而是提出了一套獨(dú)特的發(fā)展知識(shí)和援助方式。這首先有賴于日本自身成功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隨著日本經(jīng)濟(jì)自20世紀(jì)80年代飛速發(fā)展,日本向國(guó)際社會(huì)講述其戰(zhàn)后發(fā)展經(jīng)歷和知識(shí)的意愿也不斷加強(qiáng)。這一時(shí)期,日本國(guó)內(nèi)外的學(xué)者們對(duì)日本自“二戰(zhàn)”以來(lái)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的研究,為日本在援助中推廣其“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理念奠定了基礎(chǔ)。
“發(fā)展型國(guó)家”這一概念首先是由國(guó)外學(xué)者提出的。20世紀(jì)70~80年代,日本等東亞國(guó)家戰(zhàn)后的高速增長(zhǎng),與拉美國(guó)家進(jìn)口替代戰(zhàn)略的失敗及非洲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停滯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引起了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如查默斯·約翰遜對(duì)日本通產(chǎn)省的研究、阿姆斯登對(duì)韓國(guó)產(chǎn)業(yè)政策獎(jiǎng)懲措施的分析、彼得·埃文斯對(duì)韓國(guó)等四國(guó)“嵌入性自主”的總結(jié)等。約翰遜在其著作《通產(chǎn)省與日本奇跡》中首先總結(jié)了日本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日本官僚機(jī)構(gòu)能夠不受政治和社會(huì)力量要挾,同時(shí)具有強(qiáng)烈的發(fā)展意愿,通過(guò)行政指導(dǎo)來(lái)引導(dǎo)和保護(hù)日本戰(zhàn)略產(chǎn)業(yè)。此外,官僚機(jī)構(gòu)能夠通過(guò)退休后在私營(yíng)公司擔(dān)任高級(jí)職務(wù)的前官員與公司建立密切關(guān)系。通過(guò)這些舉措,通產(chǎn)省在60年代推動(dòng)了日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變化,為日本的快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做出了貢獻(xiàn)。[14]進(jìn)而,日本學(xué)者也對(duì)本國(guó)自“二戰(zhàn)”以來(lái)凸顯出發(fā)展型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的產(chǎn)業(yè)政策做了進(jìn)一步闡述。日本政府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的頭十五年里大力促進(jìn)一些薄弱工業(yè)的發(fā)展,如提供關(guān)稅保護(hù)、鼓勵(lì)引進(jìn)先進(jìn)技術(shù),特別是鼓勵(lì)在國(guó)際市場(chǎng)上具有規(guī)模經(jīng)濟(jì)、高固定成本、有借鑒經(jīng)驗(yàn)和潛力的產(chǎn)業(yè)。[15]早期受到格外關(guān)照的行業(yè)包括鋼鐵、汽車、紡織、造船業(yè)、鋁加工業(yè)。后來(lái),產(chǎn)業(yè)政策的重點(diǎn)范圍縮小到技術(shù)方面,例如通過(guò)鼓勵(lì)投資建設(shè)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的技術(shù)基地,促進(jìn)電子、半導(dǎo)體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日本的種種發(fā)展型國(guó)家實(shí)踐,為其他想要趕超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展示了一條與當(dāng)時(shí)主要西方國(guó)家和國(guó)際組織倡導(dǎo)的新自由主義不同的路徑。
有了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日本發(fā)展實(shí)踐的總結(jié),當(dāng)世界銀行開始倡導(dǎo)私有化和自由市場(chǎng)時(shí),日本政府便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日本旨在說(shuō)服世行改變對(duì)定向信貸政策的反對(duì)態(tài)度,改變世行對(duì)于國(guó)家在發(fā)展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并使之更加關(guān)注東亞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的特殊性,肯定日本對(duì)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的貢獻(xiàn),認(rèn)可日本在發(fā)展思維方面的領(lǐng)導(dǎo)作用。1991年10月,日本海外經(jīng)濟(jì)協(xié)力基金公布了一份有關(guān)世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方法的文件,承認(rèn)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貸款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但也揭示了欠發(fā)達(dá)國(guó)家市場(chǎng)機(jī)制的局限性,并對(duì)世行廣泛建議的放松管制、私有化和進(jìn)口自由化存疑。該文件尤其批評(píng)世行在任何情況下都采取了幾乎相同的一套措施,甚至在私營(yíng)部門非常不發(fā)達(dá)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qū)也是如此。文件建議必須采取措施促進(jìn)工業(yè)發(fā)展并從東亞國(guó)家的經(jīng)驗(yàn)中吸取教訓(xùn)。為了進(jìn)一步推動(dòng)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理念,日本政府還資助了世行于1993年發(fā)布的題為“東亞奇跡”的研究,探討了日本、韓國(guó)、泰國(guó)、印度尼西亞和亞洲其他地方經(jīng)濟(jì)成功的原因。該報(bào)告強(qiáng)調(diào)了政府對(duì)這些經(jīng)濟(jì)體走向成功起到的關(guān)鍵引導(dǎo)作用和政府能力的重要性,闡明了東亞國(guó)家在政府引導(dǎo)資本積累、保護(hù)具有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性的產(chǎn)業(yè)、制定引導(dǎo)市場(chǎng)的產(chǎn)業(yè)政策等方面的經(jīng)驗(yàn)。
構(gòu)建援助大國(guó):90年代的日本援助戰(zhàn)略
20世紀(jì)90年代,日本在東京非洲發(fā)展國(guó)際會(huì)議、《官方發(fā)展援助憲章》等對(duì)非洲援助的平臺(tái)和章程上推廣并實(shí)踐了亞洲模式。1992年,日本呼吁召開東京非洲發(fā)展國(guó)際會(huì)議(TICAD I),會(huì)議有來(lái)自48個(gè)非洲國(guó)家、13個(gè)捐助者、10個(gè)國(guó)際組織的近1000名與會(huì)者。日本組織這次會(huì)議的動(dòng)機(jī)有三個(gè):一、以日本的經(jīng)濟(jì)財(cái)富在非洲創(chuàng)造一個(gè)積極的援助環(huán)境;二、通過(guò)國(guó)際援助來(lái)樹立自身“世界大國(guó)”的形象;三、宣傳亞洲發(fā)展模式。這次會(huì)議最重要的成果是批準(zhǔn)了《非洲發(fā)展問(wèn)題東京宣言》,其主題是強(qiáng)調(diào)伙伴關(guān)系、所有權(quán)和亞洲發(fā)展模式,有助于非洲國(guó)家的“自助努力”。[16]
自助努力和伙伴關(guān)系意味著日本和非洲國(guó)家對(duì)發(fā)展進(jìn)程的同等影響和投入,與世界銀行和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替受援國(guó)制定政策的傳統(tǒng)做法不同,東京會(huì)議和1992年的《官方發(fā)展援助憲章》明確主張雙方作為平等成員都應(yīng)對(duì)發(fā)展過(guò)程起到推動(dòng)作用,而非僅僅等待日本單方面的給予。自助努力被認(rèn)為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有發(fā)展意愿的先決條件,這是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一大特征。另外,日本政府在援助類型上與經(jīng)合組織(OECD)對(duì)援助質(zhì)量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存在分歧,OECD要求提供贈(zèng)款援助而不是低息貸款,與捐助國(guó)貨物和服務(wù)沒有捆綁的援助,并向最不發(fā)達(dá)國(guó)家提供援助。相比之下,日本的援助方法與OECD不同,強(qiáng)調(diào)為精心挑選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起飛的自助努力提供更好的支持。日本認(rèn)為,西方的援助只會(huì)鼓勵(lì)低效的經(jīng)濟(jì)政策,甚至讓某些國(guó)家習(xí)慣于簡(jiǎn)單地拿錢,助長(zhǎng)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依賴性;而日本通過(guò)提供低息貸款,規(guī)定了受援國(guó)的償還義務(wù),因而對(duì)受援國(guó)有所約束,鼓勵(lì)它們更有效地使用資源。除了政府的實(shí)踐外,日本的私營(yíng)部門在貸款優(yōu)于贈(zèng)款這一政策上的作用也很重要。日本公司雖然沒有正式參與確定貸款分配,但是包括通產(chǎn)省在內(nèi)的四個(gè)部委必須就援助政策進(jìn)行磋商,通過(guò)通產(chǎn)省,企業(yè)可以在援助計(jì)劃中獲得一定的商業(yè)利益。雖然其他發(fā)達(dá)國(guó)家要求日本政府發(fā)放一般無(wú)條件貸款,外務(wù)省也希望促進(jìn)對(duì)貸款的全面松綁,但因?yàn)樵獾缴探绾屯óa(chǎn)省的強(qiáng)烈抵制,最后貸款只對(duì)重債窮國(guó)解除了捆綁。

在對(duì)非援助中,日本試圖以其代表的亞洲模式與新自由主義援助模式分庭抗禮
日本在20世紀(jì)90年代力圖構(gòu)建起一個(gè)有關(guān)援助新理念和新方向的對(duì)話,讓其他捐助國(guó)和國(guó)際機(jī)構(gòu)參與進(jìn)來(lái),以此與新自由主義的經(jīng)濟(jì)意識(shí)形態(tài)和贈(zèng)予禮物式的援助模式分庭抗禮。在通過(guò)援助達(dá)到大國(guó)地位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下,日本積極宣傳自己獨(dú)特的援助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以援助雙方的平等關(guān)系為基礎(chǔ),以受援國(guó)自發(fā)的努力為前提,讓受援國(guó)通過(guò)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工業(yè)發(fā)展等手段實(shí)現(xiàn)自給自足和減貧。如果這一新的援助框架能夠融入主流援助方式,則證明日本確實(shí)具備一種堅(jiān)實(shí)的知識(shí)根基,使其獲得大國(guó)應(yīng)有的影響力和號(hào)召力。
被“架空”的援助大國(guó):日本援助的失敗教訓(xùn)
事與愿違,整個(gè)20世紀(jì)90年代日本轟轟烈烈的援助戰(zhàn)略最終沒能換來(lái)國(guó)際上的領(lǐng)導(dǎo)地位。這主要是因?yàn)槿毡镜脑I(lǐng)導(dǎo)位置是僅由援助數(shù)量支撐起來(lái)的“危樓”,缺少?gòu)V受認(rèn)可的援助和發(fā)展的話語(yǔ)作為穩(wěn)固的地基。
首先,經(jīng)濟(jì)衰退引起的援助數(shù)量下降,使得支撐日本發(fā)展知識(shí)和援助地位的唯一支柱崩塌。20世紀(jì)90年代末期,東亞經(jīng)濟(jì)危機(jī)給日本帶來(lái)了很大的財(cái)政約束。除了日本自身金融體制管理和能力、主導(dǎo)產(chǎn)業(yè)選擇[17]、失去后發(fā)優(yōu)勢(shì)[18]等內(nèi)部原因,國(guó)際上經(jīng)濟(jì)和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與主要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矛盾沖突也是日本經(jīng)濟(jì)危機(jī)爆發(fā)不可忽略的原因。1985年的廣場(chǎng)協(xié)議,加速了日元升值,直接沖擊了出口導(dǎo)向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由于對(duì)日元長(zhǎng)期升值的預(yù)期,日本股市和房地產(chǎn)市場(chǎng)的狂熱也造成了泡沫經(jīng)濟(jì)。[19]冷戰(zhàn)的結(jié)束也使得日本逐漸失去了原先國(guó)際同盟在技術(shù)、市場(chǎng)、安全方面的幫助,而且美日兩國(guó)在高新技術(shù)和雙邊貿(mào)易領(lǐng)域還成了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20]面臨日益緊縮的財(cái)政預(yù)算和緊缺的援助金額,日本再次開始強(qiáng)調(diào)私營(yíng)部門參與援助,對(duì)國(guó)外經(jīng)濟(jì)利益的考量又一次成為援助政策優(yōu)先事項(xiàng)。然而,20世紀(jì)90年代的國(guó)際話語(yǔ)較50~60年代已經(jīng)有了巨大轉(zhuǎn)變。戰(zhàn)后曾經(jīng)普遍認(rèn)為政府規(guī)劃在經(jīng)濟(jì)騰飛中至關(guān)重要,貿(mào)易和援助結(jié)合可以通過(guò)涓滴效應(yīng)使不發(fā)達(dá)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主流觀點(diǎn)并未兌現(xiàn),國(guó)際援助的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了減貧、人道主義上,因而要求援助活動(dòng)與援助國(guó)自身的商業(yè)利益去捆綁化。在這一背景下,日本重提國(guó)內(nèi)企業(yè)利益明顯與國(guó)際主流話語(yǔ)相悖,因此被指責(zé)為把自己的經(jīng)濟(jì)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對(duì)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等國(guó)際議程做出貢獻(xiàn),這無(wú)疑不利于大國(guó)形象的樹立。

日本的援助領(lǐng)導(dǎo)地位是缺乏根基的“危樓”,必將因本國(guó)經(jīng)濟(jì)衰退而崩塌
其次,日本的發(fā)展知識(shí)和援助方式在國(guó)際舞臺(tái)上始終沒有成為主流。20世紀(jì)70年代,當(dāng)世界上的主要捐助國(guó)開始探討援助去捆綁化時(shí),日本援助卻一直為國(guó)內(nèi)企業(yè)在海外運(yùn)營(yíng)提供便利;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在主要援助國(guó)提倡滿足受援國(guó)的基本需求、通過(guò)NGO更加深入到貧困人口時(shí),日本則呼吁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自助努力。這種不一樣的聲音自然遭到了西方國(guó)家的抵制。20世紀(jì)70年代后期開始,新自由主義成為主導(dǎo)的發(fā)展思想,主張自由市場(chǎng),比如實(shí)施競(jìng)爭(zhēng)性匯率制度,支持貿(mào)易自由化、國(guó)有企業(yè)私有化等,[21]反對(duì)國(guó)家干預(yù)。[22]在新自由主義話語(yǔ)下,東亞奇跡也被解釋為東亞國(guó)家逐步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自由化的結(jié)果,而日本提出的發(fā)展型國(guó)家方案則被冷落。新自由主義在當(dāng)時(shí)已然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論,大量知名學(xué)者和國(guó)際組織論述了自由市場(chǎng)的優(yōu)勢(shì),如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得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等等;而關(guān)于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著作則屈指可數(shù),也沒有大量日本學(xué)者在國(guó)際頂尖的學(xué)術(shù)出版物上梳理日本經(jīng)驗(yàn)。而且在東亞金融危機(jī)的背景下,IMF提出了附加條件,迫使日本等東亞國(guó)家接受華盛頓共識(shí)并進(jìn)行改革以獲得貸款,這些經(jīng)濟(jì)體的國(guó)家能力也因此遭到削弱。[23]在政府、學(xué)界集體失聲,企業(yè)為了收益參與援助的做法受到詬病的情況下,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受眾范圍遠(yuǎn)不如新自由主義。
最后,在援助方法上,日本也難以和傳統(tǒng)援助國(guó)對(duì)話并得到認(rèn)可。西方捐助者在推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善政和仿效國(guó)際最佳做法的援助政策。例如,世界銀行根據(j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政府特征提煉出營(yíng)商環(huán)境指標(biāo)和全球治理指標(biāo),并根據(jù)這些標(biāo)準(zhǔn)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進(jìn)行排名。這種試圖通過(guò)已處于發(fā)達(dá)狀態(tài)多年的國(guó)家的標(biāo)準(zhǔn)找出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弱點(diǎn)的邏輯,在很大程度上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政治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觀的“正確性”,而忽略了執(zhí)行中的可行性。這種更加注重從知識(shí)、思想出發(fā)的援助政策很容易提煉成朗朗上口的概念,如人類基本需求、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援助有效性等,也很容易被發(fā)展中國(guó)家廣泛接受。相較之下,日本在發(fā)展型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推動(dòng)下,對(duì)能夠取得具體成果的項(xiàng)目感興趣,在政策上優(yōu)先傾斜有潛力的關(guān)鍵產(chǎn)業(yè)部門,而沒有及時(shí)提煉形式上的正確性,也沒有建構(gòu)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比如日本認(rèn)為發(fā)展中國(guó)家必須有足夠的能力獲得外匯,因?yàn)榻Y(jié)束援助或自助努力相當(dāng)于通過(guò)內(nèi)部資源調(diào)動(dòng)確保足夠的能力為發(fā)展支出提供資金。由于外匯收購(gòu)的引擎是出口導(dǎo)向型產(chǎn)業(yè),而基礎(chǔ)設(shè)施對(duì)吸引外國(guó)投資者至關(guān)重要,所以日本援助形成了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和外國(guó)直接投資相結(jié)合的方法。然而,在與西方援助國(guó)的競(jìng)爭(zhēng)中,日本沒能守住自己在援助領(lǐng)域最鮮明的特點(diǎn),反而越來(lái)越附和西方援助國(guó)的話語(yǔ),從自助努力、重視基礎(chǔ)設(shè)施慢慢轉(zhuǎn)變?yōu)橥瑫r(shí)考慮安全、環(huán)境、減貧等多項(xiàng)事宜的雜項(xiàng)清單。如2003年《發(fā)展合作大綱》涵蓋了安全、政府治理、促進(jìn)基本人權(quán)、人道主義援助等,而日本曾經(jīng)希望宣傳的發(fā)展型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伙伴關(guān)系和自助努力的援助方式則被淡化。
啟示
國(guó)際援助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不僅體現(xiàn)在量上,更體現(xiàn)在對(duì)輿論、議題設(shè)置的影響力上。[24]即使日本在援助金額上成為世界第一大援助國(guó),但有關(guān)援助和發(fā)展的話語(yǔ)和知識(shí)還是在世界銀行、IMF、經(jīng)合組織國(guó)家等傳統(tǒng)援助力量的支配之下。日本雖提出了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援助理念,但相應(yīng)的知識(shí)體系構(gòu)建和維持能力卻遠(yuǎn)不及傳統(tǒng)援助國(guó),因此可說(shuō)是一個(gè)被“架空”了的援助大國(guó)。日本的這段援助歷史折射出來(lái)的多重問(wèn)題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日本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能力和援助知識(shí)生產(chǎn)能力還不足以幫助其在國(guó)際援助體系中站穩(wěn)腳跟。在日本崛起為一個(gè)援助大國(guó)時(shí),日本只聲稱自身的發(fā)展型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是一條獨(dú)特的替代發(fā)展路徑,卻沒有清晰簡(jiǎn)潔地闡明自身理念的優(yōu)勢(shì),夯實(shí)替代路徑的知識(shí)根基。日本政府和學(xué)術(shù)界缺乏對(duì)本國(guó)經(jīng)驗(yàn)的獨(dú)創(chuàng)性研究和總結(jié)能力,而是依靠國(guó)外學(xué)者的觀點(diǎn)或資助國(guó)際組織的研究報(bào)告來(lái)闡釋自身的理念。當(dāng)企業(yè)界希望通過(guò)走出國(guó)門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援助雙方的互利雙贏,卻被國(guó)際社會(huì)指責(zé)為不關(guān)心貧困人群需求的時(shí)候,日本政府和學(xué)術(shù)界也無(wú)力論證通過(guò)企業(yè)實(shí)施的項(xiàng)目或援助貸款的合理性和優(yōu)越性。與此同時(shí),傳統(tǒng)援助國(guó)大力推廣華盛頓共識(shí),通過(guò)援助附加條件,使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逐漸在非洲國(guó)家扎下了根。
第二,日本對(duì)自身援助和發(fā)展成果的曝光度還不夠高。日本在援助中雖然非常強(qiáng)調(diào)項(xiàng)目的實(shí)際效果,實(shí)行基于請(qǐng)求的方法、注重基礎(chǔ)設(shè)施等能夠幫助發(fā)展中國(guó)家走上自助努力道路的援助內(nèi)容,但這些聲音終究被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援助解綁、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等為人熟知的話語(yǔ)淹沒了。雖然有政府在東京非洲發(fā)展國(guó)際會(huì)議上的倡議,但日本的企業(yè)界、學(xué)術(shù)界等參與對(duì)外援助工作的主體沒有有效地投入到對(duì)其發(fā)展道路和援助項(xiàng)目的分享中。比如日本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自身發(fā)展型國(guó)家研究的知名度甚至不及國(guó)外研究者,在國(guó)際一流的英文學(xué)術(shù)雜志上多見國(guó)外學(xué)者對(duì)日本援助體系的總結(jié)或批判,卻少見日本學(xué)者參與討論。這樣一來(lái),一旦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發(fā)生波動(dòng)或遭到其他國(guó)家的遏制使得援助數(shù)額有所下降,新興援助國(guó)的發(fā)展理念和互助關(guān)系就被不斷質(zhì)疑,只由援助數(shù)量支撐起來(lái)的脆弱的國(guó)際地位非常容易崩塌。
我國(guó)今天的對(duì)外援助情況與20世紀(jì)80~90年代的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國(guó)也擁有“成功的后發(fā)追趕者”和“援助大國(guó)”的雙重身份,我國(guó)提倡的“南南合作”也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南北合作”理念有所不同,與日本當(dāng)年提出的“伙伴關(guān)系”更為相似。同時(shí),對(duì)外援助也一直是我國(guó)企業(yè)走出去的重要推力。因此,日本曾經(jīng)盛極一時(shí)的對(duì)外援助歷史及其被傳統(tǒng)援助體系“架空”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對(duì)我國(guó)有很大的啟示與參考意義。能夠構(gòu)建發(fā)展知識(shí)體系,并清晰地言說(shuō)自身的發(fā)展道路,意味著有能力主動(dòng)地選擇和界定全球議題,吸引國(guó)際社會(huì)的關(guān)注和分享,并最終將自身的發(fā)展知識(shí)納入到國(guó)際議程中,將國(guó)際議程導(dǎo)向有利于與發(fā)展中國(guó)家進(jìn)行互利合作、與傳統(tǒng)援助國(guó)進(jìn)行平等對(duì)話的雙贏局面。正如新自由主義雖然被傳統(tǒng)援助者當(dāng)作自身的發(fā)展模式來(lái)宣傳,但它同時(shí)也是一種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和政府運(yùn)作的規(guī)則框架。通過(guò)新自由主義知識(shí)和話語(yǔ),傳統(tǒng)援助國(guó)構(gòu)筑了其理想的援助世界。而通過(guò)諸如全球治理指標(biāo)排名、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完成情況等遍布各受援國(guó)的國(guó)際規(guī)范,其援助制度也支撐起了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引領(lǐng)地位和話語(yǔ)影響力,可以說(shuō)發(fā)展知識(shí)與政治經(jīng)濟(jì)影響力是一種共生關(guān)系。
因此,為世界貢獻(xiàn)一個(gè)蘊(yùn)含我國(guó)自身發(fā)展知識(shí)的國(guó)際合作圖景,就是為我國(guó)定制一張真正進(jìn)入國(guó)際規(guī)則制定場(chǎng)所、對(duì)當(dāng)前國(guó)際合作的普遍性價(jià)值擁有發(fā)言資格的通行證。我國(guó)只有在發(fā)展經(jīng)驗(yàn)與發(fā)展合作上有自己的知識(shí)供給,提高自身發(fā)展知識(shí)的邏輯性、價(jià)值、信度,打通全球知識(shí)生產(chǎn)場(chǎng)所、關(guān)鍵國(guó)際組織或機(jī)制等國(guó)際議程制定渠道,才能跳出只能以傳統(tǒng)援助國(guó)的標(biāo)準(zhǔn)、規(guī)則、價(jià)值傾向?yàn)榘l(fā)展合作唯一裁量準(zhǔn)則的被動(dòng)局面,逐步完善有利于南南合作的國(guó)際議程。
(責(zé)任編輯:張文倩)
注釋:
*本文系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多元主體共同參與中國(guó)對(duì)非援助機(jī)制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16BGJ021,主持人:徐秀麗)階段性成果。
[1]?[24] 彭云:《試析日本的援助理念》,載《外交評(píng)論》 (外交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年第2期。
[2]?黃梅波、洪燕秋:《日本對(duì)非發(fā)展援助的成效與發(fā)展趨勢(shì)——基于非洲發(fā)展東京國(guó)際會(huì)議平臺(tái)的研究》,載《國(guó)際經(jīng)濟(jì)合作》2014年第4期。
[3]?陳子雷:《發(fā)展援助, 政企合作與全球價(jià)值鏈——日本對(duì)外經(jīng)濟(jì)合作的經(jīng)驗(yàn)與啟示》,載《國(guó)際經(jīng)濟(jì)合作》2017年第12期。
[4] [10]?金熙德:《日本政府開發(fā)援助》,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年版。
[5] [6] [8]?Caro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7]?Peter J. Schraeder, Steven W. Hook, and Bruce Taylor, “Clarifying the Foreign Aid Puzzle: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Japanese, French, and Swedish Aid Flows,” World Politics, Vol.50, No.2, 1998.
[9]?[12] David Arase, Japans Foreign Aid: Old Continuities and New Directions, Routledge, 2012.
[11]?Pedro Amakasu Raposo, Japans Foreign Aid Policy in Africa: Evaluating the TICAD Process, Springer, 2014.
[13] [16] Howard Lehman , “Japans foreign aid policy to Africa since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Pacific Affairs, Vol.78, No.3, 2005.
[14]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World Bank,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OUP, 1993.
[17] [20]?毋俊芝、安建平:《淺析20世紀(jì)90年代日本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載《山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年第1期。
[18]?傅鈞文:《日本金融危機(jī)分析》,載《世界經(jīng)濟(jì)研究》1998年第4期。
[19]?楊锃:《經(jīng)濟(jì)危機(jī)下,能否拒絕社會(huì)性危機(jī) 20世紀(jì)80年代的 “廣場(chǎng)協(xié)議” 和日本經(jīng)濟(jì)衰退》,載《社會(huì)》2009年第1期。
[21]?John Williamson, “The Strang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27, No.2, 2004.
[22]?Ha-Joon Chang, “Breaking the mould: an institution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lternative to the neo-liberal theory of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6, No.5, 2002;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23]?張晨、王娜:《新自由主義與發(fā)展型國(guó)家的衰落》,載《河北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