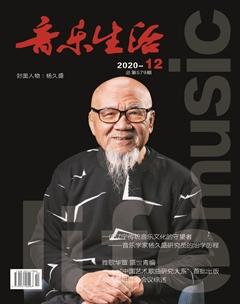評網絡時代的音樂綜藝轉型及對音樂本質的反思

一、網絡:綜藝節目的新陣地
在技術、資本和用戶的共同推動下,網絡綜藝橫空出世。從它的成長歷程來看,實則是一場與電視綜藝之間此消彼長的較量。首先,網絡綜藝憑借著更廣泛的選題、更細致的目標群體劃分和更強的互動性等優勢,分流了一批電視觀眾。接著,在線視頻無限次播出回放和手機APP隨時隨地觀看,與當下人們碎片化的時間觀念實現了深度匹配,所以它在改變人們觀影方式的同時,再次為網絡綜藝俘獲了一批觀眾。可以說,網絡作為綜藝節目的新陣地,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尤其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一批足以與湖南、浙江衛視等主流電視綜藝平臺相抗衡的網絡平臺,為網絡自制綜藝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以愛奇藝、優酷、騰訊最具影響力,《我是唱作人》就是由愛奇藝打造的一檔“純網綜藝”。
1.背靠大樹好乘涼
2010年6月,愛奇藝正式推出自制節目。之后在音樂類綜藝方面,相繼推出了《十三億分貝》(2016)、《中國有嘻哈》(2017)、《中國新說唱》(2019)等超級網綜節目。從這些節目斬獲的成績來看,它們集中反映了愛藝奇超強的制作能力和成熟的商業模式。《我是唱作人》目前已經成功推出兩季,正是得益于大樹底下好乘涼。
(1)精良的節目制作
自網絡綜藝誕生之日起,它與電視綜藝的較量便展開了。只是沒想到這場角逐從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初發起,未到十年底就已經揭曉答案。時至今日,不能說網絡綜藝完勝電視綜藝,但網絡綜藝后來者居上的勢頭已是有目共睹。盡管這個結局在初始階段難以預料,但二者在制作水平上持平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并沒有什么懸念。這些年,愛奇藝一邊夯實人才隊伍建設,一邊引進新技術,來提升節目制作水平并致力于打造精品。以《我是唱作人》為例,在它的制作團隊中,總監制陳偉被行業評為中國十大金牌制作人之一,制片人兼總導演車澈和音樂總監譚伊哲也是業內的頂尖人才。而愛奇藝于2014年建立起的基于視頻數據理解人類行為從而指導內容的制作、生產、運營、消費的視頻大腦,在全球范圍內則是首家。正是這些過硬的條件,保證了《我是唱作人》節目的制作水平。從兩季節目在豆瓣上的評分來看,第一季和第二季分別為7.5和7.4,遠高于同期其他音樂綜藝節目。
(2)成熟的商業模式
在商業模式的探索上,網絡綜藝平臺集體制定了“一手抓廣告,一手抓會員”戰略。一方面,網絡自制綜藝憑借著更加靈活的廣告植入方式,不僅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贊助商的青睞,也顛覆了人們對廣告的傳統認知。尤其是愛奇藝自制節目《奇葩說》的出現,破天荒地促成了觀眾與廣告二者拋棄“成見”達成了“和解”。之后,這種把廣告“有趣化”的手法在網絡綜藝界被運用得愈加嫻熟,綜藝節目在消費觀眾的過程中進一步拉近了制作方與廣告贊助商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講,網絡自制綜藝重新“定義”了廣告而促成了制作方、廣告贊助商與觀眾的“大團圓”,直接為其一步步蠶食電視綜藝的地位埋下了伏筆。《我是唱作人》中,節目的多個環節都實現了節目內容和廣告內容的深度融合。而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沒有絲毫違和感,并且積極地參與到了廣告商設計的各種游戲之中。如第一季專門為某贊助商定制的廣告曲,既新穎又叫賣;再如,觀眾可以通過網絡投票助力自己喜歡的選手直接進決賽,但必須要通過贊助商指定的渠道等等。
另一方面,網絡視頻平臺不斷營造所謂的特權,如屏蔽節目開播前后的廣告和選擇畫面質量更高的觀影模式等,以此來吸納會員,收取會費。2018年,愛奇藝宣告平臺會員會費收入超過廣告投入[1],成為國內在線視頻行業發展會員經濟的典范。從愛奇藝的營銷策略來看,把特權貫穿于自制節目的各個環節才是其吸納會員最重要的一環。以《我是唱作人》為例,首先,觀眾在為自己喜歡的歌手投票的過程中,會員比普通用戶多一次機會;其次,其衍生節目《開飯啦!唱作人》,只有會員才能欣賞完整版等等。所有這些特權既從節目注重的音樂本質出發,又合理利用了觀眾的喜好和對明星生活的窺探欲,實現了對粉絲經濟的深度挖掘。
2.生于斯長于斯
網絡綜藝誕生于網絡時代,又借助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實現了華麗的轉身。《我是唱作人》以扶持網絡歌手為己任,為他們搭建與主流接軌的競技平臺。此外,該節目在疫情期間借助網絡實現了大眾評審空中投票,拓寬了節目的發展空間。
(1)扶持網絡歌手
“2007年, 搜狐網創辦了國內首檔網絡脫口秀節目《大鵬嘚吧嘚》, 開啟了網絡自制綜藝節目的先河。”[2]之后,網絡自制綜藝篳路藍縷,歷經坎坷,才成就了今天的景象。但不得不說,網絡自制綜藝發展的“陣痛期”也是在電視綜藝壓制下最艱難的一個時期。在“渠道為王”的規則下,網絡自制綜藝只能規避鋒芒默默發展。但時間是最好的緩釋劑,可以看到今天的傳媒行業又重回到了“內容為王”的時代。從網絡綜藝的成長歷程來看,“渠道為王”的退場是因為現在有足夠多地且有影響力的渠道并肩而立,不僅僅是愛奇藝、優酷、騰訊和芒果TV四大巨頭,還有搜狐、樂視、西瓜、好看等后備軍。因此,網絡歌手如果想打贏這場翻身仗,恐怕也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在呼吁社會理解的基礎上,網絡場也需要有一批有足夠影響力的歌手成長起來,并且是帶著充滿誠意的作品而來。屆時,“網絡歌手”這個代名詞也會自然消失。好在這已經是一個網絡時代,筆者認為網絡歌手的春天終究會到來。
網絡自制綜藝在成長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然也深知網絡歌手的不易。并且,大家同在網絡圈,本來就是共生共榮的關系。可以看到,現在很多網絡自制綜藝都自覺承擔了“扶持網絡藝人”這個使命,而其核心就是為網絡藝人搭建一個與主流接軌的平臺。從《我是唱作人》兩季節目邀請的嘉賓來看,既有華語樂壇老將,也有當下主流選秀節目的冠軍。其實也可以講,網絡場并不缺音樂人才,而是急需社會的接納,亟待與主流歌手競技的平臺。所以節目用了“撕掉標簽,用音樂說話”作為臺語,很好地表達了節目的態度,傳遞了正能量。
(2)網絡評審團
3月份,在疫情形勢稍微好轉之時,《我是唱作人》積極響應國家“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復工復產”的號召,開始了第二季的制作和播出。4月下旬,《我是唱作人2》正式播出,與第一季上映的時間正好間隔一年。但不得不說,節目組還是克服了很多困難。該節目音樂總監譚伊哲事后在一次采訪中透漏,為了保證《我是唱作人2》的質量,他的工作室的樂隊全程參與,期間成員做了近十次核酸檢測。[3]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防止群體聚集,節目組天馬行空地想到了把第一季的百人評審團搬到網絡上。愛奇藝通過自己的專用渠道,保證了101位評審員實時收聽,空中投票。可以說這既是特殊情況下的救急方式,也是節目組充分利用網絡的創新。它不僅進一步鞏固了“觀眾滿意”的評價體系,又壓縮了節目成本。
二、原創:同質化治理的原動力
資本在推進我國綜藝節目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造成了綜藝市場秩序的紊亂,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同質化。在這種情況下,廣電總局一邊限制綜藝節目數量的審批,一邊鼓勵各大平臺積極創新。在政策調控和部分綜藝節目策劃人自省下,我國原創綜藝自2013年以后逐步走向正軌。在音樂綜藝方面,《中國好歌曲》(2014年)的揚帆出海,成功地實現了我國音樂綜藝節目的輸出,代表了我國音樂類綜藝實現了由復制、抄襲到原創的升級。《我是唱作人》是由愛奇藝打造的一檔原創音樂綜藝節目,這個原創既包含音樂是原創,又包括節目是原創。
1.音樂原創
縱觀國內音樂綜藝節目的歷史,貼著“原創音樂”標簽的節目不勝枚舉,但真真正正從“原創音樂”出發的節目卻寥寥無幾。這種現象的出現有著較為現實的原因:其一,原創音樂成本高,難以實現短期的大量供應;其二,觀眾對原創音樂的接受程度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從而使節目難以把控。所以,辦這種節目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智慧。
與此同時,國內音樂綜藝在經歷野蠻生長以后,“歌曲荒”逐漸成為制約我國音樂綜藝節目發展的瓶頸,音樂綜藝市場又亟待“原創音樂”來改善。正如一位導演所言:“一檔好的原創音樂節目,無論是對當今的華語樂壇,還是對現在的文化生態而言,都能夠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4]從這個角度而言,“原創音樂”綜藝是一種怎么都不嫌多的音樂綜藝類型。
《我是唱作人》是一檔徹徹底底推廣原創音樂的節目,只是節目另辟蹊徑,以具有一定歌迷基礎的音樂人作為嘉賓,通過他們自有的粉絲基礎來為節目立柱,從而用熱度引發聽眾對“原創音樂”的重視。盡管它不是第一檔做原創音樂的綜藝節目,但是它對“唱作人生態”“歌曲荒”的關注,卻是誠意滿滿。
2.節目原創
《我是唱作人》通過去娛樂化的手法,保證音樂綜藝的音樂屬性;通過去精英化的手法,在保證節目公平性的同時推送大眾喜歡的音樂;通過去常規的手法激發歌手的競爭意識,增添節目的戲劇張力。
(1)去娛樂化
綜藝節目一經出現,便以輕快的節奏和直白的語言拉近了媒介與人的距離,誘導人們進入了視覺主義時代。相比聽覺,視覺在調動人的情緒方面有著更為明顯的優勢。因為“從物理學角度講,光在空氣介質中的傳播速度約是 30 萬千米/秒,而聲音在空氣介質中的傳播速度是約為 340 米/秒,光速是音速的八十多萬倍。從生理學角度講,人類對外界信息的接收主要來自視覺與聽覺,然而視覺信息約占 70% 以上。從心理學角度講,人類在感性層面上,相比聽覺信息而言,更愿意接受視覺信息。所以才有‘眼見為實,耳聽為虛這個說法。”[5]音樂綜藝作為一種特殊的綜藝形式,從其誕生之日起便努力在聽覺和視覺之間尋求平衡點。但不得不說,從這么多年的音樂綜藝實踐來看,節目的聽覺被視覺拽著走好像一直是常態,而它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泛娛樂化。對于當下諸多的綜藝而言,是走向娛樂的藝術,還是堅持藝術的娛樂,是個問題。藝術的娛樂在于不改變“藝術本身的本體性,而是在藝術形式之內加以變化。反之,娛樂的藝術是以娛樂為主體,強調娛樂作用而忽視了藝術本體,把娛樂包裝成藝術作品。”[6]從表面看,這個問題事關生死,但從長遠來看,娛樂的藝術從來都是過眼云煙,靠藝術的娛樂才能幫助一個制作團隊走向成功。近幾年,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音樂綜藝節目開始了音樂本質的回歸,如《中國好聲音》《我們的歌》等節目引用的“盲選”機制就是有益的實踐。
《我是唱作人》創作團隊同樣堅持“去娛樂化”的原則,力求用音樂說話的同時堅持藝術的娛樂。首先,兩季邀請的歌手基本上都屬于言語不多的人,加上整個節目沒有一個調節氣氛的主持人,直接導致了節目錄制過程中的多次場面凝固。這種尷尬的局面看似造成了綜藝劇情的斷片,實則給觀眾帶來了歡樂。其次,整個節目采用機器人代替主持人,在冷面的金屬聲音背后是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提要求、宣結果。去掉了熱鬧的元素,反而讓歌手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音樂本身上面。

(2)去精英化
縱觀我國音樂選秀節目的發展歷程,《歡樂中國超級女聲》被稱為我國電視音樂節目“娛樂化”現象的轉折點,[7]但它亦可以視為我國音樂選秀節目從精英化向去精英化過渡的一個轉折點。《我是唱作人》延續了這種“去精英化”的模式,節目采取明星竟演和大眾評審的演出形式,8位唱作人的勝負和去留由101位大眾評審決定。首先,在綜藝節目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網絡自制綜藝憑借著對大數據更為精準的把握,不斷圍繞著“觀眾滿意”的評價標準更新升級。《我是唱作人》這101位大眾評審就是“觀眾”的一個縮影,他們幾乎覆蓋了社會的每一個層級。從評審團成員來看,他們中既有圈內大咖、音樂專家,也有由普通白領、小鎮青年、高校學生等組成的音樂愛好者。其次,《我是唱作人》節目不僅把投票器送到社會平民手上,還把他們的評語如實地剪輯到節目中。所以,我們在觀看的過程中聽到的“評語”既有專業的、委婉的和客套的,也有自我的、直白的和狂妄的。但這些評語恰恰是真實的、接地氣的,自然也是受“觀眾”歡迎的。
(3)去常規化
去常規化是現在綜藝節目普遍采用的一種方式,不得不說它既是為節目設置懸念和增添戲劇性服務的一種手段,也是對觀眾獵奇心理的一種迎合。在兩季《我是唱作人》節目中,去常規方法隨處可見。首先,投票方式去簡就繁。在這個電子時代,《我是唱作人》第一季仍采取了紙質選票和投票箱這種傳統的投票方式。在采用實名制傳遞公平性的同時,實則是營造出一種儀式感和神圣感。其次,挑戰模式非常規。八位唱作人被劃分為上、中、下三個位區,時而啟用下位區向中位區挑戰、中位區向上位區挑戰的模式,時而啟用上位區與上位區對決、下位區與下位區對決的模式。總而言之,就是要把競爭意識放大到極致,從而激發每位唱作人的斗志。當然,這種挑戰模式也讓每位歌手之前的光環都變成了陪襯,能夠避免淘汰和贏得尊敬的只有作品,并且就是要在現場征服聽眾。
三、唱作:差異化發展的新策略
音樂類綜藝節目同質化不僅嚴重損害了觀眾的期待,也造成了綜藝行業資源的過度消耗。所以,差異化發展已經不再是某一個制作平臺思索的命題,而是整個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是唱作人》以推廣原創音樂為使命,把嘉賓范圍鎖定在既能創作又能演唱的歌手身上,實現了對音樂綜藝核心環節的創新,走出了一條差異化發展之路。
1.唱作人:音樂綜藝的稀有資源
在西方,音樂創作和演唱(奏)一直被視為兩個不同的職業。而在我國,“唱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合一”的。我國的傳統音樂大多數都沒有具體的作曲家,更沒有所謂的首唱者,于是就形成了“人民集體唱作”這樣一種特殊現象。[8]直到近代,受西方音樂的影響,加上版權意識的覺醒,音樂創作和演唱在我國才逐漸分離。盡管音樂創作和演唱被視為兩個不同的職業,但總有人同時具備這兩種專業能力,而《我是唱作人》就是把節目定位在這個特殊的人群身上。該節目的名字雖然采取了綜藝流行體,但在素材挑選上卻是眼光獨到。
有人說,互聯網的出現帶來了音樂創作的繁榮。實質上,這句話只能理解為互聯網最大化地打通了音樂傳播的渠道,使得一批“草根”走到了前臺,但并不代表著創作者整體數量的攀升。此外,還有人說,只有音樂專業的人才能談創作,這句話同樣有失偏頗。非音樂專業出身的人在掌握基本的技法之后也能創作,包括在音樂史教科書上都有很多這樣的人,如俄羅斯的鮑羅丁、中國的趙元任等都是“兼職”作曲家。換句話講,音樂創作更大程度上依賴先天性條件,無論是大型的交響曲還是簡單的兒歌,都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而言,音樂創作者既不能把那些天賦異稟但卻非專業出身的人排斥在外,也不能把那些以改編歌詞、惡搞經典等為“創作”的人強行拉入。總體而言,音樂創作依然是少數人的專權。無論我們把音樂創作者的網撒得有多么大,與數量眾多的歌手以及數量龐大的音樂受眾來說,創作者依然是屈指可數。而集優秀創作與演唱能力于一體的人,相應地就更少了。正如一位樂評人所言“從十幾年來國內的音樂選秀節目來看,歌壇不乏愛唱歌、會唱歌的年輕人,但真正缺少的是唱作俱佳的音樂人”。[9]所以《我是唱作人》作為一檔綜藝節目,在唱作人這個領域進行挖掘,其實是找到了一個綜藝資源的富礦。
2.唱作:音樂人的專業考量
《我是唱作人》力求擯棄當下綜藝節目的浮華,用高標準考核選手的音樂素養來凸顯節目的音樂本質。首先,選手會唱還得會作。節目第一季采用上下半季賽制,每位首發唱作人至少要準備7首以上未發表的原創作品。所以,當時節目官宣賽制以后,媒體戲謔這個節目直接“淘汰”華語樂壇近半音樂人。[10]到了第二季,節目引入了更具挑戰性的“一唱到底”模式,意味著每位首發唱作人至少要準備9首原創作品。
其次,選手會作還得會聽。Demo互聽是《我是唱作人》的特設環節,節目要求選手們在所有人試唱完成之后現場挑選對手。Demo(demonstration)的中文意思是音樂小樣,它指的是創作者對音樂作品的一個初步構想,通常只有少許的樂器伴奏,或者就是人聲清唱。節目把這樣一個并不具備表演性質的音樂雛形搬到熒幕上,并非只是要揭開音樂創作的神秘面紗,而是賦予這個環節另外一層涵義,那就是考驗唱作人的“聽力”,因為Demo雖小,卻是歌曲的核心。唱作人們從對方這個微小的立意中捕捉到的信息越多,就能更好地為自己挑選對手提供參考,從而爭取更大的勝算。
3.唱作:音樂的保鮮劑
按照音樂的文化屬性,肯定是流傳時間越久的歌曲越好。但就音樂從生產到傳播這個過程而言,路徑卻是越短越好。由于音樂是抽象的藝術,一首作品在完成一度創作之后必須要通過人聲和樂器把樂譜轉換成聲音才能為人所欣賞,也就是所謂的二度創作。同時音樂又是情感的藝術,任何一個演奏者都不可能把創作者的意圖百分之分地表達出來,他們或多或少都會融入自己的情緒。從這個角度而言,音樂的每一次轉譯都會存在“損耗”。盡管這種“損耗”不是人為的,也不一定純粹就是壞的。但對于聽眾而言,音樂的保鮮度也是一個無可逃避的話題。《我是唱作人》給聽眾帶來的是一個從“采摘到餐桌”的過程,所有競演作品皆為歌手所創作。從所有參賽作品來看,本人作曲是硬性要求,95%以上的詞曲創作和演唱均為同一個人。并且這檔節目還要求所有作品皆為新歌,不允許“老歌重唱”,這樣就最大化地保證了作品的新鮮度。省掉轉述這個環節,就真的是一首歌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就是一首歌。
注釋:
[1] 祖薇:《愛奇藝會員收入首次超過廣告收入》,《北京青年報》2018年12月17日 。
[2] 朱傳欣:《網絡自制綜藝節目的模式創新》,《中國文藝評論》2018年第9期。
[3] 獨家專訪|譚伊哲:流量歌手的音樂就一定沒品質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5961898 99408785&wfr=spider&for=pc,2020年7月8日。
[4][9] 于帆:《讓原創音樂真正唱入人心》,《中國文化報》2019年3月27日。
[5] 王傳歷:《論羅山皮影戲“一曲多用”現象形成的原因——以伴奏音樂中的嗩吶接腔為例》,《齊魯藝苑》2020年第5期。
[6][7] 崔健:《論電視媒介下的音樂價值傳播》,《中國文藝評論》2019年第3期,第68-74頁。
[8]王耀華、杜亞雄編著:《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第47頁。
[10]《我是唱作人》嚴苛賽制“淘汰”華語樂壇近半音樂人http://ent.ifeng.com/c/7ksRhvqnDWq,201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