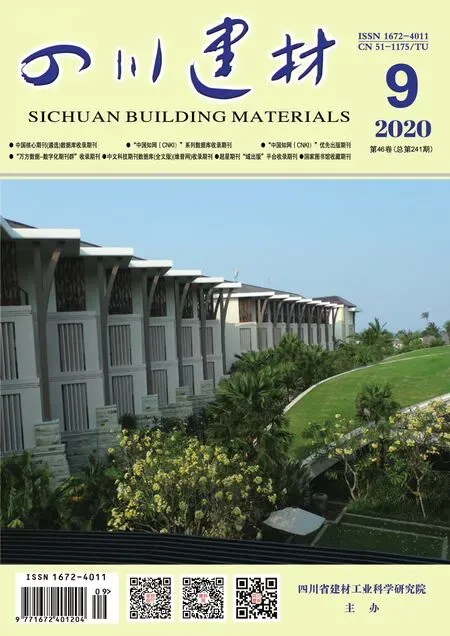西藏建成遺產的問題與保護對策淺議
朱美蓉
(西藏大學 工學院,西藏 拉薩 850012)
0 前 言
面對現代化、城鎮化的發展,隨著高樓林立、數字技術的出現,人們越來越喜歡新奇異的建筑,忽視了建成遺產;隨著城市的擴張與蔓延,建成遺產由衰落、倒塌等原因,而被忽視或被遺棄,如何保持原真性與完整性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常青[1]從處理存量與增量的關系與度,從原型轉化的類型學進行修舊;他認為建筑學應堅守“保護、傳承、轉化、創新”,對原型的傳承由形式到意境,再到異形化的變化[2]。
邵勇[3]認為應加強遺產保護教育與實踐。
薛威[4]認為建成遺產重物質改造,輕社會文化,未解決永續發展的問題。
1 相關概念與理論
1.1 概 念
建成遺產指遺產中建造起來的事物,如城市、景觀、建筑等遺產。西藏自治區(以下簡稱“西藏”)建成遺產的種類有:建筑遺產類型有聚落;古建筑、古跡、古遺址與環境;民居、莊園、宗堡、宮殿,如布達拉宮、大昭寺、帕拉莊園、藏王墓;城鎮遺產,如拉薩、日喀則、江孜;園林遺產,如羅布林卡。保護模式分為修復性與開發性兩種,如桑珠孜保護與修復設計;主要保護建筑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1.2 演變歷程、影響因素、思想基礎與特征
1)演變歷程:從生產方式上,由順應自然的以石器為主的游牧農業,到改造自然的以鐵器、蒸汽機為主的工業,再到按規律改造與利用自然的信息時代。
2)影響因素,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如西藏地理位置處于高原,處于較為封閉的、以農牧業為主的地區。
3)思想基礎:受到藏、漢、印尼等文化的交流與影響。
4)特征:歷史環境、地域特色、史地維度、社會文化性[1]。
2 問 題
2.1 技術難度大
建成遺產存在分布廣、種類多、技術難度大等問題。歷史建筑存在的技術問題,如基礎不牢,墻角磨損,基地滲水,柔性地面;墻柱歪閃,墻體倒塌,有裂縫,不能負擔相應的荷載,保溫性能差,木材遭到腐蝕、干裂;屋頂落架大修,屋頂防水;原有材料難以繼續使用,如阿嘎土。景觀遺產存在的問題,如園林植物很難經過幾個世紀的延續,新的植被與歷史建筑的如何組合;地形地貌的改變,如水源、河流的變化。在現代語境下,茶馬古道等文化線路的發展。歷史文化街區作為特定時期的生活方式的見證,由于其內部民居的物質環境存在缺陷,如隔聲、采光、保溫與隔熱等;可能出現平民化、空心化的問題。城市遺產如傳統村落、歷史文化名城等,城市不是一次建成的,在城市里可能同時存在吐蕃、薩迦、帕竹、近現代等各個時期的建筑,體現了多樣性。
2.2 利用率低,適居性不強
面對現代生活方式,建成遺產再利用率不高,適居性不強,如八廓街內民居,大多處于出租狀態;道路狹窄,停車困難,市政設施配置較低;以人為本,改善物質條件,保留立面,功能置換為商業;精細化,加入微設施,滿足公共生活需求,如街道家具[4]。
2.3 公眾參與意識較弱
建成遺產的保護者,不只是政府、文物部門的事情;作為人類的共同財富,需要公眾參與。文化社區對遺產的管理、宣傳與教育。以法國保護教育為例,夏約學校便是國家專門提供遺產保護教育的機構[3],以加強公民參與度,鼓勵居民小型投資,通過社交網絡植入小作坊;增加使用者的話語權,使之參與保護規劃[4]。
2.4 法規與管理不充分
遺產數量多,但法規與管理不充分,需要具體主管部門制定相應的法規、完善的保護體制,目前具體可行的保護措施有《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法國建有專門的建成保護區,有遺產建筑師保障法規、措施、實踐的運行[3],值得參考。
3 對 策
3.1 保護原則
①真實性,即保護遺產與其相應語境下的真實信息,如材料、工藝、做法,能分辨出具體年代;②原真性,即不改變原狀,現狀保存,如西安兵馬俑;恢復到一定時期,如甘丹寺,被大規模破壞后,在原址上恢復重建;③完整性,保護承載其價值的本體與周圍環境。
保護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①在本體上,保護的最小干預原則,進行預防性保護、微更新、微改造;建筑遺產修舊如舊,修新如新,如意大利的遺產保護只加固,不改造更新與活化;②在環境上,城市與山水格局的對話,建筑與開敞空間的關系,歷史街區整體保護如街道、廣場、古樹水系、空間序列、視線保護、輪廓線、周圍環境中自然與人文要素等;③在文化上,文化遺產作為城市物質與精神財富,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資源,體現城市特色,是城市名片與身份,具有歷史與人文特征的空間,都需要保護;④在社會上,如拉薩傳統村落,作為藏族在河谷平原地帶,以農牧生活方式為主,民居圍繞寺廟形成空間結構,每個河谷村落的文化略有區別,河谷內具有相似性。村落空間要有活力,要適應現代生活需求,必然要經歷新陳代謝。
3.2 技術策略概述
保護策略一般有:①保養維護與監測,如壁畫的退化、石刻的風化,對其溫度、濕度及可見光的監測等;②加固,如采取可逆形式對其墻柱結構體系,采取長期性或臨時性加固;③修繕,現狀整修如完善結構,去除無價值的桿件;重點修復如落架大修,結構解體重構,對文物損害較大,應保留各時期修改痕跡;④保護性設施建設,如在歷史保護單位外圍建玻璃房子,搭建保護棚罩;遷建,如埃及神廟由于水位上漲,將石刻切割、重組,整體沿山坡上移幾十米;⑤環境整治,對周圍臟亂差的環境整治,不應違背當地歷史文化與自然景觀,如建筑風貌,采用鄉土植被。
3.2.1 建筑遺產
在尺度上,延續城市肌理、織補空間;劃定紫線,原址原地;在構造上,有藏式斗拱由托木、弓木構成,但不同于漢式斗拱中斗升昂枋的做法;在材料上,采用阿嘎土、毛石、木材等原材料;在顏色與裝飾上,采用白色墻、黑框,寺廟有喇嘛紅、黃色等,如采用蓮花圖案裝飾,寺廟內有佛像壁畫等。
3.2.2 景觀遺產
歷史園林是因植被延續,使之成為活的古跡。西藏可分為莊園、宗堡、寺廟、行宮等園林類型。在選址上,除了考慮適合植被生長的自然環境外,其與不同類型的歷史建筑組合,形成不同類型的園林;植被種類多樣如莊園、宗堡、寺廟、樓閣、橋亭;在疊山理水上,較為粗獷;在園林意境與文脈上的保護。
3.2.3 城市遺產
保護層次可分為歷史保護單位、歷史街區、歷史文化名城。漸更新、分級保護。西藏城鎮中一般由寺廟與宗山、宮堡形成多核心空間結構,如拉薩以布達拉宮與大昭寺為中心,日喀則以扎什倫布寺與宗山為中心。在城鄉規劃里劃分三區三線,三區即農業區、生態區、城鎮區,三線即農田紅線、生態紅線、城鎮建設用地紅線。對于歷史村落,提高公共空間品質、活化空間,如對祭祀空間、民俗節慶活動空間,日常活動空間及基礎設施附屬空間等開發利用,使其社區化。
3.3 二次開發利用、參與式設計
利用方式:①科學研究價值,如對各個時期的史料收集與整理,形成演變路徑,以史為鏡可知興衰;增強韌性、恢復力;②展示、教育、VR模擬復原,如門孜康藏藥展示,莊園愛國主義教育,舊遺址如圓明園的數字模擬VR復原;③功能置換,植入新功能,如在最小破壞的前提下,采用可逆、可拆卸設施,賦予歷史保護單位以圖書館、博物館、學校等功能。公眾參與設計,如倡導式規劃。
3.4 文化視角下的保護與傳承
從文化傳承角度來看,保護即減少自然與人為因素造成破壞;修復即補缺,再生即再利用,如新業態、建筑觸媒[1]。從建筑類型學中尋找原型,一切原創源于原型,運用后現代主義中的裝飾、隱喻、文脈等理論,進行提取、轉化與創新原型[5]。在歷史環境中避免大拆大建,進行有機更新,保留城市集體記憶,如我國城市同心圓的形構、中軸線、曼陀羅空間[5]。其他方面如遺產廊道、文化景觀中文化的傳承,旅游開發,遺產管理,可以改善空間質量,激發空間活力。
3.5 國際憲章與管理
1964年《威尼斯憲章》中提到,古跡的維護要保存其周圍環境;1981年《佛羅倫薩憲章》主要是關于歷史園林保存憲章;1987年《華盛頓憲章》中提到保存歷史城鎮中的真實性,建筑由尺度、規模、式樣、構造、材料、顏色與裝飾決定,城鎮與周圍自然及人造環境的關系;1990年《考古遺產保護與經營憲章》是關于考古遺產立法的章程[2]。
4 結 語
文化遺產具有多樣性與真實性,應尊重其他文化,對真實性的考察,放在特定文化語境與演變時期。建成遺產營造了歷史環境,保留了城市基因與記憶,有助于文化的傳承與利用。
[ID:0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