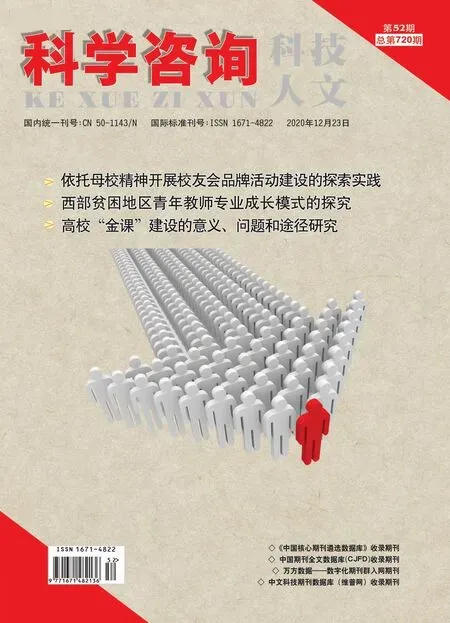基于大數據的互聯網金融征信應用研究
王迎龍 廖 寧 王德政
(重慶工程學院 重慶 400056)
互聯網金融(ITFIN)是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實現資金融通、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對整個互聯網經濟有重要作用,由于互聯網金融對數據的數量、質量有高要求,隨著大數據的應運而生,大數據應用于互聯網金融也勢在必行。
一、大數據應用于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意義
(一)是促進互聯網金融大數據廣泛應用的重要舉措
國務院于2016年1月15日頒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提出“鼓勵金融機構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信息技術,打造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國內外各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機構都在探索大數據的應用,希望大數據可以給企業帶來技術上的突破,實現自動化、升級現有風險控制模型體系、探索基于場景化的消費金融市場、提升互聯網獲取客戶的能力,從而從根本上提升金融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互聯網金融大數據涉及的內容龐大和復雜,如客戶信息的描述、客戶行為的描述、客戶的征信、企業貸款風險等,這些數據的處理和應用面臨著許多技術難題,比如如何科學準確地評價客戶的征信,即如何建立征信模型,再如,如何構建貸款風控模型,降低貸款風險等,這些影響金融行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問題,在“互聯網+大數據”背景下,如何應用人工智能方法和技術尋找一種乃至多種解決方法,是互聯網金融大數據智能應用的研究重點和迫切需要,也是促進互聯網金融大數據智能化應用的重要舉措。
(二)是提高互聯網金融機構風控水平的現實需要
大數據技術通過采集更全面、更及時、更真實的數據,快速找出不同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挖掘數據背后的風險信息,幫助互聯網金融機構迅速準確地識別和監控風險,改善風險決策模式,提高風險管理效率。例如,美國的一家網貸公司采用大數據技術,實時搜集網店店主的銷售、顧客流量、商品評價、物流、店主在Facebook 及Twitter等社交平臺上與客戶互動的信息,通過各類信息的交叉驗證分析,在數分鐘內即可評估出店主的征信風險水平,并計算出合適的貸款額度和利率,快速實現放貸。通過將互聯網各個角度的信息轉化為個體的征信信息,這家網貸公司實現了傳統金融機構一般不愿涉足的小微網店貸款業務,這得益于大數據技術迅速采集和處理多渠道、多結構數據的能力。
互聯網金融機構為了提高風險管控水平,必須做好貸后管理,實時跟進,采用平臺跟蹤為主、人工管理為輔的方式,借助征信平臺對小微企業的經營狀況進行跟蹤和監控,并由小微企業定期向征信平臺反饋企業財務數據和項目投資進度與收益的數據,征信平臺可按照設定好的模型對企業現狀進行評估,給出階段性的評估結果及該時段小微企業的違約概率,將貸款違約損失降到最低。如果階段性評估結果顯示異常,違約概率增髙,則需要工作人員進行實地調查和催收,及時切斷下一階段貸款的發放,做好風險防范工作。為避免小微企業上報征信平臺的數據不夠真實,互聯網金融機構也可派人對小微企業進行定期抽查,詳細了解企業的真實情況,確保風險可控、收益可觀。
(三)是創新互聯網金融征信評價機制的客觀要求
小微企業的征信評價問題一直是互聯網金融機構授信業務的難題之一。目前,我國大多數互聯網金融機構尚未建立小微企業專用征信評價機制。小微企業征信評級難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完備導致的銀企信息不對稱,而在互聯網大數據迅速發展的今天,這一難題有望破冰。依托互聯網數據挖掘技術和云計算功能,互聯網金融機構不僅可了解小微企業在金融領域的投融資征信,還可搜集到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社會征信、產銷上下游公司、物流公司與其在互聯網上進行交易、轉賬等經營活動中留下的信息碎片,以及小微企業在水電氣等部門的繳費記錄。互聯網技術的應用無法解決小微企業“軟信息”采集的問題,但是互聯網資源的最大特點在于“大”,通過大數據技術對龐大、細碎甚至毫無關聯的信息碎片進行分析,小微企業的征信狀況將更加真實、可視的特點呈現出來,從而得到更加客觀、準確的征信評價[1]。
互聯網金融機構創新小微企業征信評價機制,可在很大程度上扭轉其對小微企業的信息弱勢,緩解銀企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且征信評價結果可與隨后的授信準入、授信定價進行一體化對接,更好地實現前后授信管理一致,降低授信風險,同時方便貸后監督營理。因此,新形勢下創新數據挖掘與授信評價機制是互聯網金融機構授信管理的客觀要求。
二、互聯網金融征信的國內外現狀
互聯網金融征信在我國尚處于發展階段,是一個新型的行業,業務發展不完善,經驗積累較少。我國整個征信行業都以中國人民銀行的征信中心為主導地位,其他征信機構沒有得到過多的重視。目前,我國建立的基礎征信體系的系統內大約覆蓋了2000多萬家企業和9億人口,為700多家金融機構提供個人和企業的征信記錄。從征信業使用的數據上來看,我國征信機構更偏向于銀行的貸款記錄、個人征信卡還款和違約記錄、房貸以及其他貸款信息。這些信息大都來自線下收集,線上信息處于空白狀態。基于這種情況,2015年1月,央行發布了報告正式允許民間機構進入征信領域,補充我國征信業的不足[2]。
目前,在互聯網金融征信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阿里巴巴的芝麻征信系統,美國的Zest Finance大數據征信系統。
(一)阿里金融的芝麻征信
芝麻征信是大數據征信進入市場的一個應用,證明我國市場正逐漸接受大數據征信。2015年1月5日,央行發布了公告,允許8家機構進入征信領域進行個人征信業務,這意味著個人征信系統有望向商業機構開放,騰訊征信、阿里巴巴的芝麻征信位列其中。芝麻征信是螞蟻金服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征信管理和征信評級機構,依托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平臺的用戶數據的積累,依據各方各面的公共數據信息,運用云計算以及大數據技術客觀的給個人的征信情況進行評分。并通過與其他服務的合作,讓每個人都能體驗到征信帶來的價值。
芝麻征信分是芝麻征信根據得到的海量數據,對其進行分析、處理、綜合評估得到的一個具體的分數值。芝麻征信通過5個維度來進行考察,包括用戶征信歷史、履約能力、身份特質、行為偏好和人脈關系。集合過往的違約記錄、資產信息、真實的學習和職業經歷、購物繳費等活動偏好和人際交往中影響力等數據進行評估。這些征信評估可以幫助互聯網金融機構對用戶的還款意愿和是否具有還款能力得出結論,從而為客戶提供現金分期、快速授信等服務。本質上來說,芝麻征信就是一套征信系統,它的數據來源主要分三個方面:一是網絡平臺、金融機構、社交網絡等對外公布的信息;二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電商以及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的支付記錄;三是政府內部或者金融機構內部存儲的用戶的私人數據。芝麻征信通過大數據模型將通過以上方式得到的信息進行推演計算,以此作為征信評級的依據。芝麻征信可以應用于征信卡還款、網購、理財、轉賬、水電煤繳費,在芝麻征信分達到一定數值,還可以進行租車、租房、婚戀以及簽證等多種服務,租車、租房、住酒店可不用交押金,辦理簽證時不用再辦存款證明等。這種個人評級系統完善了我國的征信體系,提高了風險控制的效率[3]。
(二)Zest Finance的大數據征信系統
Zest Finance,原名Zest Cash,2009年成立于洛杉磯,是美國一家新興的創新型科技金融公司,Zest Finance剛創立便受到了互聯網金融圈和投資人的廣泛關注。
Zest Finance由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組成研發團隊,成立初期的服務對象是美國傳統金融征信風險評估系統無法覆蓋的人群。美國的基礎征信體系可以覆蓋的人口約占總人口數量的85%,因此,剩余的15%國民沒有征信評分而被銀行排除在外,由于無法獲得基本信貸需求,對于貸款的需求只能通過民間借貸或者高利貸來完成。
Zest Finance評估方式中最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假定每一個無征信的人都是“好人”,通過挖掘出他們在互聯網上的征信信息,證明信息不完整的人的真正的征信情況,幫助他們享受正常的信貸服務,通過Zest Cash平臺對其進行放貸服務。后來Zest Finance利用大數據技術重新塑造借貸審核流程,為在傳統金融中難以獲得征信的群體,提供征信評估服務,降低貸款成本。
與傳統金融相比,Zest Finance的最大的優勢在于強大的數據挖掘能力和模型開發能力。Zest Finance認為,消費者的征信記錄和征信狀況聯系是緊密的,但是征信記錄與征信狀況不是完全一一對應的關系,除了銀行給出的信貸數據,消費者還會有其他信息和行為關聯到征信狀況,哪怕之間的聯系較弱,也可以間接的比對出個人的征信情況。在Zest Finance的大數據系統中,不僅包括傳統信貸信息,還包括消費者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愿。通過多維度信息的搜集處理,實現對一個人的全方位考察。
Zest Finance在業務處理方面的效率提高了近90%,Zest Finance的模型在風險控制方面的性能提高了40%。Zest Finance希望可以把在征信貸款上取得的優勢推廣到其他應用領域,如為汽車金融,醫療服務,學生貸款等提供新的征信評分系統。
三、當前互聯網金融征信技術研究存在的不足
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小微企業,面向小微企業的互聯網金融征信大數據技術在我國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依然存在不少的問題,集中體現在:
(一)征信數據覆蓋不充分
我國大多數居民在征信評估方面的意識不強,對應的征信體系設計也不充分,加上互聯網金融本身具有強烈的民營資本色彩,抵御風險和償債能力相對較弱,在征信方面做得相較于各大銀行不夠完善,而且對于征信模型以及具體評分標準方面沒有完全統一。互聯網金融機構在產品運營過程中離不開征信系統的處理,征信系統可以在交易的各個環節比如貸款的貸前評估,貸中記錄,貸后監管起到重要作用,而征信系統的關鍵是用戶數據。按照征信系統的原理,數據越全面,征信評估結果越準確。互聯網個人征信系統應該考慮數據涵蓋傳統的征信數據、財務數據、社交數據、經營數據等[4]。
目前,互聯網金融機構建立的內部征信系統,基本沿用了各自的產品方向構建個人征信系統;如阿里小貸積累了包括信貸額度、違約記錄,同時借助阿里旗下網店、阿里云等數據信息進行征信評估審核;P2P行業代表人人貸借助前端銷售+后端審核模式,其核心還是傳統征信評估模式,其內部審核系統數據還是主要來源于貸款方的自己提供與線下確認以及第三方合作。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互聯網金融機構風險控制的缺陷在于數據的數量級別低和領域區間性太強。基本上單一企業單一領域數據搭建征信系統。
(二)大數據模型的可信賴性有待提高
征信數據模型的準確性建立在海量數據處理的基礎上,同時需要不斷的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模型參數和維度。由于互聯網金融征信系統應用時間短、數據少、經驗缺,目前的大數據征信模型大都基于規則制定,其中征信規則占有很大的比例,未能完全發揮大數據的優勢特點。因此,基于大數據的互聯網金融征信風險管控的核心不在于數據本身,而在于通過足量的數據分析得到的風險管控模型。要盡量獲取不同層面、不同領域、不同系統的征信數據,只有不斷納入足夠多的變量,在此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和建模,得到的互聯網金融征信風險管控模型才具有完備性和充分性,才能真正提高互聯網金融征信風險管控質量和水平,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種騙貸等風險事故的發生[5]。
(三)基礎征信數據整合難度大
隨著互聯網帶來的廣泛網絡化潮流,政府職能部門開始逐步信息化,同時強化數據共享,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數據整合程度但仍不能滿足大數據征信需要。互聯網金融機構缺乏可靠的政府機構作為可信的征信收集渠道,與傳統銀行或股份制銀行競爭,處于劣勢,互聯網金融機構只能從各商業銀行歷史征信數據里進行簡單的匯集整理,大量的個人征信報告原始數據仍然分布在各個司法、工商、稅務、公用事業單位等部門,政府的自來水公司、電力部門、煤氣公司為代表的基礎信息,以及個人的檔案、戶籍、司法系統、社保等系統尚未完全聯網互通,社會基礎征信信息相對缺乏。
(四)線上數據線下確認模式成本高
在央行不開放征信系統的條件下,互聯網金融機構只能自行尋求風險控制方案,較為常見的模式就是線上上傳數據、線下確認。由于借貸方的數據自行上傳,沒有第三方渠道支持,互聯網金融機構只能在線下進一步確認真偽:普通的信息通過電話或者提供的親友電話確認。涉及資產信息甚至要去住址尋訪確認,這些專門安排的人員,通過網絡、電話,甚至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到達借款人位置進行數據確認,勢必加大互聯網金融機構獲取準確征信數據的成本和痛苦。
(五)失信行為的懲戒制度不健全
我國對不誠實交易的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處罰力度不夠,導致借款人違約成本較低,市場欺詐、合同違約和債務違約等現象層出不窮,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對于社會征信體系建設不完善,監管力度不強,針對互聯網金融的交易未能與時俱進,推出適用于當前經濟發展的管理條例[6]。
(六)數據平臺標準未能統一
目前,我國對征信的征信信息平臺沒有統一的規定,僅由民間機構對數據進行定義無法實現長遠的發展。由于互聯網金融平臺未能接入到全國統一的征信系統,所以無法獲得核心的征信數據,使得其征信評價結果的準確性有待商榷。其次,不同的金融平臺的業務操作規范不同、授信標準不同、信息內容相對分散,導致征信數據形態各異,很難形成統一的數據標準,無法實現行業內數據共享,難以指定標準化的規范,現有的征信信息系統也未能覆蓋整個社會,嚴重制約大數據的信息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