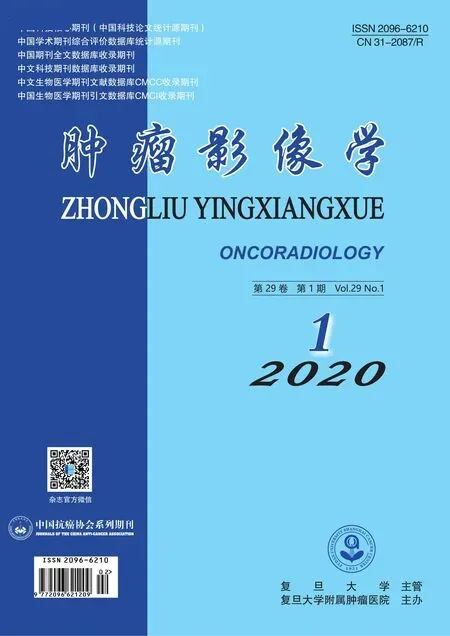三維超聲在子宮內膜癌中的應用現狀
于俊瑾,吳清芹,孔凡斌
1.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婦產科,上海 200082;
2.臨沂羅莊中心醫院藥劑科,山東 臨沂 276017;
3.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超聲科,上海 200082
子宮內膜癌為婦科常見惡性腫瘤之一,隨著子宮內膜厚度的增加,發生子宮內膜癌的風險升高[1]。對于出現異常子宮出血的女性,如果沒有子宮內膜活檢的設備,利用超聲檢查可以作出初步診斷[2]。對于病理學檢查證實為子宮內膜癌的患者,術前評估子宮肌層浸潤深度以及宮頸是否累及至關重要,這與制定手術方案息息相關。目前二維超聲在臨床上應用廣泛,隨著技術的發展,三維超聲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子宮內膜癌的診斷與評估。
1 二維超聲在子宮內膜癌診斷中的應用現狀
超聲作為無創的檢查技術,廣泛應用于常規婦科體檢或不規則陰道流血女性的初步檢查,Patel等[3]對絕經后陰道流血患者的研究表明,病理學檢查證實為良性或生理性子宮內膜病變患者的子宮內膜厚度,與子宮內膜息肉、子宮內膜增生及子宮內膜癌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但經陰道超聲檢測的子宮內膜厚度,預測絕經后陰道流血婦女罹患子宮內膜癌的價值有限[3-4]。對于無癥狀患者,Yasa等[5]的回顧性隊列研究表明,子宮內膜厚度不能預測是否患癌,對無癥狀婦女的診斷價值較低,但因其假陰性率低,可用于排除有危險因素的無癥狀絕經后婦女的癌前病變或惡性腫瘤。
Epstein等[6]應用國際子宮內膜癌分析術語,描述子宮內膜癌的聲像圖特征與腫瘤分期、分級及組織學類型的關系,該前瞻性研究表明,使用國際子宮內膜癌分析術語描述的超聲形態學特征(子宮內膜厚度、腫瘤大小、回聲性質、內膜肌層交界是否規則、彩色血流評分、血管的起源及分支等)與腫瘤的分級和分期有關,并且在高危內膜癌和低危內膜癌之間也有差異,但對于子宮內膜灰階超聲形態學和彩色多普勒血管化的輔助評估,以及對子宮肌層和子宮頸間質浸潤的評估,能否提高高危子宮內膜癌的診斷水平仍有待觀察。
2 三維超聲在子宮內膜癌診斷中的應用
2.1 三維能量多普勒超聲
血管化指數(vascularization index,VI)、血流指數(flow index,FI)、血管血流指數(vascular flow index,VFI)在評估子宮內膜良惡性病變中得到了應用。三維能量多普勒超聲可用于評估子宮內膜的多種形態和血管參數,可利用虛擬器官計算機輔助分析軟件測量子宮內膜容積、VI、FI及VFI。Pandey等[7]的研究發現,惡性子宮內膜病變患者的子宮內膜容積、VI、FI及VFI數值更大。其中VI和VFI對判定良惡性的潛力更大;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則顯示,只有VFI為顯著性變量,經過調整年齡和絕經狀態后,表現出與惡性腫瘤相關。其對血管形態的研究則顯示,大多數惡性患者表現為血管多灶起源和廣泛分布的特征。
李天剛等[8]的研究發現,子宮內膜癌患者的三維能量多普勒超聲圖像上有較明顯的血流信號,其血流參數(VI、FI、VFI)值均高于良性病變組、月經紊亂組和絕經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三維能量多普勒超聲能夠直觀地顯示子宮內膜血管的走行和分布,可以將內膜血管進行量化,能有效地鑒別子宮內膜癌、內膜良性病變和正常內膜,對早期檢出子宮內膜癌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
Dueholm等[9]的研究發現,子宮內膜厚度、子宮內膜容積、VI、FI和VFI均與癌癥有明顯的相關性,但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中,VI、VFI或FI的應用并不能提高診斷效率。
2.2 三維超聲在評估子宮內膜癌肌層浸潤深度和宮頸間質浸潤中的應用
2.2.1 三維容積對比成像技術(three-dimensional volume contrast imaging,3D-VCI)
三維超聲能夠獲取子宮體和子宮頸的超聲容積數據集,3D-VCI則是一種將容積數據集的1~10 mm切片投影到二維屏幕上的技術,利用此技術可以提高組織分界,提高診斷圖像分辨率[10]。Green等[11]比較了經陰道二維超聲與3D-VCI在子宮內膜癌診斷中的應用價值,結果顯示,經陰道二維超聲與3D-VCI診斷肌層浸潤一致性的中位數為76%(64%~93%),診斷宮頸間質浸潤一致性的中位數為88%(79%~97%);經陰道二維超聲的診斷信度優于3D-VCI(對于肌層浸潤Fliss kappa為0.41vs0.31,對于宮頸間質浸潤為0.55vs0.45)。對于診斷深部子宮肌層浸潤,經陰道二維超聲的準確率為76%(59%~84%),3D-VCI的診斷準確率為69%(52%~83%);對于診斷宮頸間質浸潤,經陰道二維超聲和3D-VCI的準確率分別為88%(81%~93%)和86%(72%~95%)。總之,相比于3D-VCI,經陰道二維超聲在可靠率和診斷準確率方面均較優越,至少在離線評估子宮內膜癌患者的子宮肌層浸潤和宮頸間質浸潤中是如此。
Jantarasaengaram等[10]的研究則發現,3D-VCI對肌層侵犯(淺表或深部)的診斷準確率為92.5%,在預測深部肌層浸潤時,3D-VCI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100.0%、89.7%、78.6%和100.0%。3D-VCI對宮頸受累的診斷準確率為90.0%,預測宮頸受累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100.0%、86.2%、73.3%和100.0%。其研究表明經陰道3D-VCI可以合理準確地預測子宮內膜癌患者子宮肌層浸潤深度和宮頸受累程度,為指導個性化治療方案提供有用的術前信息。
2.2.2 多平面成像與最小無瘤距離
三維超聲技術能夠同時顯示3個相互垂直的切面,通過在X、Y及Z軸上的移動對內膜和子宮壁情況予以多層次、多角度觀察[12],從而對子宮肌層-內膜分界提供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評估,加之彩色多普勒超聲對瘤內血流信號的評估,有助于明確腫瘤是否擴散至肌層或宮頸[13]。曹春巖等[14]通過三維超聲多平面成像對子宮內膜癌的肌層浸潤情況進行診斷,發現三維超聲多平面成像法診斷淺肌層浸潤的準確率較高,和二維超聲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然而,在深肌層浸潤方面,差異不明顯。其同時利用三維超聲技術計算腫瘤體積和子宮體積,發現深肌層浸潤的腫瘤體積明顯大于淺肌層浸潤的腫瘤體積。該研究表明,可以通過三維超聲對淺肌層浸潤進行診斷,用于臨床實踐,且腫瘤體積可作為肌層浸潤深度的診斷依據之一。
Ergenoglu等[15]通過三維超聲的不同平面測量腫瘤距離漿膜面的最小無瘤距離,并與病理測量的最小無瘤距離以及肌層浸潤結果作比較,結果發現,三維超聲測量的最小無瘤距離與組織學測量的最小無瘤距離呈正相關(r=0.474,P=0.001),判斷超聲測量的子宮內膜癌深肌層浸潤的最小無瘤距離最佳截斷值為9 mm(靈敏度89%,特異度61%,陽性預測值36%,陰性預測值96%)。
2.2.3 與磁共振成像的比較
一項納入了8項研究的Meta分析[16]表明,對于評估子宮內膜癌的深肌層浸潤,磁共振成像和經陰道超聲的特異度都比較低,磁共振成像的靈敏度高于經陰道超聲,但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Yildirim等[17]的研究表明,對于子宮內膜癌的深肌層、子宮下段和(或)宮頸的浸潤,三維超聲比磁共振成像具有更高的靈敏度、特異度、陰性預測值、陽性預測值和準確率;且兩者結合并不能提高診斷的準確率,故不推薦同時使用兩種檢查。
Deng等[18]利用擴散加權成像測量腫瘤區與癌周區(癌變內膜周圍5 mm的區域)的表觀擴散系數,研究表明,淺肌層浸潤與深肌層浸潤的患者癌變區表觀擴散系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淺肌層浸潤的腫瘤與深肌層浸潤的腫瘤癌周區表觀擴散系數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可提高術前磁共振對子宮內膜癌的評估效果。Rodríguez-Trujillo等[13]的研究則發現,在評估內膜癌子宮肌層浸潤深度方面,三維超聲(靈敏度、特異度和準確率分別為77%、83%和81%)和擴散加權成像(靈敏度、特異度和準確率分別為69%、86%和81%)有相似的有效性,結合兩者可提高診斷性能(靈敏度、特異度和準確率分別為87%、93%和91%)。擴散加權成像不僅可以評估子宮肌層的侵犯,還可以評估腫瘤在骨盆以外的轉移,可用于對可疑轉移淋巴結的識別。結合三維超聲與擴散加權成像,有利于子宮內膜癌患者術前的全面評估。
2.2.4 超聲醫師在子宮內膜癌肌層及宮頸間質浸潤評估中的作用
一項關于經陰道超聲評估子宮內膜癌肌層及宮頸浸潤的可重復性研究[19]表明,超聲醫師和婦科臨床醫師在深肌層浸潤的評估上無明顯差異,但超聲醫師在診斷宮頸間質浸潤的靈敏度、特異度及與組織病理學的一致性方面均優于婦科臨床醫師,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超聲醫師對子宮肌層浸潤深度的主觀評判方式是通過確定子宮肌層-內膜交界不清晰的點,將此處其認為的無瘤距離與正常的肌層厚度相比較,如果相差明顯,則認為達到或超過50%肌層浸潤;如果肌層厚度相似,則認為小于50%肌層浸潤。相關研究[15,20]顯示,與多種經陰道/直腸(二維/三維)超聲的客觀評價指標或模型相比較,超聲醫師對肌層浸潤深度的主觀評價是最佳的。
三維超聲作為一項經濟、簡單、無創的檢查技術,對于子宮內膜良惡性病變的診斷,以及子宮內膜癌患者肌層浸潤深度及宮頸浸潤與否的評估有一定意義,可為術前制定治療方案提供指導,而有經驗的超聲醫師可提高診斷性能。相比于二維超聲,三維超聲使子宮內膜癌肌層浸潤深度及宮頸浸潤與否的評估方法多樣化;三維超聲與磁共振成像聯合應用能否夠提高肌層浸潤、宮頸浸潤診斷的準確率仍存在爭議,但磁共振成像可提供對淋巴轉移或遠處轉移的評估,兩者結合有利于全面的術前評估。也有學者將其他的超聲技術如凝膠灌注超聲[9]、實時彈性超聲成像[21-22]等應用至子宮內膜癌的評估中,相比這些技術,三維超聲的診斷性能是否最優也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