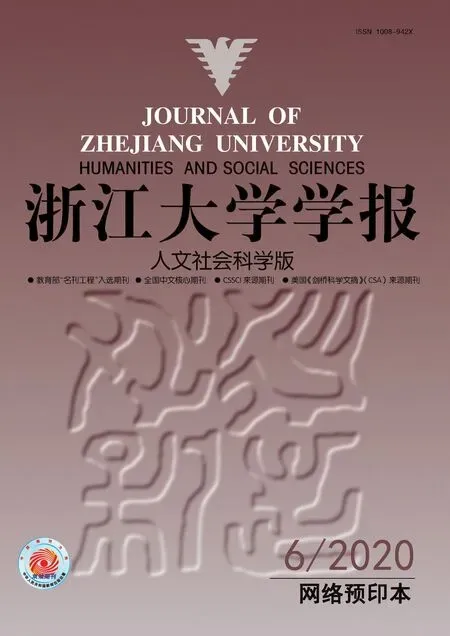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社會形式
——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核心概念考辨
劉召峰
(浙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歷來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們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由于對社會形態的內涵、劃分標準等問題的理解有差別,我國學者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有著曠日持久的爭論。產生爭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社會形式”等核心概念的理解存在比較大的分歧。鑒于此,本文將細致考辨這些核心概念,以便為更加深入地研究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奠定堅實的文本基礎。
一、 馬克思的社會觀與“社會形態”概念的創制
討論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首先要考察馬克思是如何理解社會的,要追問馬克思為何要創制“社會形態”這一概念。
馬克思把社會理解為人的活動的產物,并在關系中進行把握。我們要從人的感性活動(感性勞動)、從商業和工業對自然的改造的角度,來理解現存的感性世界,從而把人周圍的感性世界看作人的活動的產物[1]529。人的活動是在關系中進行的,社會也需要在關系中理解:“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2]221所以,馬克思把社會理解為“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1]604。
由多種要素有機聯系而構成的社會機體,又可劃分為多個層次,進行層層遞進的剖析:宗教異化根源于世俗異化;經濟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591;而在經濟活動中,生產是處于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環節,它決定交換、分配、消費[2]40;對于生產,不僅要考察生產什么(生產的物質內容),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怎樣生產(生產方式、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3]210[4]924。
社會機體是經常處于變化中的[5]12-13,社會的變遷會呈現階段性特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論述了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現代的所有制等)[1]521-523,587,明確表達了社會發展要分階段考察的思想。馬克思需要創制一個新的概念,用以標示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社會形態”就是這樣的新概念。
在1851年底開始撰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使用了“社會形態”概念:“新的社會形態(Die neue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3]471研究者們通常認為這是馬克思第一次使用“社會形態”概念(1)需要說明的是,概念的創制與思想的起源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論述了幾種所有制形式,這可以視為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雛形。參見[德]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523頁。。不過,我國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馬克思早在1847年寫作的《哲學的貧困》中就使用了這一概念[6]。其文獻依據是《哲學的貧困》中的這樣一段話:“在宗法制度、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定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后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至于作坊內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會形態中是很不發達的。”[7]165-166需要說明的是,《哲學的貧困》原文為法文,上述引文中“社會形態”的法文原文是formes de la société,其德文譯文是Gesellschaftsform[8]151,而不是Gesellschaftsformation。其實,就Gesellschaftsform一詞在馬克思著作中的使用而言,起始時間恐怕還要更早,在寫于1845年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有:“因此,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Gesellschaftsform)的。”[1]501Gesellschaftsform在中譯本中的對應詞通常是“社會形式”,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對應詞通常是“社會形態”。可能出于譯名統一的考慮,在2009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哲學的貧困》中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被改譯為:“至于工場內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會形式中是很不發達的。”[1]624這樣,我們就否定了那種認為馬克思早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就使用了“社會形態”概念的看法。
馬克思創制Gesellschaftsformation概念,可能與他閱讀英國農業化學家James Finlay Weir Johnston撰著的《農業化學與地質學講義》一書所受的思想啟發有關。1851年夏天,馬克思閱讀此書時做了不少摘錄[9]276-317。馬克思抄錄了Johnston論述沉積巖的分類的段落,注意到Johnston把formation視為比system(系)更小的地質層單位[9]292。日本學者大野節夫認為,我們可以推斷馬克思的Gesellschaftsformation是從地質學中的小單位formation或一般的地質系統(geological formation)那里引申出來的,因而,把Gesellschaftsformation譯為“社會層”比譯為“社會形態”更符合馬克思的原意[10]293。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一詞是由Gesellschaft(社會)與Formation(形態)兩個名詞合成的,它的含義是die 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社會的形態)。Gesellschaft是個陰性名詞(die Gesellschaft),其第二格是der Gesellschaft,將其置于被修飾的名詞die Formation之后,表示事物的所屬關系。為了更好地說明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構造原理,我們還可以舉“古代社會形態”的例子。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原文為法文)中,馬克思兩次使用“古代社會形態”(法文為la formation archa?que de la société或la formation archa?que des sociétés;德文為die archaische 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2)法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Ⅰ/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5, S.233, 236;德文譯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398, 403。[11]444,449。這一概念中,“古代”是對“形態”的時段限定,“社會”是對“形態”的內容限定,因而,它也可以譯為“社會的古代形態”。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在批判“三位一體的公式”時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einer bestimmten histor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3)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S.822。[4]922馬克思在此強調的是,資本不是物,而是具有歷史性特征的(不是永恒的)生產關系。如果把其中的Gesellschaftsformation改寫成die 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我們就能明白:Gesellschaft是對Formation在內容方面的限定,historischen(歷史性的,具有歷史性特征的)是對Formation在特征方面的限定,因而,中譯本中的“一定歷史社會形態”也可以替換為“具有歷史性特征的特定社會形態”。
除了“社會形態”,馬克思還使用了“歷史的形態”來標示人類歷史發展的階段性。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的第二稿中說:“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在地質的層系構造(法文為formations géologiques;德文為geologischen Formationen)中一樣,在歷史的形態(法文為formations historiques;德文為historischen Formationen)中,也有原生類型、次生類型、再次生類型等一系列的類型。”(4)法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Ⅰ/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5, S.229;德文譯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386。[12]581這里的“歷史的形態”與“地質的層系構造”相對,是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與地質構造的累積相類比的意義上來談的,它其實也就是社會的形態(die 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即社會形態(di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對馬克思社會形態概念的含義,我國學術界有多種不同的理解:(1)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不包括上層建筑);(2)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不包括生產力);(3)生產力、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上層建筑等全部社會要素的有機統一體。本文的考辨表明,馬克思創制Gesellschaftsformation(社會形態)概念,是為了標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說,不同發展階段的人類社會。既然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而且,生產力發展有階段性特征(比如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等),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有階段性更迭(比如原始公有制、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勞動制等),上層建筑也有過歷史變遷(比如中國古代國家經歷了邦國、王國、帝國這樣的階段和類型[13]8),那么,生產力、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上層建筑都理應在社會形態概念的涵蓋之下,也就是說,社會形態是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全部社會要素在內的、動態發展的統一體。有些學者之所以會對社會形態做狹義的理解(把生產力或上層建筑排除在社會形態之外),往往是因為他們混淆了“區分各種社會形態的主要標志”與“社會形態本身的涵蓋范圍”這兩個不同的問題。馬克思特別強調經濟形態是社會形態的基礎,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是區分經濟形態(從而區分社會形態)的主要標志,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否認生產力或上層建筑屬于一定發展階段的人類社會(社會形態)。
二、 “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翻譯與理解問題
在關于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討論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當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關于社會形態的兩句話了。我們先來回顧這兩句話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中譯文變遷,再來回應學界在理解“經濟的社會形態”時的爭論。
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的兩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的譯文分別是:“大體說來,亞洲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看成為社會經濟形態發展中的幾個演進時代。”[14]341“我的觀點是在于我把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一個自然歷史過程。”[14]430有意思的是,這里引述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經濟社會形態”兩個概念,其德文原文都是der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5)可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3,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16。[15]9。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1953年修訂版)中對上述第二句的譯文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從我的立場,是被理解為自然史上的一個過程。”[16]51963年修訂版的相關譯文又有改動:“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個自然史的過程。”[17]XI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第一版第13卷(收錄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第23卷(《資本論》第一卷)對這兩句話的譯文分別是:“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18]9“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19]121995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譯本的譯文有重要改動(把“社會經濟形態”改譯為“經濟的社會形態”):“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20]33“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20]101-102對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句話,2009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譯本除了把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的“古代的”改譯為“古希臘羅馬的”[3]592之外,沒有其他改動;至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那句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資本論》第一卷)則完全沿用了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譯文[5]1059。
通過以上回顧可知,譯文差異的重點在于,der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究竟是譯為“社會經濟形態”,還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其中涉及的核心問題是,“經濟”作為限定語的限定對象是“形態”還是“社會形態”。我國學者對“經濟的社會形態”概念的理解大體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第一種認為經濟是社會形態的內容限定(6)參見張亞芹、白津夫《亞細亞生產方式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載《學習與探索》1981年第1期,第121-126頁;段忠橋《重釋歷史唯物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頁。;第二種認為經濟是考察社會形態的視角(7)參見趙學清《“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本意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屬性》,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第14-19頁;趙家祥《五種社會形態劃分法和三種社會形態劃分法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載《觀察與思考》2015年第2期,第3-9頁;王靜《馬克思的社會形態范疇形成史及其當代意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頁。;第三種認為經濟是社會形態的特征定位(8)參見張一兵《社會歷史發展永遠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嗎?》,載《天府新論》1988年第1期,第33-35頁;余章寶《經濟的社會形態概念原相》,載《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第46-49頁;邵騰《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兩階段論探索》,載《學術月刊》2001年第10期,第24-30頁;張凌云《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片論——從“巴黎手稿”到“人類學筆記”》,載《學術研究》2008年第9期,第5-16頁;徐素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MEGA2視野下的文本、文獻、語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頁。。接下來,我們就來回應這一爭論。
首先,我們來看能否把經濟視為社會形態的內容限定。“經濟的社會形態”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德文原文都是der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15]9。der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是第二格名詞詞組,其第一格名詞詞組是die ?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也可以寫作die ?konomische 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其中,形容詞?konomisch(經濟的)與名詞Gesellschaft(社會)都是Formation的限定詞,因而,把die ?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譯為“經濟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經濟形態”都是可以的,而譯為“社會經濟形態”更好些,因為經濟比社會所限定的范圍更小。在馬克思親自修訂過的《資本論》第一卷的法文版序言中,就使用了la 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社會經濟形態)這一表述(9)可參見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頁。法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Ⅱ/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9, S.14。[21]19。由此可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就是“社會經濟形態”即“經濟形態”,“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說的都是經濟形態的演進。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直接使用經濟形態這一概念來指稱經濟的發展階段。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使用了“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法文為à cette formation économique;德文為jener ?konomischen Formation)”(10)法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Ⅰ/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5, S.116;德文譯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111。[12]466的表述。恩格斯在1894年寫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說:“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konomische Formation)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7]458-459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可否理解為考察社會形態的視角。應該說,馬克思確實曾經在這一意義上使用“經濟的社會形態”概念。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說:“把價值看做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做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die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11)參見[德]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頁。其中“經濟的社會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第一版中的譯文是“社會經濟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4頁)。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3,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231。馬克思的意思是: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在“榨取剩余勞動的形式”上有區別,正是這一區別才使其成為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從“榨取剩余勞動的形式”上區別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屬于從經濟的視角區分社會形態。馬克思的這段論述可以視為把經濟理解為考察社會形態的視角的直接文本依據。
最后,我們來評析把經濟看作社會形態的特征定位,認為在經濟的社會形態之外,還有非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觀點。持這一觀點的學者雖然也有分歧,但都認定共產主義社會是非經濟的社會形態。這些學者區分經濟的社會形態與非經濟的社會形態,意在提醒我們:有必要區分經濟的基礎地位與經濟的主導地位,經濟并非在一切社會發展階段都占據主導地位。筆者以為,這樣的提醒是必要的,馬克思也并不認為經濟在任何時代都起主要作用:“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5]100馬克思的意思是,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而不是經濟起著主要作用,但是,“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古代世界的政治生活、中世紀的宗教生活都建立在謀生(經濟生活)的基礎上,政治在古代世界的主要作用、天主教在中世紀的主要作用都有賴于從謀生的方式和方法這一經濟層面來說明,也就是說,經濟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紀也起著基礎性作用。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經濟的基礎性地位也依然存在——必然王國(物質生產領域)是自由王國(作為目的本身的人的發展)的基礎[4]928-929。倘若以經濟的基礎地位作為區分社會形態的標準,并以此來理解經濟的社會形態,那么,古代世界、中世紀、資產階級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都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倘若以經濟的主導地位作為區分社會形態的標準,并以此來理解經濟的社會形態,那么,古代世界、中世紀、共產主義社會都不是經濟的社會形態,資產階級社會才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總之,無論如何都達不到某些論者想要的理論結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屬于經濟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社會是非經濟的社會形態[22]。而且,把共產主義社會理解為非經濟的社會形態,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如下一段話相矛盾:“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einer h?hern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12)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S.784。[4]878其中“較高級的”指的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在馬克思本人的社會發展序列中,它就是共產主義的;如果把“經濟的”理解為社會形態的特征限定,那么,我們可以推知,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社會依然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其實,馬克思是在談論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地租、土地價格時說上面那番話的,其中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就是經濟形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就是共產主義的經濟形態。
邵騰先生還將經濟的社會形態與非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區分,跟馬克思自由王國與必然王國的區分相提并論,把它們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22]。筆者認為,這種理解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說:“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斗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4]928-929很明顯,在馬克思看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人都“必須與自然搏斗”,進行物質生產;必然王國、自由王國是并存的兩個王國/領域(即物質生產領域與作為目的本身的人的發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礎,這也就是說,物質生產的基礎性地位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依然存在。邵騰先生把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之間的共存關系錯誤地理解為后者將“歷史地”替代前者的歷史繼承關系了(13)當然,把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理解為前后相繼的兩個發展階段,并非邵騰先生首創。在《反杜林論》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都有“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這樣的說法,它用以指稱人類從被異己的力量統治到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歷史性進步(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565頁)。但恩格斯絕沒有從經濟的社會形態向非經濟的社會形態過渡的思想,也并沒有否認人在自由王國還要勞動。不過,與恩格斯“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這一提法有差別的是,馬克思認為,必然王國(物質生產領域)內也有自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可以把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未來社會的人也“必須與自然搏斗”,進行物質生產,因而,也要受必然的制約。。
基于上述辨析,我們可以得知,馬克思著作中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有兩種用法:第一,它是從經濟這一視角來看的社會形態;第二,它就是社會的經濟形態或經濟形態,它是社會形態的經濟方面或部分,因而,它與經濟基礎、經濟結構等屬于同一序列的概念,只不過它更加凸顯經濟的歷時演進特征(而非共時結構特征)。但是,不能把“經濟的”理解為社會形態的特征限定,認為除了經濟的社會形態,還有非經濟的社會形態。
三、 社會形態與社會形式
由以上的文本考辨可知,社會形態概念是馬克思仿照地質層概念,把社會(die Gesellschaft)與形態(die Formation)兩個名詞合成而創制的新概念,用于標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說,不同發展階段的人類社會。以社會形態的歷史演進來標示人類社會的階段性發展,這一思路蘊含著馬克思的“歷史性自覺”。
這種“歷史性自覺”并非始于社會形態概念的創制。在1846年12月28日給安年科夫的信中,馬克思就有了上述自覺:“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23]42-43“可見,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23]44在此,馬克思特別強調了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階段性,人們的生產方式、經濟關系都具有歷史暫時性。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更為明確地闡述了如下看法: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方式建立的相應的社會關系,以及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的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1]603。
上述“歷史性自覺”與馬克思明晰地區分物和一定的社會形式這一獨特思維方式有關。馬克思說:“機器不是經濟范疇,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經濟范疇一樣。現代運用機器一事是我們的現代經濟制度的關系之一,但是利用機器的方式和機器本身完全是兩碼事。”[23]46我們需要對機器本身與利用機器的方式進行明晰的區分,正如我們要嚴格地區分生產力與人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die Gesellschaftsform)”(14)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7,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S.452。[23]43一樣。而“缺乏歷史知識”的蒲魯東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生產力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形式必然隨著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經濟范疇只是這些現實關系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因而,蒲魯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范疇看作永恒的規律,而不是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用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23]47。馬克思批判了經濟學家們“奇怪的”論證方式: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1]612。
除了“社會形態”,馬克思還使用“社會形式(die Gesellschaftsform)”(15)有必要說明的是,與社會形態概念不同,社會形式這個概念并非馬克思創制的,蒲魯東就在《什么是財產》(又譯《什么是所有權》)一書中多次使用這個概念,其第5章第2部分第3節的標題是“第三種社會形式的定義:結論”。參見[法]蒲魯東《什么是所有權》,孫署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75、335、336、342、479頁;另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81頁的第71個編者注。指稱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三大社會形式”的論述[2]107-108就屬于這類情況。通過“最初的社會形式”“第二大形式”“第三個階段”等用語,我們就可以明了:“形式”就是“階段”,“社會形式”就是“社會發展階段”,也就是“社會形態”。
當然,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社會形式還有內涵異于社會形態的另一種用法:“像資本一樣,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也是歷史規定的社會形式(gesellschaftliche Formen);一個是勞動的社會形式,另一個是被壟斷的土地的社會形式。而且二者都是與資本相適應的、屬于同一個經濟的社會形態(?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形式。”(16)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S.824。[4]923在此,馬克思同時使用了社會形式和社會形態兩個不同的概念:雇傭勞動是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是土地的社會形式,它們都屬于資本主義這一經濟的社會形態。社會形態是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的意義上使用的,而勞動的社會形式、土地的社會形式中的社會形式是在形式規定性(die Formbestimmtheit)、經濟的形式規定性(die ?konomische Formbestimmtheit)、社會形式規定性(die gesellschaftliche Formbestimmtheit)(17)參見[德]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6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4、987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528頁。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4,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S.162, 167; 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S.833, 879; 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6-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5, S.372; 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Ⅱ/4.1,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115。意義上來使用的。形式規定性是人的活動(勞動)或物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獲得的(而非與生俱來的)、具有歷史暫時性的社會規定性(die gesellschaftliche Bestimmtheit)(18)德文原文參見Marx K. & Engels F., Marx/Engels: Werke, Band 26-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5, S.372。[24]400。
為什么內涵有異的社會形態與社會形式,馬克思也曾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呢?筆者以為,那是因為它們在本質上有相通之處:物、人的勞動在不同的社會關系(特別是生產關系)中獲得的特定社會形式,就是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形態)以及整個社會發展階段(社會形態)的標志。
以上,我們考辨了馬克思創制“社會形態”概念的來由,特別是這一概念的構造原理,探究了“經濟的社會形態”中的“經濟”作為限定語的限定對象及含義,剖析了社會形態與社會形式的異同,從而為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研究奠定了更為堅實的文本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