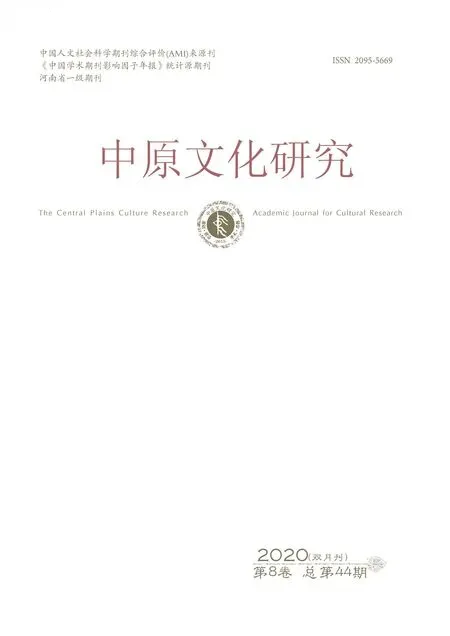宋代經筵制度探析
龔延明
宋代皇室在藩邸置講讀官,讓皇子從小接受教育。如某位皇子立為皇太子之后,即配置東宮官,其中有太子侍讀官、侍講官;在資善堂,由太子講讀官講學。一旦皇太子繼位,當了皇帝,需依“皇朝家法”[1]《崇儒》七之二五、二六,2898;[2]300,開經筵,接受經筵官的再教育。即按規定時間,聽經筵官講讀,這就是宋代的經筵制度①。經筵制度是皇帝接受經、史和寶訓(先帝謨訓)教育,提高自身治理國家能力和個人文化素養的重要途徑。
一、經筵制度之創設
皇帝召儒士至宮中講學,通稱為經筵,源于西漢。《古今源流至論》載:“自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于石渠,經筵之所始乎此。”[3]490《漢書·宣帝本紀》:“(甘露三年春正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4]272
經筵官侍讀,則始置于唐,稱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開元三年(715年),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乃以馬懷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通鑒》。至開元十三年(725年),置集賢院,有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于是有常職矣[3]491。是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②。唐代侍讀官,為帝王“師臣”,待遇崇高。玄宗時,馬懷素與褚無量同為侍讀,輪日值班禁林集賢殿書院,“肩輿以進”;或行在遠(皇帝在離宮別館),聽乘馬直達宮中,宮中每有宴見,宴罷,皇帝目送,以“師臣之禮”[5]102。
然唐末五代,天下大亂,經筵制度廢弛。至趙宋王朝建立,重文輕武,復經筵制度。宋初,并未專設給皇帝講經史的經筵官,但太祖、太宗朝開始請儒士講經。宋太祖始置講席,先后召宗正丞趙孚、處士王昭素至便殿講《周易》[6]454。據王明清《揮麈錄·前錄》載,開寶八年(975年),太祖所召處士王昭素,為王明清五世祖,在崇政殿說《易》,然后命官,至右拾遺,“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于此”[7]6。但未成為常制,繼而“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以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問。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每出經史,即召文仲讀之”[6]454;[8]卷二四,太宗興國八年十一月庚辰,559-560。
由上可見,太祖朝有崇政殿說書之名,太宗朝有侍讀之稱。但此兩者,皆臨時之稱,屬偶爾為之,非屬正式經筵官。真宗朝,始建立經筵制度,設置經筵官。
這里需要澄清的是,宋代經筵官中有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但都不屬于學士院的翰林學士之職,要注意區別。《宋史·職官志》所列學士院官有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知制誥、直學士院、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并不包括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崇政殿說書等。但由于《宋史》纂修者將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等直接置于學士院之后,又漏掉標示“經筵官”小目,易致讀者誤為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崇政殿說書等為學士院官[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3;[10]109。
但在北宋真宗朝與南宋孝宗朝,經筵官與翰林學士同在學士院輪宿值:“隆興初,上用真宗故事,輪講筵、學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兩員,以備宣引咨訪,往往賜酒留款。其后,以兩人難獨召,若同召則議論難盡,止命一員遞宿。自后,益遴其選。或國忌妨行香,若有故員少,及大暑,皆權免。間遇除授宣鎖,講筵官已入直,率聞命,蒼皇而出,至有不及伺候,從吏借馬于內諸司者。或偶值本院官直宿,就留鎖院。若大除拜,當有錫賜,則不系當日與否,往往特宣云(每直兩日,謂之頭直、末直)。”[11]302可見,雖經筵官輪宿學士院,但備咨訪而己。薦夜有除拜草制,經筵官“蒼皇而出”,仍須輪時召翰林學士入院。院吏得臨時借馬馳往學士家宣召鎖院草制。這說明,經筵官非屬學士院官。
二、宋代經筵職官
宋代復經筵制度,較為健全。其經筵官之設,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北宋前期經筵官
1.翰林侍讀
太祖朝,有崇政殿說書。太宗朝,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用著作郎呂文仲為侍讀,后遷為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12]82;[1]《職官》五七,3190。這是除授經筵官之始,然未有常制,講官隨意命名,待遇不高。
2.翰林侍讀學士
咸平二年(999年)七月丙午,始置,三員。以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并為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讀、兵部員外郎中呂文仲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1]《職官》六之五七,3190。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與翰林學士同。
3.翰林侍講學士
咸平二年七月丙午,始置,一員。以國子祭酒邢昞守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與翰林學士同[10]109。
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臺諫兼侍講:慶歷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長于講說,特召之。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3
先是,侍讀名秩未崇,真宗首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位遇大大提高,“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于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直官名,于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1]《職官》六之五七,3190;[8]卷四五,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957。“宣坐賜湯,其禮數甚優渥,雖執政大臣莫得與也”[13]10。
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秘閣,即值班辦公室設于秘閣內。故程俱《麟臺故事》,就將經筵講讀官歸屬三館秘閣中。但真宗朝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雖為專職經筵官,也有可以充外任帶職者。如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翰林侍講學士、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邢昞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知曹州[8]卷六六,真宗景德四年八月庚戌,1483。天禧二年(1018年)十二月,參知政事張知白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8]卷九二,真宗天禧二年十二月辛丑,2131。
4.崇政殿說書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丁亥創置崇政殿說書,四員,掌進讀者書史,講篤經義,備顧問應對,以資稍淺之庶官充。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國子監博士楊安國并充崇政殿說書。每日以兩人入侍講說[8]卷一一四,仁宗景祐元年正月丁亥,2662;[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5。
仁宗朝后又增講筵官至十四員。景祐四年(1037年)又設天章閣侍講四員,其中賈昌朝經以崇政殿說書兼天章閣侍講,品位比直龍圖閣[8]卷一二○,仁宗景祐四年三月甲午朔,2822。如王洙為天章閣侍講,專讀寶訓要言于邇英閣[9]卷二百九十四《王洙傳》,9814。嘉祐三年(1058年),侍讀官有十人,多為翰林學士相兼者;加上天章閣侍講、崇政殿說書,共十四人。歐陽修說:“侍讀之職,最為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14]1335至此,曾以經筵講官名官者,有翰林侍讀、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可由侍從官以上,從四品以上文臣充),及天章閣侍講、崇政殿說書(可由資淺者,即庶官正五品以下充)。
(二)元豐改制后的經筵官
宋神宗元豐改制,定經筵官編制。此后,除哲宗元祐間曾增“學士”之號外,至南宋皆遵依元豐改制不變。
1.侍讀
正七品,掌講讀經、史。以學士或侍從官(從四品以上職事官或寄祿官)以上有學術者充。
2.侍講
正七品,掌講讀經、史。以學士或侍從官以上(從四品以上職事官或寄祿官)有學術者充。元豐五年(1082年)五月癸未,通直郎、中書舍人(從四品職事官)陸佃兼侍講[8]卷三二六,神宗元豐五年五月癸未,7839。陸游《家世舊聞》亦載:“元豐中,侍經筵(按:指陸游祖父楚公陸佃)。”[15]231
3.崇政殿說書
正七品,掌講讀經、史。以秩卑資淺(庶官,則正五品以下寄祿官)有學術者充。徽宗朝,在末年一度改崇政殿說書為邇英殿說書。宣和六年(1124年)九月,以校書郎楊時為邇英殿說書,徽宗說:“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16]卷十四,徽宗宣和六年九月丙戌,977南宋復稱崇政殿說書。據《神宗正史·職官志》載:“崇政殿說書,從七品,掌講讀經、史。……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只日(按:為“單日”,下同)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1]《職官》六之五八,3192元豐改制后首位除授的崇政殿說書為蔡卞:“元豐五年五月癸未,起居舍人(從六品)蔡卞兼崇正殿說書。”[8]卷三二六,神宗元豐五年五月癸未,7839
總體來說,元豐改制對經筵官進行的改革,有兩個特點,一是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皆省去“翰林”“學士”之號,但稱侍讀、侍講;二是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多為兼職。
如《宋史·職官志》載:“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元祐六年,馮京兼侍讀充太乙宮使。”[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3崇政殿說書或有專職,如布衣程頤以薦而為崇政殿說書:“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宣徳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既上殿,以經筵命之。……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睹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朝官寄祿官階,正八品)、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圣朝之所宜為也!’”[8]卷三七三,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9029-9031
崇寧中,初除說書兩人,皆以隱逸起,蔡崈、呂瓘,仍遂其性,詔以方士服隨班入朝[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5。《鐵圍山叢談》載:“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寧中,初除二人,皆以隱逸起。蔡寶(按:作崈)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用,其學行修飭召。呂瓘者,亦以髙節文學有盛名,居弗仕,數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謁,入侍經筵焉。亦熙朝之盛舉也。’”[17]27
元祐七年(1002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1098年)又省去。哲宗即位初,定“講讀官職錢為三萬(三十貫)”。《宋會要輯稿》載:“元符元年二月十三日,三省言:‘裁定六曹寺監文字所狀,乞降指揮: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向去置與不置。’詔:‘元祐復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指揮更不施行。’”[1]《職官》六之五八,3192即經筵官仍依元豐之制,統稱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南宋經筵官依制,建炎元年(1127年)詔:“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講讀,充宮觀兼侍讀。”[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3
三、宋代經筵兼官
宋代經筵官,仁宗朝以后多以他官兼。這是由于經筵官是接近皇帝,給皇帝講課之人,要求嚴格,必須是學問好、有聲望、有地位的官員。同時,皇帝利用經筵講課,將其作為一條了解和咨詢的渠道,相對獨立于相權的臺諫官,就常成為經筵兼官。此外,經筵官又是權相暗箱操控、打探皇帝信息動態的難得孔道,因此專權的宰相,如秦檜就常通過除授言路官必兼經筵官的權術,使其親信成為經筵官。宋代臺諫官多兼經筵官,也反映出經筵官之除授,成為宋代皇權與相權明爭暗斗之地。
(一)臺諫官、兩省官兼侍讀、侍講
真宗朝之前,御史臺與諫院官例不兼經筵官,“蓋以宰執間侍經席同,避嫌也”[20]716。這是說,臺諫官身為皇帝監察百官的工具,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臺諫官充經筵官,若宰執侍講,經筵官其解經、史,聯系時政,或有所顧忌。此外,皇帝或欲咨詢政事、世事,經筵官當著宰執面,也未敢直言。
臺諫官兼經筵官,仁宗朝偶或有之。其盛行于南宋高宗朝,特別是秦檜專權時期。自慶歷以來,御史中丞多兼侍讀。左、右諫議大夫未有兼者,紹興十二年(1142)春,秦檜親信萬俟卨以御史中丞羅汝楫以諫議大夫始兼侍讀。自后每除言路必兼經筵官[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3。
臺諫官兼侍講。慶歷二年(1042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任經筵者,仁宗以昌朝長于講說特召之,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4。
元祐中,司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司馬光之賢,故特有是命。紹興五年(1135年),范沖以宗正卿、朱震以秘書少監并兼,蓋殊命也。乾道六年(1170年),張栻始以吏部員外郎兼。南宋后,庶官兼侍講者唯此三人。若紹興二十五(1155年)張扶以國子祭酒,隆興二年(1164年)王佐(狀元)以檢正,乾道七年(1171年)林機以宗正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張扶本以言路諫官兼說書,就升其秩,王佐時攝戶部;林機嘗為右史,且有舊例,故稍優之。
中興后,王賓為御史中丞,見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后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紹興十二年,則萬俟卨、羅汝楫。紹興二十五年,則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講。非臺丞(御史中丞)、諫長(左、右諫議大夫)而以侍講為稱,又自此始。[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4
(二)宮觀使兼侍讀、侍講
元豐八年(1085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元祐元年(1086年),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元祐六年(1091年),馮京兼侍讀充太一宮使,未幾,乞致仕,不允,仍免經筵進讀。中興以來,如朱勝非、張浚、謝克家、趙鼎、萬俟卨并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1163年),張燾以萬壽觀、湯思退以醴泉觀并侍讀。乾道五年(1169年),劉章(狀元)以佑神觀兼焉。
南宋高宗朝后,多以提舉宮觀官、醴泉觀使兼侍讀,處罷相之舊大臣(個別例外),理宗朝,更出現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經筵官侍讀雖存,但出現邊緣化趨勢,多用為加官,并不赴經筵。故《宋史·職官志·官品》與《慶元條法事類·官品雜壓》皆無“侍讀”,但有“侍講”“崇政殿說書”。如左相湯思退于紹興三十年(1160年)十二月罷相后,次年十月“湯思退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9]卷三二《高宗紀九》,604,實際上是赴閑而已。到理宗淳祐間,侍讀帶“醴泉觀使、奉朝請”,作為體貎大臣的加官而已,如:
(淳祐四年十二月)乙亥,鄭清之授少保,依舊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進封衛國公。[9]卷四三《理宗紀三》,831……(淳祐十年)三月癸未,趙葵辭相,以為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9]卷四三《理宗紀三》,842
(紹定六年)十月丁亥,寧宗、理宗權相史彌遠病重,致仕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仍奉朝請。乙未薨(按:乙未是農歷十月二十四日,即授史彌遠“侍讀”后八天即死,此亦可見權相史彌遠權力欲至死不衰,與秦檜如出一轍)。但這并非意味著南宋后期沒有赴經筵的侍讀官。如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乙巳,守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陳卓[16]2697。
宮觀兼侍講。國初、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侍讀。乾道七年,寶文待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虞允文奏曰:“胡銓早歲士節甚高,不宜令其遽去朝廷。”帝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故有是命。[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5
(三)臺諫官兼崇政殿說書
崇政殿說書,原無臺諫官兼任者。至秦檜獨相擅權時,紹興十七年(1157年)四月,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掌握朝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里。對此,南宋呂中《皇朝中興大事記》評論道:
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執政、侍從、臺諫皆用私人,則有以彌縫于外朝矣;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闖于內朝矣。獨經筵之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于是以(秦)熺兼侍讀,又以巫伋為說書,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講官之進說,而臣無復天子之臣矣。[18]卷一百五十六,紹興十有七年四月辛丑,2958
南宋奸相秦檜擅權,除授臺諫官必為親信,如勾龍如淵、萬俟卨、羅汝楫等,以鉗制輿論,同時臺諫官必兼經筵官,以此偵伺高宗動息。呂中對秦檜以親信為臺諫官與經筵官,其用心則作為自身固位、鉗制抗金輿論及駕馭高宗的工具,有過深刻的分析:“和議未成之前,以中丞如淵而擊異議之臣。又以右正言巫伋而使之入經筵,以伺上之支,欲竄諸賢,則使之露草而論其罪犯,欲斥去執政,則使之彈擊而補其處。而臺諫皆檜之私人。上親政之初(按: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宰相秦檜死,高宗始得親政),首重言官,增置言官,而陳俊卿、杜莘老之徒弟出,凜然有慶歷元祐之風,則臺諫之紀綱正矣!”[19]646
秦檜死后,臺諫官“遂罷兼(經筵官)”,因此孝宗朝經筵官,臺諫官兼者甚少,例如:
隆興元年四月,起居郎胡銓兼侍講,講《禮記》,右諫議大夫丁王大寶兼侍講,講《易》。……是月,司封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王十朋(狀元),除起居舍人、升侍讀。五月,權工部侍郎兼侍讀張闡除工部尚書兼侍讀。……六月,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醴泉觀使湯思退兼侍讀。……二年六月,起居郎胡銓兼侍講除兵部侍郎升侍讀。……八月,檢正諸房公事王佐(狀元)、殿中侍御史晁公武并兼侍講。[1]《職官》六之六一,3196
但寧宗慶元后,因皇帝皆由權相操控,秦檜的“套路”又復活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慶元后,臺丞(御史中丞)、諫長(左、右諫議大夫)、洎副端(侍御史)、正言、司諫,無不預經筵者。未及兼者,惟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20]716但這不是絕對的,亦有非臺諫官兼任經筵官,如寧宗朝朱熹,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9]卷三七《寧宗本紀》一,716。
各朝經筵官或多或少,未有定員編制。宋寧宗即位之初,經筵講讀官增至十員。比高宗朝多出一倍多:“(紹熙)五年,寧宗欲增講讀官至十員,各專講兩日。”[21]卷二六《帝學·紹熙晚講》,517-518朱瑞熙《宋朝經筵制度》概括道:“總的來說,宋代講讀官‘自來’‘并不限員’,即沒有十分固定的編制。”[22]5
可見兩宋專職經筵官甚少,多是進士出身的有學問文官兼職。侍讀、侍講以兩省、侍從官兼,崇政殿說書以庶官兼,如:“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為秘書丞(從七品,庶官)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按:兩省侍從官)兼侍講。”[9]卷四百二十三《李大同傳》,12643
四、宋代經筵的講讀時間與進讀內容
宋朝,自太宗朝以下,都有開經筵之制。即使皇帝幼沖,太后垂簾聽政,或在用兵之世,也不曾中斷。哲宗朝,英宗高皇后垂簾聽政,亦“至簾下觀講官進說”,說明經筵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也依然堅持。宋室南渡,在宋金戰爭中,高宗亦未中止經筵講讀。建炎元年十二月詔曰:“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講學)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18]卷十一,建炎元年十有二月丙辰朔,283
(一)經筵講讀時間
宋代講筵開講與停講時間,據《神宗正史·職官志》:“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只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1]《職官》六之五八,3192;[9]卷一六二《職官志》,3813長至,即冬至。在每年上半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節,下半年八月至十一月冬至日,在此期間,多或以逢單日開講筵。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言:“二月開講,止于重午;八月復開,止于冬至。”[1]《崇儒》七之一九,2895通常,兩日一開經筵,北宋時單日、雙日講讀,并未統一:“恭惟皇朝家法,以親近儒臣、講論經義、商較古今為求治之本。列圣相承,所守一道,典學之勤,蓋漢唐賢群君所能及。然考之故實,皆二日一開經筵,率用雙日一讀一講。惟仁宗皇帝自干興后,只日亦或講說,而亦未以為常也。”上引《神宗正史·職官志》,定于單日講讀。所以未能說北宋“率用雙日一讀一講”[1]《崇儒》七之二六,2898。南宋則多以逢單日舉行。如宋光宗即位之初,即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御邇英閣開講:“自是只日,率以為常。間遇休假,也特命講。”[1]《崇儒》七之一八,2894宋寧宗十分重視經筵講讀經史,單日早一講、晚兩講一讀,雙日晚兩講兩讀。也就是說,在開經筵期間,不分單、雙日,“咸御經筵,兩讀兩講,《寶訓》《通鑒》《詩》《書》《禮記》《春秋》《語》《孟》,分日更進,率以為常”[1]《崇儒》七之二六,2898。
(二)經筵講讀內容
經筵講讀內容,講解經、史、詩、寶訓、時政記等,亦講當代人所著的通史《資治通鑒》。經書包括《易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孝經》《道德經》,史書如《左傳》《史記》《漢書》《舊唐書》《新唐書》《貞觀政要》《稽古錄》《資治通鑒》《唐鑒》《三朝寶訓》《兩朝圣政》(即《皇宋中興兩朝圣政》)等,此外《文選》和古賢詩也都曾作為經筵講讀內容③。如慶歷四年(1044年)九月,仁宗“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講《毛詩》,王洙讀《祖宗圣政錄》,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書》”[1]《職官》六之五七,2525。又如宋孝宗即位開經筵,點讀的經史為《尚書》《周禮》《三朝寶訓》[1]《崇儒》七之九,2295。宋寧宗則除《祖宗圣政錄》《三朝寶訓》之外,點讀了《兩朝圣政》[23]44。宋神宗剛即位,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在講筵席上,神宗讓司馬光進讀他正在撰寫的中國政治通史《資治通鑒》,并親為《資治通鑒》作序[6]458。南宋政權初建,宋高宗于建炎二年(1128年)開經筵,依例請皇上點定講授課程,高宗“詔講《論語》,讀《資治通鑒》”。
皇帝開講筵,聽講讀官講經史,目的是從中汲取治亂之經驗教訓,要求講讀官尊重史實,不必有所忌諱。“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于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后王鑒戒,何必諱?’”[24]8仁宗“命侍臣講讀,凡經書有該治亂及教化者,周悉講論”[25]356。
好的經筵官講讀經、史,能古今為用,觀照歷史、聯系現實,以達到資治的目的。茲舉經筵官周必大為例。周必大,進士出身,孝宗欽點他為侍講,官銜為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周必大撰《周禮》講義: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會其數,雖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會之耳。
恭聞真宗皇帝西幸鞏洛,得生鯉不忍食,而縱之;憫羔羊叫號,即詔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猶因庖廚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并舉,誠可為萬世法。
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于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奸,則視生靈肝腦涂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蓋周官之罪人也!④
上引講義,引《周禮》經典語錄,在闡釋本義的同時,將宋仁宗之仁慈、重民生,與梁武帝佞佛、信奸臣而釀成侯景之亂作了對比,從而揭示學習經書是為施行仁政之旨。這樣給皇帝講經,效果很好,就講活了,而不是停留在枯燥的文義考證上。
開經筵講讀,宋朝皇帝不是為了裝飾儒雅門面,實有提高治理國家能力的用心。因此十分重視從先帝謨訓中汲取政治經驗。在聽讀經筵官講讀經、史之外,也要求講讀官講讀先帝《正說》《三朝寶訓》《兩朝圣政》等,從中得到啟迪,應用于決策之中。
如寶元二年(1039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十分詳細,列出了自漢、晉、南北朝、隋唐至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戶口數。這個統計是怎么來的呢?原來是出于仁宗在經筵聽講解真宗《正說·養民篇》時,受到啟發,深感國家戶口數的增減事關重大,遂命編修院與三司做歷代戶口統計的:
先是,上御邇英閣,讀真宗皇帝所撰《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后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圣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于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8]卷一二三,仁宗寶元二年三月壬寅,2897-2898
此外《寶訓》與《圣政》,也是仁宗之后歷朝皇帝經筵必讀之謨訓。鄧小南《祖宗之法》中說:
經筵講讀,在宋代,某種植意義上是教育天子的平臺。從目前資料來看,經筵進讀的“祖宗圣諭,是以《寶訓》為主。亦有進讀《圣政》者,例如寧宗朝,曾讀《高宗圣政》《孝宗圣政》。《寶訓》所記錄的,雖然是往事言談,但皆出自本朝祖宗,又被評為后嗣帝王奉為治國章法,比照處理時下事務,因而被評為賦予至上的權威。”[2]300
五、宋代經筵的講讀場所與講讀方式
(一)經筵講讀場所
經筵講讀無固定殿閣,不同時期有相對穩定的場所。內殿、秘閣、資善堂、邇英閣、說書所、講筵所、延羲閣等,皆曾為講筵之所,其中以講筵所為常設之講讀場所。《玉海》載:“天禧四年,宣祐門內東廊以北,講筵所亦在焉。”[21]卷一二九《祥符資善堂》,2387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正月癸丑建邇英閣、延羲閣,寫《尚書·無逸篇》于屏。邇英閣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羲閣在崇政殿之西,北向。當日,開延羲閣講讀。召輔臣觀翰林學士盛度進讀《唐書》,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講《春秋》,講罷,曲宴崇政殿⑤。英宗即位不久,即“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者經、史”[9]卷十三《英宗紀》,255。南宋亦置講筵所,《乾道臨安志》記載:“經筵:講筵所,資善堂,講筵閣。以上并在禁中。”⑥
講筵的開設,則由專門管理講筵事務的機構負責。北宋稱管勾經筵所,南宋困避高宗趙構諱,改稱主管經筵所。如元豐八年七月庚申(哲宗已繼位),中書省言:“管勾經筵所言:‘準《令》,講筵春起二月,止五月三日,秋起八月上旬,止冬前十日。今來本所未敢依令施行。’”此記載說明,在北宋神宗、哲宗朝,管勾講筵所機構是常設機構。盡管神宗病逝,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但管勾講筵所未罷廢。因此在皇位交接之后,新的幼沖皇帝在守制中,如何開經筵?管勾講筵所上奏中書省請旨。答復是:“候祔廟畢,取旨。”[8]卷二五八,元豐八年七月庚申,8574-8575擔當管勾或主管官是內侍。“說書所或講筵所的長官稱管勾說書所或知管勾經筵所,由內侍充任”[26]271。擔當主管講筵所的內侍,地位很高,有的為內侍省的長貳官擔任者。如宋理宗紹定二年(1229年),詔杭州大滌洞鑄銅鐘,其監鑄人則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主管經筵所、提點資善堂劉世亨[27]457。主管講筵所下設有祇應御書、手分、投送、看管士兵和灑掃庭除之士兵等[1]《崇儒》七之五,2887。
(二)經筵講讀方式
經筵的講讀方式,在宋仁宗乾興之前,講讀官皆坐講,賜茶。坐前設案,講義本子擺放在案上,皇帝別坐而聽;乾興后,說書日,講讀官先賜坐、賜茶;臨開講,則侍立,體現所謂君臣之義;講畢,復賜坐、賜茶,以示皇帝尊師之禮[1]《職官》六之五七,3191。
(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程頤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頋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于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16]卷十三,宋哲宗元祐二年春三月甲寅,822
講讀中,經筵講官主講,宋代皇帝在經筵中聽經筵官講讀,多能專心聽講,有所收獲。宋寧宗好學不倦,即位后一改隔日講讀為每日講讀:“每當講讀,凝神審讀,諸儒之說間有理到詞達,足以發明微旨,默契圣心者,必首肯意受,喜見天顏。或誦說之多,至漏移十數刻,亦未曾有倦色。蓋自昔帝王之好學誠篤不厭,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1]《崇儒》七之二六,2898
在聽講過程中,皇帝隨時提出疑問,講官解答,帝聽之,宰輔也可解答。如景祐四年(1037年)十月丙戌,侍讀丁度讀《正說·養民篇》。仁宗問:“尸子言:‘君如杅,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焉。’”[28]696 冊,卷四《仁宗皇帝》上,750熙寧三年(1070年)十一月,神宗在聽侍讀司馬光講《資治通鑒·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時,提問:“使漢武帝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司馬光回答:“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神宗駁之:“人與法亦相表里。”[28]696 冊,卷八《神宗皇帝》下,773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奮發有為的君主,使漢代文明達到高峰,如守祖宗成法無為而治,能達到如此輝煌境界嗎?神宗顯然以此說明因應時代演進、變法之重要。司馬光則堅持守舊立場,以“蕭規曹隨”之例來反對變法。神宗并沒有認同,提出法與人是“表里”關系,法是人的需求的外化,如果人的需求有變化,法必須跟著變化。在西漢初,久經戰爭喪亂,社會需要安寧。到了漢武帝時,情況已變,人們有強國富民之需要,君主就要對祖宗之法有所變更。這反映了宋代講筵席也是君臣結合經史商討國策的平臺。宋代君主博覽群書,聽經筵官講讀,多能專心聽講,有所收獲,并常能在講讀中將所得學問與講讀官切磋。景祐四年,宋綬講《春秋》。仁宗對講官說:“《春秋》經旨在于獎王室尊君道。丘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錄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圣旨。臣等自今凡丘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僣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28]696 冊,卷四《仁宗皇帝》上,750
此外,開講或一書講讀終篇時,會特召宰執陪聽:“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羲(閣)。每初讀,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遂賜宴。”[13]10中書門下、樞密院二府大臣聽講時,在講讀官前設座位[1]《職官》六之五七,3191。“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易》終篇,特召宰執聽講”[1]《職官》六之六一,3195。
經筵講授時,史官,即起居郎(左史)、起居舍人(右史)等記注官,自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起,許入講筵所侍立,以記錄皇帝與講讀官言論[8]卷一七六,仁宗至和元年八月戊午條,4273。記注官陪侍經筵,職在記言動:“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9]卷二九九《石揚休傳》,9930乾道八年(1172年),吏部尚書兼侍讀汪應辰言:“凡經筵官侍講、侍讀皆賜坐,記言動者皆立。今臣兄為起居郎(汪涓),其立固當。臣猥以侍讀,反得賜坐。”[1]《職官》六,3196史官入侍經筵,須將其所記言動,退而撰寫成記注:“經筵記注官侍立,并以所聞退書其實。”[16]卷二十七上,孝宗淳熙八年四月,2265關于經筵所講讀活動的著述,初非出自史官之手,而是出乎說書官之手,景祐三年(1036年),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凡書筵侍臣出處、升黜,封章、進對,宴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為二卷。”仁宗閱后,將此書命名為《邇英延羲二閣記注》[8]卷一一八,仁宗景祐三年年正月乙已條,2774-2775。哲宗朝重申:“講讀、記注官同共編修(《邇英閣記注》)。”[8]卷四六四,哲宗元祐六年八月辛亥條,11087-11088南宋延續此制:“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洪遵言‘臣以記注陪侍經幄,瞻望天威,近在跬步,至于御茗分珍、華墩賜坐……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修注官雖與簽書,未嘗有奏事者。’”[1]《職官》六,3195起居郎、起居舍人陪侍經筵,職在記注,不能在御前奏事。
結 語
宋代皇帝愛讀書,同時禮賢下士,重視延請飽學之士至宮中,為皇帝上課,經筵制度得到持續傳承,自太宗后無一朝不設。經筵制度,在趙宋王朝,被定為“家法”:“恭惟皇朝家法,以親近儒臣,講論經義,商較古今,為求治之本。”[1]《崇儒》七之二五、二六,2898
縱向考察中國古代政治史,文治成功,這是宋代對維護華夏文化沒有斷裂的最大貢獻。如若任唐末、五代混戰的局繼續下去,主張維護大一統的儒學理論——“四書”“五經”,勢必被軍閥視為弊屣而棄之,科舉制也不可能振興。錢穆說:“幸而還是宋代特別重視了讀書人,軍隊雖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然能復興,以此內部也還沒有出什大毛病。”[29]101經筵制度,是宋代皇帝主動延請深諳經、史的士大夫為師,深造儒學,從而充實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從中汲取治國經驗教訓的一種良好的經國制度,成了宋代趙氏王朝的“祖宗家法”,可以視為“中國之治”的一份重要遺產。
注釋
①參見朱瑞煕《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第二章《皇帝制度》第七節《經筵制度》;參見白鋼主編《中國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7 頁。②參見《新編翰苑新書·前集》卷十一《經筵·侍讀 侍講 崇政殿說書》,《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4 冊,第102 頁;《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中書省·集賢殿書院》,第1213 頁。③參見王應麟《玉海》卷二六《帝學》,第513-530 頁;《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五六至六三《侍讀 侍講》,第2524-2528頁;宋熊克撰,辛更儒校補《皇朝中興小紀事本末校補》(待出版稿)卷十四,建炎四年七月己已條,范祖禹在經筵所進《唐鑒》,第83 頁。④參見周必大《文忠集》卷首《年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 冊,第8頁;同前書卷一五四《承明集》二《經筵講義·周禮》,第1148 冊,第679頁。⑤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六,仁宗景祐二年正月癸丑,第2720 頁;汪圣鐸點校《全宋文》卷七下《宋仁宗二》,第351 頁。按《長編》作“盛度進讀《唐詩》”,誤;《全宋文》作“盛度進讀《唐書》”,是。今據《宋史全文》。⑥參見《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二《翰林侍讀學士》:“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沒只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第3813 頁;《乾道臨安志》卷一《行在所·經筵》,《宋元方志叢刊》4 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216 頁;《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行在所》,第210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