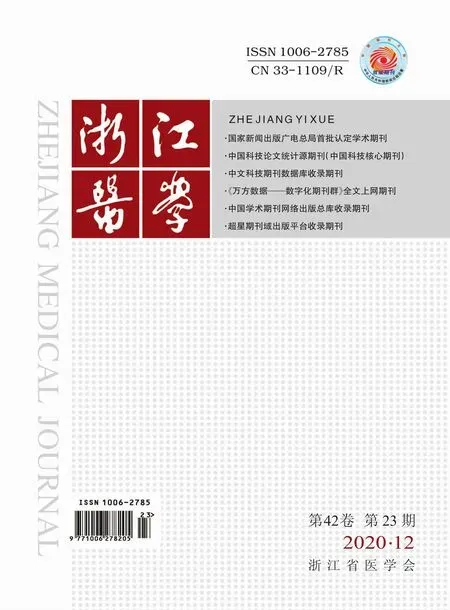死亡受體5的生理作用及臨床應用概述
曹佳樂 葉子煊 余冰慧 林道潑 勞佳瀅 邵曉曉
腫瘤壞死因子相關凋亡誘導配體(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TRAIL)與凋亡素配體1、TNF-α同源性較高,因此也被命名為凋亡素配體2[1]。TRAIL共有5種受體:死亡受體(death receptor,DR)4、DR5、誘騙受體 1、誘騙受體 2 以及護骨素。DR作為TRAIL的功能性受體可介導靶細胞凋亡,其中DR5因與TRAIL親和力高、誘導效應強備受關注。研究發現,DR5與TRAIL結合后可選擇性誘導多種腫瘤細胞凋亡,發揮抗腫瘤作用,同時也調節免疫細胞參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發展。本文就DR5的基本結構、生物學功能及其與腫瘤和自身免疫性疫病的關系等作一綜述。
1 TRAIL的結構與功能
TRAIL為Ⅱ型跨膜蛋白,C端位于細胞外,N端位于細胞質內,其基因TNFSF10位于染色體3q26,含5個外顯子和4個內含子并編碼281個氨基酸。TRAIL廣泛分布于脾、肺、前列腺等正常組織,還在淋巴細胞、自然殺傷細胞、巨噬細胞等表達并進行調控[2]。TRAIL的受體中,DR含有完整的死亡結構域傳遞死亡信號從而誘導靶細胞凋亡。誘騙受體不含死亡結構域或缺乏完整的死亡結構域從而競爭性抑制細胞凋亡。護骨素與TRAIL的親和力較弱,可結合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受體活化素配體調節骨密度,但不誘導細胞凋亡[3]。
TRAIL較凋亡素配體1、TNF-α等凋亡因子特異性更高,主要在激活的T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表面表達并介導細胞毒性,殺傷高度表達DR的腫瘤細胞。正常細胞表達較高水平的誘騙受體,故可逃脫TRAIL的凋亡作用。TRAIL還可調節免疫穩態,如抑制Th1和Th17增殖、促進Treg的增殖、參與衰老中性粒細胞的凋亡等。最近研究表明,TRAIL還與炎癥性腸病、類風濕性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疾病相關,參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病過程。
2 DR5的結構與特性
DR5為Ⅰ型跨膜蛋白,主要分布于外周淋巴細胞、肝細胞、心肌細胞、神經元、小腸細胞、結腸細胞等細胞中,并在肝癌、肺癌、乳腺癌、直腸癌等腫瘤中高度表達。DR5由基因TNFRSF10B編碼,cDNA全長1 146 bp,編碼381個氨基酸。DR5的轉錄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如抑癌基因p53、NF-κB、核轉錄因子C/EBP同源蛋白、異丁苯丙酸等,翻譯又受到人抗原R等影響[4-5]。
DR5與DR4的同源性僅為46%~48%,提示兩種受體存在明顯差異。基因轉錄方面,兩者3′-非翻譯區差異較大[4];基因表達方面,DR4表達主要受到啟動子甲基化、細胞內轉運和翻譯后修飾的調控,而DR5表達則多由轉錄過程調控[6];組織分布方面,兩者均在多種組織中表達,但在膽管上皮中僅表達DR4,而在大腦血管內、腎單位袢、結腸固有層、支氣管血管內皮中僅表達DR5[7]。與DR4相比,DR5在凋亡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8-9]。這可能與以下兩點有關:(1)DR5與TRAIL的親和力更高。過去研究表明,TRAIL在37℃時與DR5的親和力更高[10]。(2)DR5誘導凋亡的能力更強。DR4和DR5在人肺鱗癌細胞SK-MES、人結腸癌細胞Colo205、人乳腺癌細胞MDA-MB-231中的表達量相當,Kelley等[11]制備出僅與DR4或DR5結合的兩種TRAIL進行凋亡實驗,結果發現,DR5選擇性TRAIL誘導能力更強。
3 DR5的生物學功能
DR5活性多樣且以介導凋亡為主,結合TRAIL后可經內外源性途徑產生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ysteine-containing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s,caspases)高效激活凋亡通路[12]。此外DR5還參與非凋亡途徑,如激活NF-κB通路、誘發壞死性凋亡等。
3.1 介導細胞凋亡 DR5與TRAIL結合后三聚化,募集Fas相關蛋白死亡結構域(Fas-associated protein with death domain,FADD)。FADD 與 caspase-8前體(procaspase-8)結合,最終形成死亡誘導信號復合物(deathinducing signaling complex,DISC)。FADD 樣白介素-1轉換酶抑制蛋白(FADD-like intedeukin-1β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y protein,FLIP)是 caspase-8 無活性的同系物,可競爭FADD抑制DISC招募pro-caspase-8。
凋亡細胞根據是否依賴線粒體的放大作用分為Ⅰ型細胞和Ⅱ型細胞。Ⅰ型細胞產生大量DISC,經外源性即非線粒體途徑凋亡。死亡誘導信號復合物經多泛素化和切割后形成新的caspase-8進入細胞質,激活下游效應蛋白caspase-3,直接誘導細胞凋亡。Ⅱ型細胞僅有少量DISC,經內源性即線粒體依賴途徑凋亡。活化的caspase-8使BH3相互作用域死亡激動劑斷裂形成截短形式,進入線粒體并誘導細胞色素C等釋放。細胞色素C與凋亡酶激活因子、pro-caspase-9形成凋亡復合體,活化caspase-3,啟動caspase級聯反應。
TRAIL與DR5胞外域結合使DR5三聚化并激活下游通路,因此傳統觀點認為DR5胞外域是負責信號傳遞的主體。最近Pan等[13]發現,即使缺乏TRAIL和(或)DR5胞外域,DR5也可經其跨膜域中同源二聚體和三聚體的相互作用進行自我聚集,激活caspase級聯反應,而DR5跨膜域關鍵氨基酸位點的變異會影響受體聚集以及凋亡進行,這說明DR5的激活主要依賴跨膜域。
3.2 激活NF-κB通路 DR5可激活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死亡結構域蛋白介導的NF-κB通路,并獨立于凋亡通路。DR5主要通過兩條途徑激活,第一條依賴成熟的caspase-8激活casapse-3,第二條則由procaspase-8介導,最后均在抑制性κB激酶的作用下活化NF-κB[14]。凋亡通路中的caspase-8和caspase-3可裂解和滅活NF-κB通路中的信號因子,而 NF-κB會上調抗凋亡蛋白FLIP,提示DR5凋亡通路與NF-κB通路之間互相制約[14]。
3.3 促進細胞增殖 DR5在部分腫瘤中可促進細胞增殖甚至誘導腫瘤侵襲和轉移,其機制主要包括3個方面:(1)消除細胞毒性T細胞等殺腫瘤細胞,導致腫瘤免疫逃避。(2)激活NF-κB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等非凋亡通路分泌細胞因子,刺激腫瘤活化增殖。(3)增強Treg免疫抑制功能。此外,DR5效應還與其細胞定位有關。DR5在細胞表面可介導細胞凋亡,但在核轉運受體蛋白importin-β1作用下,借助核定位序列可移位核內最終導致細胞TRAIL耐藥[4]。不僅如此,核DR5還可與核酸內切酶Drosha、結合蛋白DGCR8以及調節蛋白p68、hnRNPA1等相互作用,抑制let-7 miRNA成熟,造成基因LIN28B和HMGA2損傷,從而正向調節腫瘤生長[4]。
4 DR5與腫瘤的關系及應用
4.1 DR5與腫瘤的關系 DR5在多種腫瘤中高度表達,有效誘導細胞凋亡。DR5基因敲除(DR5-/-)和TRAIL基因敲除(TRAIL-/-)小鼠腫瘤易感性增加且更易發生腫瘤轉移。研究表明,敲低人肺癌細胞系A549、H460和PLA-801C中DR5表達會增強腫瘤侵襲和轉移[15]。A20鼠B細胞淋巴瘤模型、鼠p53半敲除(Trp53+/-)淋巴瘤模型中,TRAIL-/-小鼠較野生型小鼠腫瘤生長和轉移的概率增加[12]。
4.2 臨床應用 惡性腫瘤傳統治療主要選用手術和放化療相結合的模式,常伴有明顯的毒副反應和耐藥現象,因此亟須找到一種安全高效的藥物。TRAIL受體激動劑(TRAIL receptor agonists,TRAs)是基于 TRAIL-DR靶向特征而設計出的一類藥物,主要包括重組TRAIL和DR特異性抗體。但這些藥物臨床療效多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歸結于以下3點[12]:(1)原發性腫瘤對TRAs耐藥。(2)激動劑效應不強。(3)缺乏可靠的生物標志物。
4.2.1 重組TRAIL 重組TRAIL形式多樣,抗腫瘤譜廣,臨床潛能較大,然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還有待考證。由于護骨素表達增加、DR表達降低、FLIP表達過度等原因,多種腫瘤出現TRAIL耐藥[12,16]。人重組TRAIL杜拉樂明因半衰期短、易與非凋亡受體結合等原因造成藥物療效低下。此外,TRAIL還可促進腫瘤生長。Hoogwater等[17]證明,TRAIL可原癌基因KRAS依賴性刺激小鼠結直腸腫瘤侵襲和肝轉移。Hartwig等[18]證明,TRAIL可經NF-κB通路產生IL-8、C-X-C型趨化因子配體 12(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CXCL1)等趨化因子促進小鼠肺癌細胞增殖。
4.2.2 DR5特異性抗體 DR5特異性抗體較重組TRAIL半衰期更長,且僅結合DR5不受誘騙受體干擾。小鼠試驗證明,抗DR5單克隆抗體可誘導多種TRAIL敏感的腫瘤細胞凋亡,但對正常肝細胞作用甚微[8]。由于較高的穩定性和安全性,DR5特異性抗體也很快發展至臨床階段。遺憾的是,第一代藥物如來沙木單抗、曲齊妥單抗等既沒有提高客觀反應率,亦沒有增加患者整體生存率,多于Ⅰ、Ⅱ期臨床試驗中被叫停,可能與其二價結合模式以及免疫細胞Fcγ受體減少有關[12,19]。
4.2.3 新型療法 盡管臨床效果不佳,DR5在腫瘤治療的潛能依然推動著治療進展。新型TRAs正在逐漸開發且部分用于臨床研究,主要特點為穩定性更高、激動性更強、多價結合等。TRAs與放化療、抗凋亡蛋白抑制劑、TRAIL增敏藥物、天然化合物等的聯合也可增強凋亡活性。此外,利用生物標志物綜合考量TRAIL-DR5效力是腫瘤個性化治療的新方向。研究發現,O-糖基轉移酶GALNT14的表達增高與TRAIL敏感有關[20]。Pal等[21]表明,TRAIL可促進KRAS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增殖。
5 DR5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關系及應用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機體以自身組織器官為抗原產生異常免疫應答而導致的疾病。研究發現,DR5在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中上調并具有保護作用。敲除DR5及TRAIL會增加小鼠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性,而注射重組TRAIL卻可減少炎癥和自身免疫性破壞。此外,DR5及TRAIL對炎癥的緩解亦可預防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相關腫瘤的發生[2,22]。
5.1 炎癥性腸病 炎癥性腸病是一組病因尚未完全明確,反復發作的慢性非特異性腸道炎癥,主要包括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凋亡紊亂是炎癥性腸病重要特征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炎性腸段上皮細胞的凋亡水平顯著高于正常腸組織[23-24],克羅恩病患者腸固有層中的淋巴細胞則存在凋亡缺陷[25-26]。DR5參與腸道炎癥的發生、發展。研究證實,DR和TRAIL基因多態性可能與炎癥性腸病易感性相關[27-28]。Zhu等[29]證實,DR5-/-小鼠較野生型對葡聚糖硫酸鈉誘導的結腸炎以及相關腫瘤如結腸腺瘤有更高的易感性。國內學者也證實,TRAIL-/-小鼠經葡聚糖硫酸鈉誘導的結腸炎較野生型更為嚴重,并伴有外周血單個核細胞和腸系膜淋巴結中Th17水平的升高和Treg數量變化[30-31]。最近小鼠研究證實,TRAIL主要是通過非凋亡途徑抑制葡聚糖硫酸鈉誘導的結腸炎,且是與DR5相互作用抑制結腸炎T細胞激活[32]。以上研究均提示DR5對炎癥性腸病特別是潰瘍性結腸炎的發生發展具有保護作用。現多數研究僅處于初步階段,其分子機制仍待進一步闡釋。除了凋亡通路,研究者還可將DR5與炎癥性腸病的研究范圍拓展至非凋亡通路以及免疫細胞調節等方面。此外,可利用動物模型對重組TRAIL、DR5特異性抗體等制劑進行療效比較,為DR5臨床應用奠定實驗基礎。
5.2 類風濕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因滑膜細胞、淋巴細胞等浸潤導致滑膜組織增生和骨組織破壞的慢性炎癥性疾病。Zhang等[33]發現,抗DR5單克隆抗體可劑量依賴性誘導離體成纖維樣滑膜細胞凋亡,并抑制TNF-α、IFN-γ等炎性因子分泌。類風濕性關節炎小鼠研究顯示,DR5與TRAIL結合后可抑制T細胞活化以及促炎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分泌[34]。有學者發現TRAIL可抑制類風濕性關節炎小鼠Th17增殖并誘導Treg增殖,發揮抗炎作用[35]。可見,DR5是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理想靶點,通過誘導成纖維樣滑膜細胞的凋亡、調節Th17/Treg軸等途徑直接或間接緩解疾病。
5.3 系統性紅斑狼瘡 系統性紅斑狼瘡是一種多系統損害性結締組織病,表現為細胞凋亡紊亂,伴有DR5及TRAIL顯著增多。Saeed等[36]檢測發現,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血清TRAIL水平不僅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且與疾病活動程度呈正相關。Wigren等[37]發現,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血清DR5水平高于健康對照組,并與心血管風險相關,提示DR5或許是該病心血管損傷的潛在生物標志物。
6 小結與展望
DR5可介導靶細胞凋亡并激活NF-κB等旁路途徑,對腫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重要意義。DR5與TRAIL親和力高并廣泛分布于腫瘤細胞,是腫瘤治療的理想靶點。盡管藥物有效性低下、腫瘤細胞耐藥等原因使得DR5前期臨床發展不佳,但越來越多的改良藥物和新型方法在臨床前研究中表現良好并相繼納入臨床試驗。DR5與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并有望成為新的治療靶點,但仍缺乏明確的分子機制,也尚無成熟的臨床應用。最近DR5定位效應及其跨膜域自行聚集的發現提示DR5可能比TRAIL更適合成為治療靶標,并為今后研究提供新的治療思路如促進DR5自我聚集、抑制DR5核受體表達、篩選合適的受體激動劑等[4,13]。未來的研究者需在充分掌握DR5生物學活性的基礎上結合DR5調節機制設計出多元化、精準化、聯合化的用藥新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