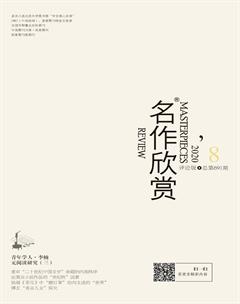災難敘事,當以“真”動人
摘 要:在文學史上,以“災難”為題材的作品屢見不鮮。災難敘事以殘酷的災難事實為依據,采用文學的方式對事實進行選擇性地創作表現,其源于事實又高于事實。作為當代文學史上災難敘事的代表作品,《溫故一九四二》重真相而輕溫情;《黃河東流去》重理想卻有失真實。真正優秀的災難敘事作品須得以對事實的尊重為前提,在此基礎上表現“作為人” 的真情實感,以感人的故事和真摯的情感動人。
關鍵詞: 災難敘事 《溫故一九四二》 《黃河東流去》 真情實感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歲月中,“災難”從來都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以“災難”為題材的作品更是數不勝數。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和李凖的《黃河東流去》都是當代文學史上災難敘事的代表作品,但兩部作品在災難書寫地選擇上卻不盡相同。本文認為《溫故一九四二》重真相而輕溫情,《黃河東流去》重理想卻有失真實。在真相和理想之間,作家究竟應當如何進行災難敘事是文章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一、真相與理想的抉擇
對以災難為題材的作品而言,真相往往是殘酷的,它以摧枯拉朽的姿態消解著人類幾千年的文明歷程。災難摧毀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人性隨之受到考驗。
《溫故一九四二》中由干旱、蝗蟲所導致的大饑荒造成近三百萬人餓死,數千萬人流離失所的災難事實是不可回避的。“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累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至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a殘酷的現實置人于絕望的處境之中,萬千災民在死亡的邊緣徘徊。在人本能的生存欲望驅使下,丈夫賣妻、夫婦賣子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層出不窮。在求生欲望驅使下,人無意識地實現了向獸的退化。人性與良知被饑餓驅趕,倫理道德喪失殆盡。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選擇對黎民百姓的生死視而不見,對上層官員來說,三百萬人的性命比不上斯大林格勒戰役與丘吉爾感冒,甚至有人大發國難財。人對災難的麻木態度與人性的冷漠自私被展現得淋漓盡致。災民自身無力抵抗災難,政府亦無心救助,人親手把自我推向絕望的境地。災難的無情,死亡的威脅,人性的丑惡,生命的低賤構成了殘酷的真相。
馮小剛在《溫故一九四二》的序中曾多次提到,小說文本在籌備拍攝電影的過程中多次送審均未通過的主要原因是:“調子太灰,災民丑陋,反映人性惡,消極。” b
但是丑惡并非災難敘事的全部,美善表現了最后的倔強。作為同時期災難敘事的代表作,李準的《黃河東流去》講述了1938年日軍入侵中原地區,國民黨當局采取“以水代兵”的策略強行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以赤楊崗地區百姓為代表的黃泛區人民背井離鄉逃荒十年的悲慘遭遇。在十年的逃荒歷程中,赤楊崗的村民們分別經歷了水災、旱災、蝗蟲等諸多殘酷的災難。他們躲避過飛機的轟炸,承受過城市人的欺壓,為獲得糧食不惜喪失性命。長松一家為了活命不惜賣掉閨女,小嫦娥為減輕梁晴負擔,去工廠做工下落不明。赤楊崗村民們千里跋涉向西逃荒,曾幾度在死亡的邊緣徘徊。雖然作品中也寫了海騾子和海香亭等人一心為己,通敵出賣鄉民,趁機大發國難財的行為,但并未詳述。
在《黃河東流去》中,作者力圖在殘酷的現實中尋找隱藏在普通人背后的文化力量以及他們在災難面前表現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所以作品的格調是深沉悲壯的,更是昂揚向上的。首先,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赤楊崗地區的七戶農民無論身在鄉村,還是逃亡的路上都竭力維護著傳統宗法社會的秩序,遵從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倫理道德;在逃難的過程中,從海長松、陳柱子等人身上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國人民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精神品質。優秀傳統文化賦予的力量使他們經受住了災難的考驗。其次,從人情、人性的角度看,作為“人”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美在這里彰顯。在親情上,李麥千里尋女,海老清視女兒如珍寶;在愛情上,梁晴和天亮的愛情并未因長久的分離而變質,藍五與雪梅的愛情奏響的是梁祝的悲歌。內在文化力量的支撐以及村民們對美好人情人性的追求使得赤楊崗人民在與絕望的斗爭中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在經歷長達十年的流亡之后,他們最終得以返歸故土,在這群普通的農民身上蘊含了數不盡的希望,他們不斷尋找自救的方式,以頑強拼搏的精神和昂揚的斗志奔向光明。
誠然,作品中對美好人性的表現與著力找尋希望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正如何恩玉所說:“作品在寫民族的光芒四射的精神支柱方面,任務完成地比較好,但在尋求民族劫數的根源和因襲的包袱方面,作品就黯然失色了。” c
《溫故一九四二》立足現實,對災難殘酷的一面毫不掩飾。 站在歷史的角度,對災難如實地表現是對歷史的尊重,它為歷史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史料。它以堅決的態度反抗“被遺忘”的命運。但站在文學的角度看,對現實的丑惡完全地表現則使文學喪失了審美的“愉悅”,失去了文學的悲憫與力量。《黃河東流去》努力尋找美,人們從悲劇中發現了積極向上的力量,并以此走出精神恐慌,但它在表現災難記憶和人性復雜性方面略顯單薄。兩部作品各有其不足,如此而言,災難敘事中真相與理想的最佳平衡點當在何處?
二、災難敘事以真動人
“真”是最好的平衡點,在作品中,我們要盡可能還原災難,在對惡的反思中發掘美,去尋找人能度過這一次次災難,并能在丑中重歸于美的精神動力。
《黃河東流去》確實挖掘到了支撐中華民族綿延不息的文化因子,但是作品也正是因為偏重于對文化以及美好人性的追求而相對忽略了對民族災難根源的追尋,導致災難敘事流于表面。作者對美的過度追求使他自覺減少了對丑的挖掘。一方面,李準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寫農民身上積極向上的力量,他雖然看到了農民自身因襲的落后因子,卻并沒有對農民思想的弊端進行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在追求美好的過程中,作者把人性提到了一個理想的高度,為了突出人性的美好而忽略了人性復雜的、消極的一面。李麥作為赤楊崗逃荒的領頭人,她身上體現的那種英雄式的大無畏精神、先進的思想覺悟和近乎全能式的行為作風使她失去了作為農民的真實。同時,不論是梁晴還是愛愛和雁雁,幾乎所有新一輩的女性在作者的筆下都是外在美與心靈美的集合體,她們作為人所具有的美與丑的矛盾融合被單一化。從災難敘事的角度講,《黃河東流去》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書寫了具體的災難,但卻忽略了隱藏在農民意識中造成災難的根源,從而失去了災難的深度;此外,接近完美的人物形象又使災難敘事缺少了它真實可感的一面。在談到《黃河東流去》的創作時,作者曾說:“從小說中可以看見我對鄉村生活的依戀,有意識地回到質樸中去,回到自然中去,流露出我對故鄉、對大自然的依戀和歌頌。”d赤楊崗是作者理想中的鄉土,而太過美好的理想就不免缺了些真實感。《黃河東流去》尊重了黃水泛濫的災難事實,在真實的基礎上挖掘了理想,但作者對理想過度地表現削弱了現實的殘酷程度,缺少真實性的災難敘事無法引起讀者的共鳴。
根據“文學四要素”的相互關系,世界是文學活動產生和存在的物質基礎,更是文學作品再現或反映的對象。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災難敘事的作品是在災難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這也就說明在進行災難敘事時,對災難事實的關注與表現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也是最為基礎的部分。首先,失去了災難事實的支撐,災難敘事便如空中樓閣,終究底氣不足;其次,尊重災難事實也是保留災難歷史的一種方式,災難敘事承載了一個民族幾代人沉重的歷史記憶,同時也為后世提供了借鑒。
上面說過,災難敘事作品是對災難事實的再現,在再現的過程中作者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作者對災難事實的選擇以及表現的程度都具有很大的主觀性。文學作品作為作者的創造物和讀者閱讀的對象,它不僅屬于作者,更屬于讀者,屬于世界。所以,作者進行災難敘事還要站在文學接受主體的角度考慮。顧曉明認為:“一次真正能夠感動人的災難敘事,必須洞悉和表達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體驗和想象的超凡情愫和潛質,在因難以言表的痛苦遭際而變得和乖戾悖的事態中,裂變出一種圣潔晶亮的真善美。”e巨大災難的降臨以超常規的方式打破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習慣,特殊時期的特殊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改變人們的認知方式。災難是一場考驗,人們在困厄艱難的環境中所做的掙扎與努力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從這力量中裂變出來的真善美正是人們所渴求的。向榮教授也認為:“災難敘事還有普遍的人性的維度,在此,人性的偉大光輝得以放大和張揚。” f
真正好的災難敘事作品應當在尊重并超越災難事實的前提下做到以真摯的情感動人。災難敘事當立足實際,努力表現“作為人的真實的美”。人性是復雜的,在災難的威脅之下,理想中的美并不具備說服力。人們有其丑惡的一面,面對死的恐懼,災難的威脅和迷茫的未來,他們有意志上的掙扎和道德上的矛盾,但他們必定也有對生的渴望和對真善美的追求。人在災難面前未必勇敢,也并不完美。災難敘事所要做的就是表現真實的人,表現作為人所具有的真情實感,從人在絕望與希望的掙扎中看到向上的力量。對讀者而言,閱讀文學作品是“認識”和“愉悅”的過程,對事實的認識和正能量的接受能夠使讀者獲得內心的滿足。總而言之,災難敘事要有一種超越事實的“真”,以真正的事件、真實的故事和真摯的情感動人。
ab劉震云:《溫故一九四二》(典藏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第4頁。
c何思玉:《一部過渡性的作品——〈黃河東流去〉得失管見》,《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第124—127頁。
d 徐其超,呂豪爽:《〈黃河東流去〉文化價值探尋》,《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56—60頁。
e 參見《〈唐山大地震〉引熱議:災難敘事究竟以何動人》,《解放日報》2010年7月31日第006版。
f 彭貴川:《文藝理論的現實關懷與學科未來——“后悲劇時代的災難敘事與人文關懷”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6頁。
作 者: 陳靜,文學碩士,鄭州大學文學院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