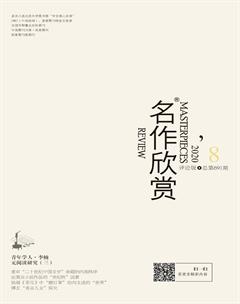論“網絡文學”命名
摘 要: “如何定義網絡文學”一度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熱點,卻極少有人對“網絡文學”命名表示疑惑。二三十年來,大家一直使用“網絡文學”,似乎理所當然。殊不知,這一不證自明的命名存在著諸多的模糊性。媒介命名是否準確?“網絡文學”如何體現出民族性與世界性?在現今以網絡類型小說為主流的泛文化娛樂全產業鏈中,再堅持“網絡文學”的叫法是否有意義?在成長中的文學形態面前,相比定義網絡文學現象,轉而思考“網絡文學”命名或許能為網絡文學基本學理研究打開新的思路。
關鍵詞:網絡文學 概念 命名
一、媒介命名是否準確
如果說有人在研究唐宋文學,有人在研究明清文學,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因為根據不同的時段可以劃分出不同特點的文學;我們常說的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等也都在大家的認知范圍內,因為這是根據意識形態上的變遷或政治活動來作為文學的分野;因為題材、主題等要素,有革命文學、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鄉土文學;因為文學創作手法、創作理念的不同,有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非虛構文學。這些文學命名都是有跡可循且符合常理的。然而,“網絡作為技術平臺,只是一個載體,以載體命名文學,前所未有”。順著“網絡”往前推,那就應該有“紙張文學”“絹帛文學”“竹簡文學”“甲骨文學”等,先不談論有無這些文學命名的存在,這樣的文學命名有何意義?它既沒有體現出歷史的時間概念,又沒有表述出“新文學”與之前文學在內容或形式兩方面的新質。“從文學的限定語‘龜甲‘竹簡‘絹帛到‘紙面‘網絡這些載體的變化上”,恐怕只能“看出科技發展史之一斑”。
如果“網絡文學”強調的是其傳播的新媒介屬性,那么它相對的應該是“印刷文學”與“口頭文學”。如此,那些先在網絡發表后又線下出版的文學作品到底該歸為網絡文學還是印刷文學?現在有很多傳統經典書籍經過人工碼字或電子掃描都可以在網絡上看到,這些變成電子資源后的印刷文學又該如何稱呼?以媒介命名的“網絡文學”,即使已經約定俗成地使用了二十多年,也不難看出其命名的誤區及不準確性。
再說,有學者在定義網絡文學時將其與傳統文學放在一起加以區分,仿佛“網絡文學”是針對“傳統文學”提出的。實際上,中文的“傳統”,英文的tradition、convention均是指世代相傳的、舊有的精神、制度、風俗、藝術等事物,與之相對的應該是現代的、前衛的、新階的事物。因此,與“傳統文學”對應的文學命名應該是能夠革舊查新、進行藝術創新的“先鋒文學”“新興文學”或“現代文學”之類。何況,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當時的網絡文學“四大寫手”(寧財神、邢育森、李尋歡、安妮寶貝)的作品在現在看來只是傳統文學的網絡發表。若真是應了某些研究者的說法,將“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兩相對照,那么傳統文學作為過去的、從前的、完成時態的某種事物就只“等著后人的懷念或者繼承,傳統的文學工作者也只是在發揮余熱了”,顯然,“網絡文學”“是一種很不準確的而且已經引起混亂的命名”。
二、何以體現民族性與世界性
目前存在的網絡文學定義可以三大標準劃分:一以“文學”為標準;二以“網絡”為標準;三是將兩大標準結合起來,稱之為結合版。也就是說,網絡文學的定義大都聚焦于兩點——“網絡”與“文學”。要么是出于對“網絡”的技術崇拜將網絡文學定義為:凡是在網絡媒體流通的文字;要么是出于文學審美的視角定義網絡文學是在網絡上傳播并與傳統文學有著創作方式、創作手法、文學體制等方面不同的文學。但這兩類都忽略了創作實踐中的網絡文學現象。依照網絡文學的實際情況來看,在漢語網絡文學之外,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網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論批評等方面形成了不同民族的網絡文學特色和文學陣營”,是二十年中國網絡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勁旅。是以,“漢語網絡文學”命名的提出為我們思考“網絡文學”何以體現民族性的問題提供了契機。
“網絡文學”命名明顯偏重于“網絡”新媒介,指代非紙質版傳播的文學。有個問題是,網絡文學能囊括除紙質版傳播文學以外的一切文學形式嗎?單小曦在《數字文學的命名及其生產類型》中斷言:如今的網絡文學并不能涵蓋所有數字文學。“今天也存在著大量的非網絡化的以光盤、計算機軟件、數字儲存器特別是越來越智能化的電子書形式傳播、發行、閱讀的數字文學形態,這些都不能稱之為網絡文學。”也就是說,用“網絡文學”來命名在西方稱為“超文本文學”(Hypertext Literature)、“數字文學”(Digital Literature)的此種文學形態是不準確的,更不要說它是否體現了世界性。在“中華網文與美國大片、日本動漫、韓國游戲”共稱“當今世界文化創意產業領域中并駕齊驅的‘四駕馬車”的當下,對靠國內輸出的域外翻譯網站接觸中國網文的外國讀者來說,在這一平臺上的“網絡文學”就等同于Online Literature(在線文學),當中國文化與世界接軌時,“網絡文學”命名能體現世界性嗎?“在線文學”命名是否更加恰當呢?在網絡文學的成長中,這都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三、“網絡文學”=“網絡小說”?
網絡文學目前已然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一個炙手可熱的對象,據中國知網檢索,截至2020年5月,以“網絡文學”為主題的碩博論文有1056篇,期刊有5251篇,會議論文和報紙文章分別有115篇和1404篇。有意思的是,再分別以“網絡小說”“網絡散文”和“網絡詩歌”為主題檢索時,卻出現了較大差別的結果。同段時間內,研究網絡小說的碩博論文有569篇,期刊有1579篇,會議論文有18篇,報紙文章有312篇;研究網絡散文的篇數分別是2篇、16篇、1篇、1篇;研究網絡詩歌的則有44篇、208篇、5篇、13篇。也就是說,在網絡文學作品批評研究中,網絡小說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
網絡文學網站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現今正處于市場化運營的高速發展期,據2019年9月《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站數量為518萬個,其中有一部分為文學網站。在歐陽友權編撰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這本書中列舉了20家大型文學網站代表:起點中文網、創世中文網、縱橫中文網、阿里文學、晉江文學城、17K小說網、瀟湘書院、小說閱讀網、紅袖添香、起點國際、起點女生網、云起書院、言情小說吧、榕樹下、塔讀文學、愛讀文學網、幻劍書盟、天下書盟、逐浪網、紅薯網。可以發現,這二十家代表網站中有三家直接以“小說”命名網站,而以“散文”“詩歌”命名的一家也沒有。
在關于網絡文學的定義中,已經有研究者將“網絡文學”與“網絡小說”畫等號了。李敬澤提出約定俗成的網絡文學概念“其實很明確,主要就是指在網上生成和閱讀的那些長篇小說”。閱文集團總經理楊晨將這一概念解釋得更為清楚:在他看來,網上的散文、詩歌并不是網絡文學,網絡文學就只是長篇通俗小說,因為“網絡文學的讀者,他們并不會只閱讀網絡文學,但當他們上網想閱讀這類作品時,他們想看的絕不是詩歌散文。我們硬把它們也列入網絡文學,硬去推薦給讀者,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甚至如今網文界的“主流”定義和學界、官方、媒體以及公眾在評論、報道網絡文學時的“社會化”定義都傾向于類似《悟空傳》《誅仙》《盜墓筆記》這樣的長篇連載類型小說。
此外,2009年以后,資本的進入催生了網絡類型小說的空前繁榮,由此產生了網絡文學IP概念,形成了以網絡小說為源頭的產業鏈。網絡文學開始全版權運營,與影視、動漫、游戲、演藝等泛文化娛樂領域聯合打造文化產品,“跨界合作”成為未來網絡文學發展的可能方向。
在以上三種情形下,再堅持使用“網絡文學”命名是否還有意義?“網絡小說”能夠取代“網絡文學”直接命名這一文學現象嗎?如果可以,為什么是“網絡小說”替代“網絡文學”,而不是“網絡散文”“網絡詩歌”呢?類似的疑惑在近二十年網絡文學研究中并沒有得到討論,這其實是需要反思的。
四、結語
“我們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網絡文學,其實它只是一個籠統含糊的概念,這個稱呼更多地帶有隨意性”。研究者們在追問思考如何定義網絡文學時,首先得弄清楚“網絡文學”這個命名本身的模糊性。雖然“網絡文學”因為被廣泛運用而具有了某種理所當然性,但是筆者認為從網絡文學不斷生長的事實來看,這一命名只是暫時的,必將有更適當的概念來替代它。
參考文獻:
[1] 夏烈.裂變與交互:當下文藝生態的直觀與反思[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
[2] 張登林.“網絡文學”命名的草率與內涵的無區別性[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1).
[3] 康橋.網絡文學的命名與功能[J].南方文壇,2011(3).
[4] 許苗苗,許文郁.網絡文學的定義[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1).
[5] 歐陽友權.中國少數民族網絡文學20年巡禮[J].福建論壇,2018(10).
[6] 單小曦.數字文學的命名及其生產類型[J].中州學刊,2011(6).
[7] 陳定家,唐朝暉.網絡文學:揚帆出海正當時[J].文藝爭鳴,2019(3).
[8] 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M].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
[9] 李敬澤.網絡文學:文學自覺和文化自覺[N].人民日報,2014-07-25(24).
[10] 楊晨.網絡文學的內涵、創新及寫法[A].周志雄.網絡文學研究(第2輯)[C].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
[11] 范傳興.再談網絡文學的定義[A].周志雄.網絡文學研究(第2輯)[C].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
作 者: 劉志慧,阜陽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張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