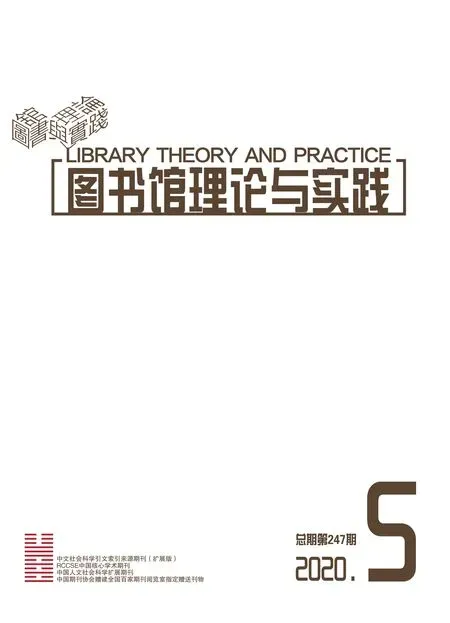黃純元先生及 “知識交流論” 思想研究
馬 敏,黃麗霞(黑龍江大學.信息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內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轉變,傳統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滯后性逐漸顯現,理論指導下的圖書館事業發展也凸顯出自身的不足,這就催生了學界理論研究的新高潮,如知識學、文獻交流論、情報交流論、知識交流論等,可以說它們在中國圖書館學本質研究史上起了 “開源” 的作用,其中宓浩和黃純元的 “知識交流論” 在提出之際便備受熱議,理論開創者之一的黃純元先生對知識交流論的提出和解讀是目前最為深刻的,他的很多觀點和見解一直影響至今。2019年是黃純元先生逝世20周年,筆者撰寫本文目的是在回顧學者圖書館學思想的同時讓更多的同行關注其學術貢獻,并借此文表達對黃先生的崇敬和懷念。
1 黃純元先生簡介
黃純元(1956—1999),上海人,1979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1988年考入東京大學攻讀圖書館情報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之后繼續攻讀教育學部圖書館學博士學位,至1996年完成博士課程回國,繼續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后于1997年獲得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
黃純元先生的學術生涯可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其赴日求學為界,留學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兩個:一是以社會科學為基礎,開展情報學、情報教育、情報機構及情報工作的研究,文摘服務及刊物研究,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二是關于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影響最廣的是他與恩師宓浩提出的 “知識交流論” 。在黃先生留學及之后期間,互聯網逐漸普及、信息化時代來臨,其基礎理論研究主要以信息社會為背景而展開。
2 知識交流論理論研究
2.1 理論解釋
“知識交流論” 以社會科學為基礎,以信息學和傳播學的相關內容為理論支撐,以滿足社會需要這一本質要求為理論闡述的基點,并將其貫穿于整個理論。宓浩和黃純元在《知識交流與交流的科學》一文中闡述了 “知識交流論” 的理論依據和基礎理論框架,而提出上述結論的關鍵在于回答了 “圖書館活動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我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應該從圖書館和社會內在聯系中,從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知識交流過程入手進行考察。”[1]其中的關鍵概念是 “個體知識” “社會知識” “文獻” “圖書館” 。在筆者看來,社會中個體認識差異性特征是產生知識交流的主要原因,通過文獻開展的知識交流是解決認知差異并實現人類文化傳遞和延伸的有效手段。圖書館為適應廣泛存在的知識交流這一社會需要而不斷調整運營模式,從我國古代的藏書樓、國外的經院,到近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雖然辦館理念及服務模式在不斷變化,但是不斷收集、整理、保存文獻的這一責任一直延續,這也是文獻背后的知識得以不斷延續傳承、知識交流得以實現的重要原因。
但該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之后,一度陷入停滯的狀態,學術界對于該理論的后續研究也是少之又少,十幾年后,黃純元發表《追問圖書館的本質:對知識交流論的再思考》才又一次掀起討論 “知識交流論” 的熱潮。黃純元先生通過謝拉的圖書館學思想變遷來前瞻 “交流理論的分化” ,[2]進一步分析了理論的不足之處:①知識交流的本質不能很好地、全面地解釋和適應于圖書館現象,制約了圖書館功能的發展;②文獻促使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知識交流達到同一性是 “知識交流論” 所追求的目標,但是隨著闡釋學、接受學等理論的發展,文本一旦產生其意義的闡述便不再局限于作者以及意義的無窮性。理論的不足和現實中的挫折導致該理論沒有形成完善的框架和體系,無法落實到圖書館事業的實踐中,但這也正使得學者們透過知識交流論從新的角度提出更適時的理論,呈現出 “百家爭鳴” 的局面。對于圖書館學 “元理論” 的追求是每一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者的夙愿,但是一味追求 “一元” 的理論很容易產生局限和固化,正如后現代圖書館學者所強調的多元化,不正是這種 “百家爭鳴” 的呈現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所產生的社會需求是圖書館作為一個服務行業適應時勢、不斷發展的基礎,社會性也應該是圖書館學理論發展的一個方向。
2.2 理論發展
知識交流論突破圖書館現實活動的表象,深入到更為抽象、內在的知識交流層次,將圖書館活動的意義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來指導實踐。在當時的圖書館學界,從知識交流的角度分析圖書館事業是注重價值理性的突出表現,相較于同階段盛行的 “新技術說” ,知識交流論更注重從人文主義的角度構筑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這對于圖書館學建立穩固的學科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自20世紀80年代提出至今,知識交流論對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啟發性的作用,如 “知識組織” “知識服務” “知識管理” “知識集合論” 以及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知識交流的課題等。
筆者以 “知識交流論” 為主題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發現目前關于該主題的論文主要是基礎理論創新研究和知識交流的專題研究。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新的角度出發,圍繞知識交流論的社會性特征開展研究,希望讀者能夠對黃純元先生以及他一直踐行的社會學科精神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3 知識交流論的影響
3.1 內在影響
3.1.1 基礎理論研究
黃純元先生在研究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時,將圖書館學置于社會范疇展開闡述。圖書館學認識層次的深入表現在認識主體的變化:從常規的圖書館活動到深入的知識、信息、情報。圖書館活動(如圖書借還)將用戶與圖書館聯系起來,滿足了用戶對于圖書館資源的需求,但它仍然局限于圖書館這一實體本身,缺乏社會性、廣泛性;而知識、信息、情報等微觀主體并非唯圖書館專有,且它們是常規圖書館活動表象下的共性存在,這種共性使得圖書館學更合理且更容易與其他學科建立聯系,這也是將圖書館學研究與社會現象和需求聯系起來的橋梁,故在此基礎上開展的圖書館活動不再是館內的專屬活動,而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可見,這是 “知識交流論” 的中心觀點,即以社會科學為研究背景、以滿足社會需求為根本,指導作者的基礎理論研究。
滿足社會需求不僅是黃純元先生開展基礎理論研究的基點、推進圖書館變革的理論支撐,同時也是規劃圖書館事業發展戰略、指導圖書館實踐的標準,即 “圖書館事業發展與否的唯一依據應當體現在和社會協調有序的程度上和滿足社會需要的能力上” 。[3]在過去以工作技術和方法為主導的圖書館學研究中,圖書館事業是一種靜態的發展模式,主要圍繞圖書館這一實體、利用館藏資源開展服務,是一種單向的輸出,這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圖書館知識資源中心的權威地位所決定的。隨著新技術、互聯網以及信息時代的到來,資源獲取的便利性和多元性使得圖書館需要改變單向輸出模式,以交互交流為方向,將 “圖書館活動歸屬于社會信息活動范疇” ,強調圖書館的中介作用,變被動為主動,將圖書館活動與事業發展及社會需求聯系起來,實現其社會效益。在作者看來,這樣的定位不僅是理論有效指導實踐的需要,也可以消除基礎理論研究的 “疏離感” 。
3.1.2 信息政策理論研究
我國關于信息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彼時信息社會逐漸取代工業社會,大量的國外譯著也推動了國內學者對信息政策的認識和研究。黃純元先生在讀博期間對日本的信息政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先生指出研究日本信息政策的形成和發展的目的是為了 “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信息控制” ,[4]并在借鑒日本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社會實際的基礎上為信息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議;之后,先生從 “用語使用的基本情況” 和 “政策問題群” 角度出發,對比分析了英國、美國、日本、中國對于 “信息政策” 的使用和研究情況,發現同一國家在不同時間段和不同領域對于信息政策理解的不同及不同國家社會發展進程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使信息政策研究極具多樣性。[5]此后,黃純元先生分析了信息政策問題形成的背景,即 “信息社會的政策需要” 和 “政策問題的綜合化” ,[6]而這也是先生提出認識框架和體系結構的關鍵。
這三篇信息政策理論的相關研究一直延續的一個思想是特定的信息社會環境和發展階段是研究信息政策的基礎,這是黃純元先生將社會性或稱社會需求貫穿于研究中的又一體現。分析國內的信息需求是我國制定信息政策、推動信息社會建設的依據和標準,實時關注國外的信息需求則是充實理論和前瞻研究熱點的重要輔助手段。信息鴻溝是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發展差距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學術理論界集中體現為理論研究的時滯性,因此開展信息政策方面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這是我國在信息社會中突破傳統、實現創新的關鍵。
3.2 外在影響
在知識交流論提出之后,很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框架對其進行完善補充。這些新理論的研究是將知識交流論中的部分觀點與其他學科理論或研究熱點及社會環境導向相結合而提出來的,即理論的分化。
3.2.1 知識組織理論
相較于 “知識交流” , “知識組織” 在國內外圖書情報學的研究中都走得更遠,盡管各國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但該理論的發展前景以及行業影響都遠遠超過了 “知識交流” 。筆者在中國知網中以 “知識組織” 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分析檢索結果后發現,學界一致認為劉洪波、蔣永福、王知津等學者真正意義上推動了 “知識組織” 理論的研究和發展。通過研讀劉、蔣二人關于知識組織的相關文獻,筆者發現兩位學者對于知識組織理論的研究均與 “知識交流論” 有一定的聯系。因此,筆者大膽推測, “知識交流論” 對 “知識組織論” 的提出和發展有一定的理論影響。相對于 “知識交流” ,盡管 “知識組織” 的理論基礎發生了改變( “知識交流” 強調交流, “知識組織” 重在分類),但兩種理論都將研究對象定位于 “知識” 單元,且均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種種共性都足以佐證 “知識交流” 對于 “知識組織” 的影響。
劉洪波是我國較早系統開展知識組織理論研究的學者,其研究成果對于后來者有很好的啟發性和引導性。劉洪波在關于知識組織理論的研究中,常將其與知識交流論一并作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認為二者是互補的關系,都是實現 “知識的社會化過程”[7](包括知識生產、知識組織、知識交流和知識利用)的一部分:知識組織是保證知識交流完成的前提,知識交流是實現知識組織目標(即實現知識社會化)的手段。筆者認為,劉洪波的研究更多的是為知識交流理論做補充,從來源、影響、解釋力等方面詳細闡述了該理論的合理性和意義,同時對理論批判的觀點進行了理性分析, “基礎理論的研究不具有直接運用于實踐的效能,它只有通過應用研究和技術研究的轉化才能產生作用” ,[8]而學者和實踐者不能很好認識這一觀點也是后期理論研究暫緩甚至停滯的原因。劉洪波認為,該理論過多強調圖書館知識交流的外向的社會功能,對于圖書館內部組織活動的理論解釋不足;他對圖書館內部活動的闡述依然是以知識為核心,以 “知識組織理論” 為理論支撐,并指出圖書館文獻收集整理的實質是對文獻中所包含知識的篩選和整序,而這一過程是實現知識交流的基礎。
與劉洪波不同,蔣永福認為 “有的學說直接把某一學科理論或某一學科理論的一部分觀點、結論拿過來認作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而沒有與圖書館實際深入融合” ,[9]也就是說存在拿來主義的傾向,這也是該理論在后期無法被普遍認同的主要原因。縱觀蔣永福關于知識組織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他不再只是從 “知識” 這個上位詞來考量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為了實現 “知識序化” 的目標,他將 “知識” 細化,從主觀知識和客觀知識的角度展開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提出了知識服務理論,認為知識組織和知識服務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圖書館活動。[10]其實,知識服務與知識利用意思相同,它們都表達了圖書館活動的宏愿,蔣永福將知識服務與知識組織一起納入到知識組織理論中,研究更為深入,這也是劉洪波與蔣永福在關于知識交流論的觀點中出現差異的重要原因。
3.2.2 其他理論貢獻
繼知識交流論之后,我國圖書館學界關于 “知識XX論” 的研究層出不窮,但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占據圖書館學 “元理論” 的位置,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而不能完全解釋圖書館學現象,也就是說不能勝任圖書館學本質的要求。那么,這樣孜孜不倦地追求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致力于挖掘圖書館學本質、為達到 “元” 的地位而竭力探索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這也就是后現代圖書館學者們所探討的問題。后現代主義追求價值多元,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學界的基礎理論研究中至今沒有提出一種獲得廣泛認同的圖書館學本原,這也是圖書館學界吸收后現代主義理論開展研究的一個原因。我國關于后現代主義圖書館學的研究以蔣永福先生的《不再追問本質:圖書館學理論的后現代走向》為起點,蔣先生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的成果非常豐富且有代表性,但后期他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對于圖書館學是否應該追求本質提出質疑,表示應該 “擯棄理性主義一元論的束縛,尊重價值觀之間的客觀差異性,從而走向多元價值觀之間的民主對話和博弈選擇,這就是圖書館學理論應然的后現代走向。”[11]
“知識交流論” 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開啟了我國圖書館學界對于 “元理論” 的探討,盡管很多學者都不將自己的理論定位為元理論,時刻保持著一種謙卑嚴謹的學術研究態度來接受其他學者的批評建議,但是探索圖書館學本質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同一觀點的研究越來越深、越走越遠,但是不同觀點之間的壁壘也越來越高,這其實對于理論發展是不利的,后現代圖書館學理論正是抓住了這一關鍵點開展研究,也許對于圖書館學理論研究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知識交流論的后續發展間接地對于后現代圖書館學的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 結語
黃純元先生在圖書情報學研究的道路上除受其恩師宓浩的引導外,自身對于圖書館學事業奮斗獻身、不斷求索的精神也是其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2019年是黃純元先生逝世20周年,筆者以 “知識交流論” 為中心回顧先生對圖書館學研究的貢獻,以表達對學界前輩的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