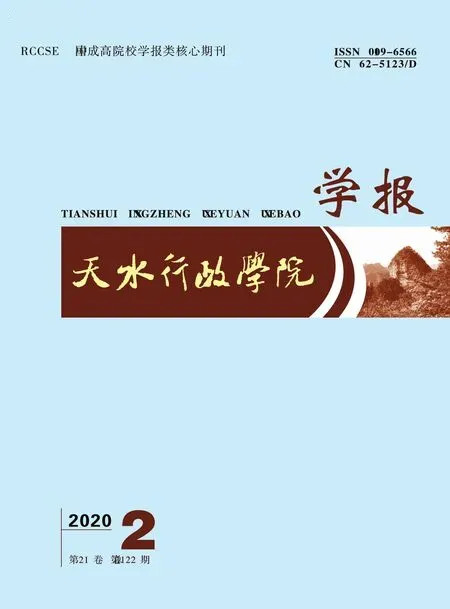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黃玉霞
(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875)
當今世界雖然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但仍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數十億人還在貧困中掙扎,消除貧困仍然是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目標。馬克思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致力于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他在指導工人階級革命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了科學的反貧困理論,對當今世界的貧困治理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現如今,經過幾十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仍有一小部分貧困人口的問題亟待解決,貧困仍然是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大挑戰。因此,深入分析馬克思的反貧困理論,對于打贏當前的脫貧攻堅戰,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貧困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基本內容
(一)貧困根源: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對貧困問題的分析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之上的,他在肯定資本主義社會所取得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了這種社會制度的弊端。不可否認,“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但是物質財富的絕對增長并不意味著貧困的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飛速發展也沒有改善工人階級窮困潦倒的處境,因為“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2]資產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后,通過一系列資本主義制度來剝削工人階級,無休止地榨取他們的剩余價值,導致工人階級處境艱難,愈發貧窮。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欺壓現象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3]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商品所需的生產資料和工人自身的勞動力相分離,資本家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工人為了養家糊口,不得已出賣自己的勞動,在肉體和精神上異化為機器,毫無自主能動性可言,并且無論工人生產多少產品,創造多少財富,都與工人本身無關,因為“勞動所產生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4]這種狀況所產生的結果必然是“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5]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勞動是導致工人階級貧困的重要原因,它不僅讓工人陷入貧困的境地,面臨物質匱乏的危險,同時也扭曲工人的本質,摧殘他們的精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6]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不僅使工人階級在經濟上遭受貧窮,精神上也極端匱乏,這種悲慘的境遇使馬克思更加關注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現象,從而為無產階級提供科學的指導。
(二)貧困后果:資本積累與相對過剩人口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困問題進行研究時,十分注重對剩余價值理論的分析和應用,并把它作為反貧困理論的重要支點。馬克思認為正是資本家無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的邏輯,才使得廣大無產階級被迫從事異化勞動、淪為生產機器、陷于極端貧困。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榨取并不是短期的一次性的行為,而是長期的持續性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通過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生產規模,進行資本積累,從而使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延續和發展。
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追求,是資本家進行資本積累的直接動機,因為“資本是死勞動,它就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7]在追求剩余價值的過程中,資本家不斷吮吸“活勞動”以達到資本積累的目的,隨著資本積累和生產技術的改進,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全部資本中不變資本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可變資本所占的比重逐步減少,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也逐步減少,其結果必然導致勞動者就業困難,形成大批的產業后備軍,出現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相對人口過剩。這種相對過剩人口實際上同赤貧是一回事,他們不但一無所有,而且無法通過勞動為自己謀取生活資料,于是就變成了赤貧。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也生產著大批的過剩人口,使得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程度不斷加深。資本主義制度一方面為少數人生產財富,另一方面為多數人制造貧困,這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反貧困目標: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大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更好地服務于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8]馬克思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始終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實踐性。馬克思曾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9]馬克思的反貧困理論在揭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工人階級貧困根源的同時,也為工人階級擺脫貧窮指明了出路——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
馬克思的反貧困理論實質上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從人的解放與自由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把無產階級這一受壓迫和剝削的群體從奴役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明白自身為什么貧窮,從而掌握這一思想理論武器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困現狀的分析來闡述自身的政治主張,指出無產階級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翻身覺醒、從自在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自覺組織起來要求改變自身現狀,才能逐步擺脫貧困,改變本階層和全人類的命運,這就為無產階級擺脫貧困指明了根本出路。
二、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路徑安排
(一)把制度革新作為反貧困的首要前提
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狀況,得出了無產階級整體性貧困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無產階級喪失生產和生活資料,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被資本家無情地榨取剩余價值,生活極端貧窮。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的狂熱追求者,在利潤的驅逐下泯滅道德和良心,通過不斷擴大資本主義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無止境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資本“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本身,因此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10]工人的死活從來不在資本家的考慮范圍之內,在金錢的問題上也從來沒有溫情可言。對資本家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榨取最大的剩余價值、謀求更多的利潤才是唯一要關心的事情,正是這種無休止的壓榨,導致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程度不斷加深。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進行制度革新,才能為無產階級反貧困創造先決條件,才能促進社會成員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反貧困的根本手段
在馬克思看來,發展生產力是反貧困的根本手段,“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1]發展生產力、生產物質生活是人類為了生存繁衍無時無刻不在從事的歷史活動,也是人類進行歷史活動的基本前提條件。資本主義社會正是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和變革才創造和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性質,導致階級矛盾激化,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無產階級貧困積累的歷史。
對于無產階級而言,要想改變被奴役剝削的命運,擺脫貧困的束縛,必須抓住生產力這一根本因素,通過推動生產力的不斷變革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自身的解放和發展。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而不是思想活動,“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12]無產階級只有在社會歷史實踐中,通過推動生產力的變革,逐步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系,才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人的解放。
三、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當代價值
(一)堅持走社會主義的反貧困道路
在馬克思看來,制度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一制度基礎上的生產方式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發,失業和相對人口過剩不斷加劇,無產階級愈發貧窮,最終導致階級矛盾不斷激化,資本主義社會走向消亡。因此,建立一種有別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的理性制度選擇。建國初期,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立足于中國國情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13]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把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出了一系列扶貧開發的國家戰略,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重要的戰略部署。
黨的歷代領導集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始終堅持不忘初心,把改善民生、消除貧困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這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在社會主義制度層面的生動反映,體現著反貧困實踐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不斷深化與發展。現如今,經過70 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社會主義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社會主義制度展現著蓬勃的朝氣與活力。在看到這些發展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實際情況,這些最基本的發展事實時刻提醒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們立黨立國的基本出發點,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決地貫徹執行。
(二)堅持依靠發展生產力解決貧困問題
作為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大難題,貧困的產生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它不僅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毫無疑問,制度變革為消除貧困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但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意味著貧困的絕對消除。換言之,制度變革只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其全部內涵。馬克思反貧困理論的價值目標就在于通過發展生產力逐步消除貧困,從而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條件。在這一點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指出:“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內生產力水平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后來鄧小平又將這一思想升華為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要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貧窮,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論述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具有資本主義社會所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十八大以來,國家更是高度重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出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這一點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15]”這一論述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思想,對于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逐步消除貧困、實現共享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堅持把扶貧開發作為改善人民生活的攻堅之舉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把人民的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這既是黨的執政理念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選擇。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是要關心人民,尤其是最底層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扶貧工作無疑就是關心人民利益的最好體現。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帶領人民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使6 億多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在反貧困事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就目前來看,中國的貧困形勢依然嚴峻,仍有一部分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亟待解決,貧困問題仍然是影響經濟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一大挑戰。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把扶貧攻堅擺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來保證扶貧開發工作的順利進行。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從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與新時代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相結合,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戰略思想,并把它作為新時代貧困治理的攻堅舉措,在政策幫扶、資金調配上采取更大的力度和更強的針對性措施,開啟了規模更大、覆蓋更廣、更有針對性的扶貧工作,并且立志“確保到2020 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16]“精準扶貧”理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在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又是中國共產黨貧困治理的一大創新成果,對打贏當前的脫貧攻堅戰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與貧困作斗爭的歷史。為了解決這一大歷史難題,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在實踐過程中進行了多種嘗試和制度創新,試圖從根源上消除貧困,但是由于其階級和時代局限性,最后往往以失敗告終。馬克思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畢生都在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孜孜奮斗,其創立的反貧困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無可比擬的科學性、時代性和生命力,對我們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貧困治理和反貧困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是反貧困事業取得最終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因此,我們要更加充分地利用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扶貧事業,推動中國扶貧事業早日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