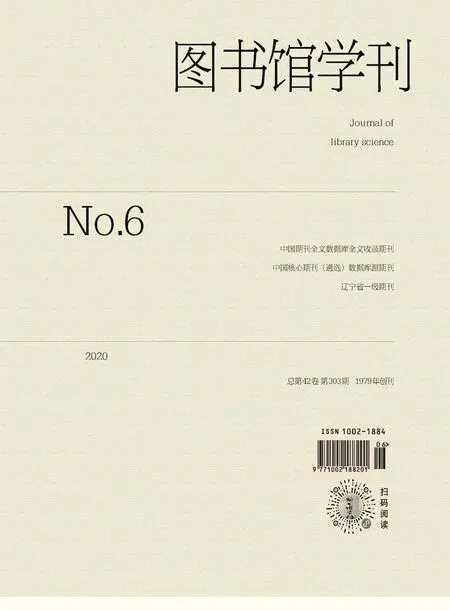《真臘風土記》的文獻價值*
田明偉
(溫州大學,浙江 溫州 325035)
真臘曾是扶南古國北部屬國,公元7世紀并扶南自立,遷都吳哥,10至13世紀是柬埔寨文明最輝煌的時代,也稱吳哥時代。《真臘風土記》是反映13世紀末吳哥時代的著作。該書記載詳實、生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之為“文義頗為賅瞻”。目前學界對該書的研究多聚焦在版本考訂與校注上,缺乏對其文獻價值的深入挖掘。
1《真臘風土記》的作者
作者為周達觀,元代溫州人。在不同文獻中,作者名字有差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真臘風土記》一卷,元周達觀撰。達觀,溫州人。”[1]清代錢曾《讀書敏求記》記載:“周建觀《真臘風土記》一卷。”[2]此處的“建”字應該是“達”字的誤書。清人孫詒讓《溫州經籍志》記載為:“周草庭《真臘風土記》,元貞元年隨使諭真臘時所作”[3]。此處的“草庭”應該為周達觀的字號。元人吾邱衍所撰贈詩三首則記錄為《周達可隨奉使過真臘國作書紀風俗因贈三首》[4],這里的“達可”應該是“達觀”的又名。“周達觀本人沒有當過官,他出使真臘是作為欽使隨員身份,并非朝廷命官。后來自號草庭逸民,正好反映他結廬草庭,無官無職,以逸民自居的生活情況。”[5]
周達觀為元人林坤《誠齋雜記》作序時自稱“永嘉周達觀”。[6]廣義來講,溫州即是永嘉,位于今浙江省。狹義來稱,則今日溫州為市,永嘉為縣,溫州更接近甌江出海口,永嘉縣則位于甌江北側。溫州地區自來就是貿易城市,有海港之利,宋元時期與海外的關系十分密切,宋朝開始,這里置市舶司。在哲學觀念上,也能發展與商業功利相映的思想,產生溫州的永嘉學派是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鼎足而三的學術流派,該學派顯著特點就是強調功利。作為具備對外商業交通視野的溫州人,周達觀在隨團去真臘前,可能已經跟來往溫州的商人學會了一些柬埔寨語。“正是由于他通曉柬埔寨語的緣故,招諭真臘的使節從溫州開洋的時候,周達觀才得以隨使同行。”[7]
作者在該書序言曰:“元貞之乙未六月,圣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徳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8]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即公元1295年周達觀接到隨使前往真臘的命令后,經過8個月的準備工作,在元貞二年,即公元1296年3月24日從溫州港出發。公元1296年4月18日到達東南亞的占城(今越南)。之后又經過3個多月的航行最終到達真臘。周達觀所在的使團在真臘停留約一年的時間,于大德元年,即公元1297年決定回國,用了近兩月時間,即公元1297年8月30日抵達今浙江寧波。若以返國后一年寫成,則《真臘風土記》成書的年代可定為公元1298年[9]。
2《真臘風土記》的內容與版本
全書大約8500字左右,卷首是“總敘”,其他內容分40則,記當時柬埔寨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經濟活動(農業、工業、貿易)、建筑、雕刻,及中國和柬埔寨人民友好通商關系。“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10]然而該書在章節構架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現在各章節內容詳略不一,缺乏一定的連貫性。
該書迄今刊本、抄本有十余種。涵芬樓百卷本《說郛》本,又稱《郛》甲本,元末陶宗儀編,近人張宗祥輯佚,1927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明嘉靖年刊陸輯等輯的《古今說海》本。明刊李拭輯的《歷代小史》本,刊行于隆慶萬歷年間,今有商務印書館《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1940年。明刊吳琯輯的《古今逸史》本,萬歷刊本,今有商務印書館《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1940年。明重輯《百川學海》本。清初重定陶氏重輯《說郛》本,《郛》乙本。清《古今圖書集成》本,清雍正四年(1726年)刊本,今有1934年中華書局縮印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文津閣本。清瑞安許氏刊本,道光己丑(1829)年巾箱本,1963年杭州古籍書店重印。清吳翌鳳手抄本,原為李盛鐸藏書,今歸北京大學圖書館。民國王輯《說郛》本,民國四年(1915年),王文濡編,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馮承鈞譯伯希和《真臘風土記箋注》本,1957年中華書局出版《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本,簡稱“馮本”。清《舊小說》本,清吳曾祺編,宣統庚戌(1910年)商務排印本。清《香艷叢書》本,清蟲天子輯,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11]。
3《真臘風土記》的評介和校點
該書早期并未引起學界關注,直到19世紀初期繼法國殖民者侵入印度支那之后,法國“漢學家”開始注意這本書。隨著世界第七大奇跡吳哥窟以及對吳哥文明的發現,《真臘風土記》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1819年J.P.A.雷慕莎曾根據《古今圖書集成》本譯成法文。1902年伯希和根據《古今說海》本譯成新的法譯本,并加注釋。1936年,松楓居主人將其翻譯成日文。1967年該書英文本出版。1971年柬埔寨作家李添丁出版柬埔寨文版《真臘風土記》。很快引起中國學者興趣,1975年香港陳正祥出版《真臘風土記研究》;1976年臺灣金榮華出版《真臘風土記校注》;1981年夏鼐出版《真臘風土記校注》,該書考究完善,注釋翔實,學術價值也最大。1999年段立生在《世界歷史》發表《泰國帕儂諾石宮遺址和真臘古史補證》,根據新發現的泰國帕儂諾石宮遺址考察了真臘國的版圖、宗教信仰和政治統治、民俗風情,補充了真臘古史的部分空白。2007年鄧文寬在《中華文史論叢》上發表《中國古代歷日文化對柬埔寨的影響——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讀記》,根據《真臘風土記》第13則的歷法使用考證“真臘”使用的歷法當為秦朝歷法,只有少數是西方歷法,真臘受中華文化影響則是無疑。2015年蔡貽象在《公共外交季刊》撰文《元朝周達觀出使柬埔寨及今日意義》一文主要從外交角度闡釋了周達觀出使對當今國際交流的價值,具有新時代的意義。
4《真臘風土記》的文獻價值
該書是存世的同時代人描述吳哥文化極盛時代的唯一記載,是世上僅存最早介紹真臘吳哥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歷史文獻,甚至連柬埔寨文獻中,也找不到這種中古時代文物風俗生活的記載。不僅保存了中柬兩國人民之間經濟聯系和文化交流的史料,還詳細地記錄了溫州往返真臘的航海路線,同時呈現出元代知識分子對域外的觀察視角及心態,豐富了中外關系史研究資料。
4.1 保存中柬兩國經濟文化交流史料
《真臘風土記》記載中柬兩國人民之間的經濟聯系主要體現在兩國人員往來和商品貿易上。《真臘風土記·異事》有記:“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12]南宋末年周達觀的溫州同鄉薛氏就在柬埔寨生活了。《真臘風土記·流寓》又載:“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于彼。”[13]周達觀認為華人來柬埔寨,是因為國內生活所迫。并且“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14]中國人在柬埔寨還得到了當地人的尊敬,“往年土人最樸,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為佛,見則伏地頂禮。”[15]《真臘風土記·欲得唐貨》載:“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為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瓷器……”[16]可見,元代溫州漆器與中國的金銀、絲織品、錫器、青瓷器等在當時的柬埔寨都是廣受歡迎的商品,享有很高的聲譽。而在中國市場上備受青睞的真臘象牙、犀角、黃臘等商品,也正說明兩國經濟交往的頻繁與廣泛。
書中反映出中柬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當時柬埔寨的喪葬習俗,“人死無棺,止以差席之類,蓋之以布。抬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17]隨著“唐人”來到柬埔寨后,“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往往皆唐人之遺種也。”[18]中國的火葬習俗在柬埔寨逐漸興盛起來。當時柬埔寨的歷法“每用中國十月以為正月。是月也,名為佳得。”[19]以農歷十月為一年首月正是中國秦朝的歷法。
柬埔寨因為古文明沒落,加上近代戰爭頻繁等原因,除少數石碑文保存部分史料外,幾乎所有的古史資料均已消失殆盡,《真臘風土記》是唯一一部關于古代柬埔寨的文獻著作,可彌補柬埔寨古史之不足。柬埔寨學者李添丁稱贊“這本書是一部研究柬埔寨歷史的寶貴資料。迄今為止,有關柬埔寨的任何歷史書籍和教科書都沒有超過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20]“人們將《真臘風土記》的功勞,與《大唐西域記》指導英國人和印度人發掘那爛陀古廟相媲美,由此可知關于吳哥古城的歷史材料十分珍貴。”[2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然元史不立真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22]
4.2 詳細記錄溫州往返真臘的航海路線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關系發展的極盛時期。從馬背上崛起的蒙古統治者往往采用開放的對外政策,積極支持海內外商業貿易。如對大運河的修通、海道的開發和陸上驛站的設立尤為重視,并在各港口設立市舶司(泉州、慶元、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等地),管理海外貿易。此時的中國在科技、航海上的技術都已臻成熟。“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對海外交通的發展,也有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海船的載重量和抗沉性能都有明顯的提高。”[23]《真臘風土記》總序中說:“過昆侖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余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24]周達觀一行人所乘坐的巨船,吃水較深,在岸邊的港口都無法停靠,只有所謂“第四港”的港口可以進入,說明了元代造船技術的先進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不僅如此,“總序”中詳細介紹了此次出訪的航線,如何從中國出發?走哪條海路?遇到何種困難?最后是怎樣回國?都為后人留下了準確的記載。總序又說“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昆侖洋入港。”[25]這里所謂的“丁未針”及“坤申針”,即是羅盤定位。其準確的方位角,夏鼐先生解釋為“‘丁未針’之方向為‘南南西’,即二百零二度三十分(方位角),或‘南二十二度三十分西(方位)’。‘坤申針’之方向為‘南西1/6西’,亦即二百三十二度三十分(方位角),或‘南五十二度三十分西(方位角)’。”[26]這樣的考證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方位,完全可以還原出當日周達觀的航行路線。即是從今溫州出發,然后往西南經過臺灣海峽,再走到海南島右下的海域,最后沿著南中國海一路而下,在越南等地暫停補給,最后由湄公河的出海口,沿河北上進入真臘,路線非常清晰,給后代商船留下了一個可靠的依據。《真臘風土記》詳細地記錄了溫州往返真臘的針位,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記有針位的書籍。
4.3 呈現元代溫州知識分子域外觀察視角心態
周達觀出使真臘是作為欽使隨員身份,并非朝廷命官,他在寫《真臘風土記》時,較少受到修撰地方志書體例上的束縛。所以無論是他的觀察視角還是心態,無不反映出傳統士大夫對域外風俗的好奇心及觀念上的偏執。讓讀者深切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如,第37則“澡浴”為例:“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澡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于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為恥。”[27]周達觀在真臘看到吳哥婦女脫衣入水澡浴的情景,以中國人傳統的思維觀念看待異域風俗,認為這是羞恥的。從地理學上看,今日柬埔寨處于熱帶,尤其在夏天氣溫高達40攝氏度,在這種環境下,當地居民脫衣戶外澡浴本來就屬于正常之事。甚至今日吳哥一帶,仍有許多婦女洗浴習慣與七百年前周達觀所見相同。周達觀帶著儒家傳統知識分子的眼光去觀察域外的真臘風土人情時,不免帶有蔑視的態度,所記載內容也局限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視野。當他所見所聞與自己接受的傳統教育有悖時,內心充滿了矛盾與焦慮。這也正是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常態。周達觀對真臘風俗的觀察視角為今天研究中外關系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之前不被重視的私人撰寫文獻,也逐漸進入到研究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