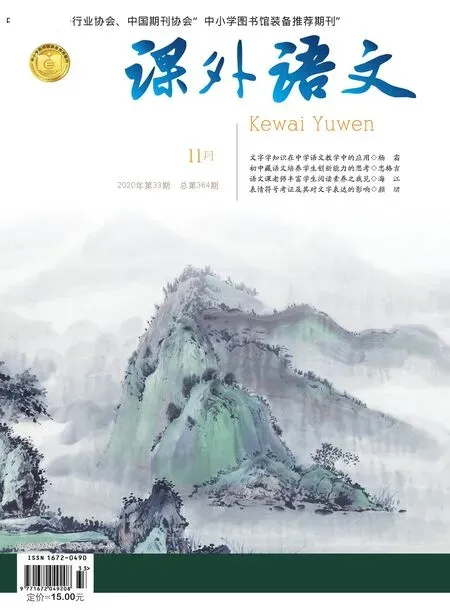淺談魯迅作品對初中記敘文寫作選材教學的啟發
——以部編版初中語文教材中魯迅作品為例
周 晨
(江蘇省無錫市梅里中學,江蘇 無錫 214000)
引言
中學階段學習魯迅作品,有利于促進學生自身人格的養成以及道德修養的提高。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說:“魯迅是語文教學的一個難點和重點,但是同時他還是一把金鑰匙,一旦把魯迅拿下,學生過了魯迅這一關,他不可能不喜歡語文,他不可能不喜歡作文。”對中學生而言,魯迅作品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跨欄。魯迅的“嬉笑怒罵”式文體,使學生對魯迅作品產生某種“抗拒”,從而難以對其作品作深層理解,更不用說運用到寫作中。然而,從選材角度看,魯迅作品對初中生記敘文的寫作還是有很大的啟發。
初中階段的寫作學習主要集中在記敘文的訓練。記敘文的選材決定了整篇文章的走勢,是作品的血肉軀體,它能吸引人眼球、能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這是文章可讀性的前提。因此,寫好記敘文,最關鍵的是選材,選到了一個好的材料,文章就成功了一半。
一、部編版初中語文教材中魯迅作品選編淺析
部編版語文教材初中階段一共收錄了七篇魯迅先生的作品。從整體來看,是從不太有閱讀障礙的回憶性散文入手,使剛進入初中的孩子在心理上有較強的認同感,所以選自魯迅散文集《朝花夕拾》的三篇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長與〈山海經〉》《藤野先生》分別安排在七年級上下冊以及八年級上冊。《朝花夕拾》多側面地反映了作者魯迅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經過。此書也是七年級上冊的必讀名著,由此可窺探出此書的意義重大。
而人物更多、性格更復雜的短篇小說《社戲》《故鄉》《孔乙己》安排在之后,都收錄在魯迅短篇小說集《吶喊》中。此小說集具有深刻的社會與歷史意義,描繪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時期的社會生活,揭示了種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對舊時中國的制度及部分陳腐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較徹底的否定,表現出對民族生存濃重的憂患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強烈希望。初三學生正是人生三觀開始形成的時候,所以將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安排在九年級上冊是很明智的選擇。此篇雜文,作于九一八事變三周年之際,鼓舞了民族自信心和抗日斗志。
二、魯迅作品對初中記敘文寫作選材的啟發
我們對魯迅作品的學習,除了讓我們感受、理解魯迅在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心境與思想并感知他的語言風格之外,還要品讀他的選材。品讀魯迅先生的這幾篇散文和小說,你會發覺這給初中生記敘文寫作選材主要有兩方面的啟示:記述源于生活的事件和敘寫有生活原型的人物。
(一)記述源于生活的事件,以“憶童年”主題為例
魯迅先生的“童年”題材作品,給中學生記敘文寫作的有益啟示是選取自己生命中記憶深刻、對自我有重大影響、源于生活的事件。童年是富有意趣的、天真的,魯迅的童年生活也不乏這些幸福的亮點,作者寫作時很自然地把它們攫取出來,字里行間流露出先生悠然的回憶。這些事件,重要的是對于作者自我的意義,而不是在別人看來重要不重要。在寫作時,如何將宏大的、抽象的意象投注到文字中,也許將其具體化、縮小化,會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童年所有樂園的形象都具象化,具體到“百草園”之中。如果將童年樂園“百草園”比喻成一個舞臺,其中的選材就如同舞臺劇中的角色,一個個登臺演出,但是主角只能是于作者新奇的、有趣的物、人、事,這些對于當時是孩子的作者來說是最重要的。
所以夏天的故事中少不了童年陰影“美女蛇”,這是極富戲劇性的一個選材,體現童年時期故事對人思想的影響,那么我們學生可以模仿魯迅先生,找尋記憶中對自己思想產生影響的故事,并將它作為題材寫到作文中去。
所以冬天的童年當然是少不了堆雪人,但是這個選材比較“大眾”,不夠新奇有趣,而魯迅先生選擇的是“捕鳥”。紹興舊時帶有濃郁地方色彩的捕鳥方法,獨到又有趣,這當然是建立在童年時親身經歷過的趣事之上才能寫出。又如童年“三味書屋”讀書生涯的記錄。在上學的千篇一律的讀書、習字和對課的枯燥生活中,對于孩童來說生活的亮點是什么呢?作者和讀者都喜歡跑到園子里玩耍、描繡像畫等畫面。因此,要摒棄老套的選材思路,開拓選材的視野。
《社戲》這篇小說以作者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為依據,描述幾次看戲的經歷。但真正寫社戲的內容并不多,魯迅用不少筆墨在開頭寫“我”到外祖母家的其他生活以及看社戲遇到的困難,在結尾又寫了六一公公送羅漢豆的事。作者所懷戀的不是社戲本身,而是在看社戲過程中與農家孩子結下的誠摯友誼和農村的自由生活。“社戲”作為一條線索,在文中起著貫穿故事情節的作用。所以在寫作中,借用“線索”也是很高明的一種方法,借用一個意象一以貫之,起到前后情節、情感的連接,從而達到主題主旨順其自然地顯露。
再如《阿長與〈山海經〉》中要體現一位舊農村婦女長媽媽善良、樸實而又迷信、嘮叨的形象,以孩童的眼光記述睡覺成“大”字、教我一堆麻煩的禮節、給我買來《山海經》等事件。此篇給我們的更大啟發在于“角色視角轉換”。魯迅寫回憶童年,就將自己置于孩童的視角,寫什么就以什么視角,使得讀者的代入感很強,很容易對人物產生深刻的印象。
(二)敘寫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
敘事離不開寫人,魯迅筆下的人物個性鮮明,都是真正的“人”。每個人物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性格都是尋常的人性,沒有特意為了表示主題而刻意塑造“超人”,這是魯迅對待文學的真誠。為什么能如此呢?因為作者都是敘寫有生活原型的人物。通過外貌、動作、語言、心理、神態等多角度、多方法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
1.外貌描寫。寫人,往往先從第一印象的外貌入手。魯迅作品中對人物的外貌描寫大多使用白描的手法,直接且直觀。如《藤野先生》中“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迭大大小小的書”。寥寥幾筆的速寫,寫出了藤野先生的簡單樸素和不拘小節。個人形象的粗糙是以留級生的描述,“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并以在公車上會被人當作扒手來展現的。
再如《故鄉》中描寫楊二嫂:“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和之前“豆腐西施”的溫柔形象大相徑庭,對比之間更顯出如今楊二嫂的刻薄小市民形象。
又如《孔乙己》,一開始沒有直接描述孔乙己的外貌,而是先講述了短衫人站著喝酒與長衫人坐著喝酒的區別,從而引出“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這樣一個落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穿長衫是科舉時代讀書人的象征,而孔乙己的長衫卻“又臟又破”,長期不洗不補,既說明孔乙己很窮,只有一件長衫,又說明他很懶,連洗補衣服都不肯動手。不肯脫下這么一件長衫,是唯恐失去他讀書人的身份。
2.語言描寫。語言描寫的靈動也是寫作功力的體現,語言要富有人物的性格。如《故鄉》中對楊二嫂剛出場的語言描寫:“哈!這模樣了!胡子這么長了!”“不認識了么?我還抱過你咧!”“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大轎,還說不闊?嚇,什么都瞞不過我。”“阿呀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不肯放松,便愈有錢……”通過這些語言,生動準確地刻畫出楊二嫂尖刻勢利、愛搬弄是非的小市民嘴臉。又如《孔乙己》中孔乙己這個迂腐的舊知識分子形象就是滿嘴的“之乎者也”,“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這些經典語言總被學生們喜歡,但寫作時卻用對話來湊字數,充滿了無效信息。因此,讓學生明白,選用的人物的語言要為人物形象服務。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想在寫作中擁有獨到的選材,我們可以從魯迅的作品中學到:一是源于生活,感悟其中;二是將題材細致化,借用“線索”貫穿全文,承前啟后;三是角色視角轉換,寫什么就轉換成什么視角,切換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