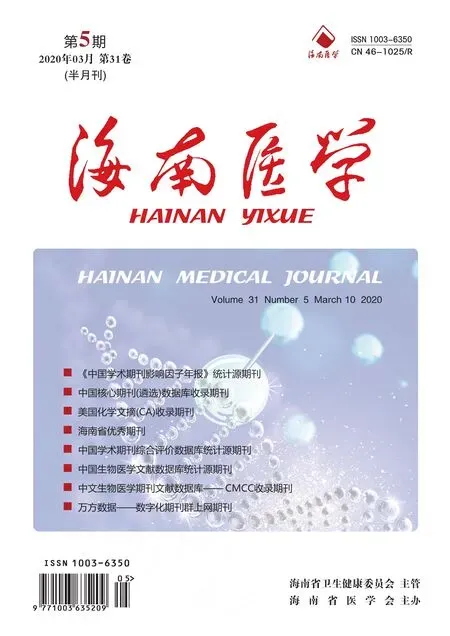磁共振成像和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在垂體腺瘤患者視功能評估中的應用
梁海瑩 綜述 龐燕華,李瑞莊審校
廣東醫科大學,廣東 湛江 524000
垂體腺瘤是一種起源于垂體前葉的顱內腫瘤,EZZAT 等[1]報道患病率為16.7%。視覺功能障礙是垂體腺瘤最常見的癥狀之一,它是由視交叉的直接壓迫或視交叉血液供應系統的紊亂引起的[2-5]。垂體位于硬腦膜袋內,附著于蝶鞍橫膈膜的下側[6]。垂體腺瘤很容易向周圍擴張[6-7],視交叉位于垂體上方,當腫瘤生長到鞍外時,壓迫前視覺通路引起軸突變性,導致視網膜神經纖維層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RNFL) 厚度變薄,常常會引起視覺障礙,例如由于視交叉壓迫導致視力下降或視野缺損[8-15]。因此評估腫瘤的壓迫效應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影響垂體腺瘤患者的治療和預后[16]。
視交叉受壓后可通過手術或醫學手段恢復部分視功能。然而,最佳治療時間窗期尚不清楚,也沒有經過驗證的能促進視力恢復的預測因素[17]。目前認為可能影響術后視功能恢復的各種因素包括腫瘤生長速度、交叉壓迫的嚴重程度、腫瘤大小、視網膜神經纖維層厚度和視力障礙持續時間[17-22]。
磁共振成像 (MRI) 是指導垂體腫瘤患者治療計劃的主要診斷工具。垂體腺瘤壓迫效應的標準臨床評估是基于常規MRI 和神經眼科檢查。常規MRI 將確定腫瘤的大小及其與周圍結構的關系,但不能檢測視覺通路的功能性和可能的微結構損傷。對表現為嚴重視力喪失的患者的處理是相對明確的;對于具有輕度到無視力喪失的患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視力有可能逐漸下降,確定手術干預的最佳時機,就不那么確定了。
檢測視覺通路的功能性和可能的微結構損傷可以通過光學相干斷層掃描 (OCT) 客觀地評估[17,23-27]。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儀是超聲的光學模擬品,可進行活體眼組織顯微鏡結構的非接觸式、非侵入性斷層成像,其軸向分辨率取決于光源的相干特性,可達10 μm,且穿透深度幾乎不受眼透明屈光介質的限制,可觀察眼前節,又能顯示眼后節的形態結構,在眼內疾病尤其是視網膜疾病的診斷、隨訪觀察及治療效果評價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28]。
本文針對磁共振成像和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對垂體腺瘤患者視功能評估進行簡要綜述。
1 垂體腺瘤損害視功能的機制
典型的垂體瘤生長主要向上突破鞍膈,直接壓迫視交叉,或影響視交叉血供,導致雙眼顳側視野缺損。隨著腫瘤生長,累及到未交叉的視神經時導致鼻側視野和視敏度下降。無論是受壓還是缺血損傷,神經節細胞均可發生軸漿流運輸受阻,軸突變性、壞死,繼而萎縮消失[29]。OCT 檢查較檢眼鏡更為早期的在視網膜上發現這種軸突變性所造成的結構性改變。
早期垂體腺瘤壓迫視交叉導致軸漿流動紊亂、傳導受阻和脫髓鞘是可逆的。更長時間或更嚴重的壓迫導致軸索纖維變性和視神經萎縮是不可逆的。輕微的萎縮可能沒有功能影響。然而,進展性視神經萎縮導致視力下降和視力損害,即使在手術減壓后仍可持續進展[30]。
有研究表明,即使垂體腺瘤直徑小于1 cm,也可以發現視力損害。損傷程度直接取決于腺瘤的直徑和視路上壓迫的位置[31]。SADE 等[32]還發現,患者的視神經扭轉角<114.5°可能對視神經造成潛在的不可逆損壞。對于視神經管口的這種不可逆損傷,存在兩種可能的機制:其一是鐮狀韌帶壓迫造成的直接損傷;其二是扭轉角引起的血流動力學并發癥。在鞍上大腫瘤中,視神經管開口處的鐮狀韌帶壓迫了視神經[32]。因此,視神經管減壓術適用于前路鐮刀狀切除韌帶和視神經鞘開口[32],關于血液動力學并發癥,HOYT等[33]報道由于垂體大腺瘤引起的視神經壓迫破壞了視神經的供血,視神經內動脈、靜脈和毛細血管網的長期壓迫導致停滯性缺氧,這些機制對視神經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累積或累加效應。
2 垂體腺瘤患者的磁共振成像
目前MRI是垂體病變的首選影像學方法,在顯示垂體病變輪廓和確定腫瘤與鞍旁軟組織結構的關系方面優于CT。
在MRI冠狀位上,頸內動脈海綿竇段是最明顯且較為恒定的標志,因此可以將頸內動脈海綿竇段上緣連線為測量垂體瘤冠狀位相對高度的標準線,腫瘤向上生長突破鞍膈,在冠狀位上為啞鈴狀稱之為“束腰征”,MRI檢查可顯示視交叉受壓情況;在MRI正中矢狀位上,額底—鞍背上緣連線水平相對固定,用以作為測量垂體瘤正中矢狀位高度的標準線[34]。
MRI 可以從三維結構上了解腫瘤的大小與周圍結構的關系。根據腫瘤大小進行MRI診斷,垂體腺瘤在大體形態上可分為:直徑<1.0 cm 為微腺瘤、直徑>1.0 cm 為大腺瘤和直徑>3.0 cm 為巨大腺瘤。垂體的高度是診斷的主要指標,如果高度超過8 mm,即有臨床意義[34]。
垂體瘤高度在常規MRI 掃描中,可以根據Tl 冠狀位表現分級:0 級是腫瘤上緣與視神經之間有空隙;1 級是腫瘤上緣觸及視神經,但視神經未變形;2級是腫瘤上緣壓迫視神經,使之變形:3 級是腫瘤壓迫的視神經上緣己接觸到三腦室底;4 級是三腦室底變形[35]。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的質量和可用性的提高,使其在垂體瘤患者的治療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預測視覺功能障礙和手術結果方面[18,36-37],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影像學模型來量化視覺設備的變形。包括視交叉橫截面積、視交叉高度、腫瘤高度、視交叉與腫瘤的空間關系、視神經萎縮和信號改變[18,22,35-39]。但這些模型要么顯示出混合的結果,要么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例如,EDA 等[22]報告了交叉和腫瘤之間的空間關系與視覺障礙程度相關,而池田和吉本剛明[40]則提出交叉和腫瘤的相對位置在視覺功能障礙中不起作用。另一種常用的放射學測量方法是腫瘤大小[22,38]。潛在的這種結構模型的顯著局限性在于垂體瘤的高度和體積都受鞍區解剖變異和腫瘤生長方向的影響。
MONTEIRO 等[365在確定視覺功能和手術結果時檢查了交叉位置和視神經萎縮,并使用多變量分析發現,視力恢復的最佳預測因子是視神經萎縮的嚴重程度與視野喪失程度和測量的視交叉抬高。但是,視神經萎縮的臨床應用受到其主觀性質和MRI 圖像質量的限制。TOKUMARU 等[39]也研究了視神經信號強度作為視覺恢復的潛在預測因素的作用,但發現只有疾病持續時間與術后視力改善相關。這種限定信號變化的結構分析與上述視神經萎縮的挑戰相似。由于缺乏具有預測能力的客觀放射學模型,在根據垂體瘤的結構特征對垂體瘤擴大患者進行評估和分型時面臨著一個持續的難題。理想情況下,治療決策應包括有關視覺通路結構變化的信息,這些信息是客觀的、容易再現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和對治療后視覺恢復的預測。此外,對視覺功能的全面評估仍然是臨床決策的主要驅動力,而神經影像學則是輔助信息來源。
雖然基于MRI 的結構分析是垂體瘤患者治療的一個重要和有用的工具,但是有限的客觀指標可以預測術后視力恢復。因此,有必要繼續研究前視路結構和功能完整性的新的假定標志物,例如光學相干斷層掃描。
3 垂體腺瘤患者的光學相干斷層掃描
隨著眼科醫師對視網膜變化、視功能惡化和視交叉損害之間密切關系的了解,視網膜逐漸成為垂體腺瘤患者視覺恢復的研究重點。光學相干斷層掃描提供視網膜層的非侵入性橫斷面成像[41],已被用于評估垂體腺瘤引起的視網膜形態學變化,并探討視網膜層厚度與患者視覺功能之間的關系[42-45]。
當視交叉被直接壓迫或其血液供應系統受到垂體腺瘤干擾時,可能會發生軸索損傷和功能障礙和/或視網膜神經節細胞 (retinal ganglion cell,RGC) 的凋亡[3,23,26,46-47],導致RNFL 和神經節細胞內從狀層 (ganglion cell and inner plexiform layer,GCIPL) 變薄。鼻側視網膜主要受其與視交叉中交叉神經纖維的聯系所影響。隨著病變部位和視交叉受壓位置的變化,以及視交叉損傷的加重,顳側視網膜也因損傷的纖維而變薄。
腫瘤對視交叉的緩慢和慢性壓迫可能導致軸漿停滯和血管伸展,從而阻礙視交叉的血液供應。RNFL 厚度的丟失在所有節段均彌漫性發生。RNFL變薄反映了視網膜神經節細胞變性的程度,并與視野喪失的嚴重程度相關[26]。在垂體大腺瘤患者中,術前RNFL厚度較薄表明視力和視野損失更嚴重[48]。這種損害是永久性的,即使在治療后也會持續;它是導致長期視覺缺陷的原因[27]。
垂體腺瘤向上壓迫視交叉,以雙顳葉偏盲為特征,經蝶手術是治療這些病變的有效的方法。術后視力恢復是需要關注的問題,許多研究探討了視力預后的預測因素。視覺結果與多種因素相關,如腫瘤大小和癥狀持續時間[36,49-50],但直接評估視神經功能可能是重要的。檢眼鏡是一種傳統但被廣泛接受的診斷方法。檢眼鏡檢查發現的視盤萎縮被認為是嚴重的視神經損傷,并與經蝶竇手術后視力恢復不足有關。相比之下,腫瘤鞍上延伸的患者有時會出現視盤萎縮,但在腫瘤切除后視力損害會恢復。因此,需要更有效的方法來評估視神經狀況。
在前視覺通路壓迫的情況下,有兩種結構值得分析:其一是OCT可以測量視乳頭周圍視網膜神經纖維層 (pRNFL) 厚度,并估計構成視神經的神經節細胞軸突的數量。其分析提供平均RNFL 值和每象限的值 (顳、鼻、上和下) ;其二是OCT 可以測量黃斑神經節細胞復合體 (ganglion cell complex,GCC) 。GCC 包括視網膜神經節細胞層 (由神經節細胞的細胞核組成) 和內網狀層 (由神經節細胞的樹突形成) 。
垂體腺瘤可以誘導RNFL 變薄,這反映了由前視覺通路受壓引起的軸突變性。RNFL丟失是一種可重復且有用的標記物,用于診斷和隨訪幾種神經系統疾病中的視神經軸突損傷[51-54],包括垂體腺瘤[24]。
視交叉的壓迫與較薄的鼻側和顳側RNFL 有關,而在青光眼中,上和下區受影響最大[55],其測量是客觀和可量化的,而檢眼鏡檢查視神經蒼白的測定是主觀的和不可量化的。RNFL厚度也是評估腫瘤嚴重程度和預后的有用工具,RNFL 厚度的減少程度已被證明與視野缺陷相關[26],它可以預測由壓迫引起的交叉視野缺損患者減壓手術后視功能的恢復[27,56-58]。正常RNFL 厚度的患者顯示出增加的視覺恢復傾向,這種效應在長期隨訪后繼續存在[59]。
在細胞水平,視神經受壓導致視網膜神經節細胞 (RGC) 軸突損傷導致雙向變性現象:遠端軸突節段的Wallerian (或順行) 變性,以及受影響的RGC 的逆行性近端軸突變性和延遲的凋亡細胞死亡[60-61]。雖然導致這種細胞死亡的分子機制尚不清楚,但據估計,成年哺乳動物視神經損傷造成的細胞損失的嚴重性取決于幾個因素,如損傷類型及其與視網膜的接近程度[62]。
雖然pRNFL 變薄在垂體腺瘤引起的視交叉壓迫中很常見,但并不是所有的眼都能檢測到顳側視野缺損[29]。這種差異可能與傳導阻滯或軸突缺血引起的RGC 功能障礙有關[63],但尚未變性,因此在OCT 上顯示與神經軸索萎縮的損傷相關[26]。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一旦厚度降到某個閾值以下 (通常是標準健康對照數據庫的第五或第一個百分位數) ,OCT 上的橫截面pRNFL 厚度減小通常會被檢測到。如果厚度值還沒有超過這些臨界值,那么早期的pRNFL萎縮就可能不被注意到。更現代的分析試圖通過結合神經節細胞層 (GCL) /神經節細胞內從狀層 (GCIPL) 的厚度測量來提高OCT 對鞍區病變的檢測和監測的靈敏度。目的是直接量化由于交叉壓迫或彌漫性視神經壓迫導致的鼻側視網膜GCL 萎縮的程度。與pRNFL 相比,GCL/GCIPL測量已被證明具有更好的測試重復性,提高了視神經病變評估中的診斷準確性[64-66],并與視覺功能障礙具有更強的相關性[67]。事實上,有幾項研究已經評估了GCIPL測量在鞍區病變中的用途,并報道了在垂體腺瘤[58,68]早期檢測視交叉壓迫時提高的診斷靈敏度,即使視野檢查沒有視野缺陷[58,69]。
OCT 可以從垂體大腺瘤中檢測到輕度的pRNFL和GCL變薄,這些腺瘤缺乏視交叉或神經壓迫的影像學證據。CENNAMO 等[70]研究顯示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相比,58%的垂體腺瘤患者的平均黃斑GCIPL 厚度顯著降低,而無視交叉受壓的患者。筆者認為,其潛在機制可能與MRI未檢測到的微觀壓迫有關,或與垂體腫瘤分泌的血管活性肽內皮素-1 相關的RGC 軸突內軸漿流動的干擾[70]。這一有趣的發現需要進一步研究。
總之,這些研究支持OCT作為評估垂體腺瘤患者的重要輔助檢查的作用,以確認是否發生了前視覺通路受累,或客觀地量化臨床上明顯視覺缺陷患者的視網膜超微結構損傷程度。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具有已知垂體腺瘤的患者的視力損害可能由于多種原因而發生,包括并發的眼病,例如屈光不正、干眼、白內障或原發性視網膜病變。
OCT顯示pRNFL或GCIPL/GCL變薄的模式和程度的進行性變化可能有助于確認視力變化與視交叉或視神經壓迫有關。
對垂體腺瘤視交叉病變的OCT的縱向研究表明,由于RGC的再生能力較差,手術視交叉減壓[23,59,71]后,pRNFL 和GCIPL 厚度的恢復不明顯或不恢復[64]。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在OCT診斷時更嚴重的RNFL和GCL萎縮是否可能作為手術減壓后視力恢復不良的先兆。因此,一些研究者探討了OCT在垂體腺瘤視交叉病變中的預后作用。
較早的利用TD-OCT 的研究表明,術前RNFL 厚度的更明顯減少是手術后視力恢復差的一個強有力的決定因素[27,43,59,72]。在一項研究中觀察到了閾值效應,其中pRNFL 絕對厚度低于75 mm 的眼睛視覺恢復的可能性較低[17],盡管需要謹慎地解釋這一發現,因為絕對厚度測量可能會在不同的OCT 設備之間發生變化[73]。最近使用SD-OCT 裝置的研究表明,PRNFL 和神經節細胞測量的趨勢相似[41,74]。神經節細胞分析似乎與單純的PRNFL 厚度相比,與視覺結果具有更強的相關性,如果可能的話,應定期對這些患者進行分析。
4 結語
綜上所述,垂體腺瘤直接壓迫或視交叉血液供應系統的紊亂是垂體腺瘤患者出現視功能障礙的主要因素,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的質量和可用性的提高,使其在垂體瘤患者的治療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醫師可以通過磁共振來對瘤體侵犯的鞍上和蝶竇進行分類,評估視交叉和腫瘤之間的空間關系與視覺障礙程度相關性,是否需要手術干預。但對于那些未出現視交叉壓迫卻已經出現視功能損害的患者以及術后患者視功能恢復的預測指標在磁共振成像上并不明確,因此還需結合光學相關斷層掃描分析視網膜變化、視功能惡化和視交叉損害之間的密切關系,OCT提供了視網膜超微結構損傷程度的補充、定量的觀點,以便醫師及時發現垂體腺瘤患者視功能隱匿性病變,盡早挽救患者的視功能,同時對術后視功能恢復做出預判。隨著儀器設備的不斷更新,醫師對視網膜各個超微結構的透徹研究不斷深入,為患者提供更好的診治方法,獲取最好的預后結果。